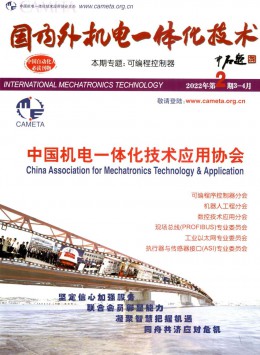一體化意識形態與當代文學論文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一體化意識形態與當代文學論文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1關于意識形態
20世紀50~70年代當代文學是在一種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發展的,因此影響文學發展的意識形態也具有特殊性,由于新中國剛剛建立,政權還不是非常牢固,所以建國后的整個社會生活都打上了高度的政治色彩并納入整齊劃一的步調,也就是說意識形態中的政治意識形態被高度強化,其他意識形態極度萎縮。從意識形態應有的內涵來說,政治意識形態只是其中之一,哲學意識、宗教意識、審美意識都是構成文學話語的意識形態內容,但在中國當代文學文本中,除了被領導層驗證并肯定的政治意識之外,哲學意識、宗教意識顯然是渴望而不可及的。另外構成特定時代的意識形態應該是多層的,有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有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形態,還應該有民間的意識形態,三者應該是并存的,可是在20世紀50~70年代的當代文學歷史話語中,我們幾乎聽不到來自知識份子和民間的聲音。由此可見,在那個特殊年代影響當代文學發展的意識形態只是來自官方的政治意識形態,他是狹隘的但又是無法抗拒的,他是文藝創作的通行證。
2意識形態對當代文學的規約
2.1“榜樣”的力量
一提到榜樣,人們很自然的就會想起雷鋒同志,想起“學習雷鋒,好榜樣,忠于革命忠于黨”這首耳熟能詳的歌曲,可以說雷鋒同志是所有中國人的道德楷模,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這一點是不容質疑的。而在20世紀50~70年代的文學創作中,同樣也有“雷鋒式”的好榜樣,榜樣是如何產生并樹立起來的呢?讓我們先踅回當代文學的原點,可以說中國的當代文學始于20世紀40年代初的延安革命文藝,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奠定了中國新文藝的發展方向,從文學的政治性,文學服務的對象等方面規范了文學的時代使命,在《講話》精神的指導下,解放區文學無論是小說還是詩歌都出現了嶄新的容貌。特別是趙樹理的小說創作因其鮮明的時代政治性以及廣大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而成為文學創作上的“榜樣”,文藝界權威人士對“榜樣”如是評價:“是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進而,向榜樣學習的活動馬上如火如荼的開展起來了,號召所有的邊區文藝工作者向他“學習”、“看齊”,可以說是政治的需要造成了文學創作上“榜樣”的產生,在那個年代政治壓倒了一切,也掩蓋了一切,文學的規律性和多樣性自然不算什么,只要文學作品能很好的服務于政治就有可能成為“榜樣式”的作品。而所謂的向“榜樣”看齊其本質上就是向“政治”看齊。1949年第一次文代會正式的將的《講話》精神確立為和平時期文藝運動的共同綱領,進而將解放區的文藝路線推廣至全國,榜樣仍在不斷樹立中,《紅旗譜》、《創業史》等小說及賀敬之的政治抒情詩等等,這些作品都因其突出地表現了“時代風氣”及“民族氣派”而成為同時期文學創作中的“榜樣”,在“榜樣”的感召下,大批的文藝工作者們都積極的投身于向“榜樣”學習的文學創作中,這樣一來大量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趨同的文藝作品誕生了,比如說紅色文學、政治抒情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然而,并非所有的文藝工作者都能創作“榜樣式”的作品,對于政治主流之外的“另類”作品,批評界及時并很有力度的對其進行批判和清算,比如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對“紅樓夢研究”的批判等等,在第一次文代會的一年以后,文藝整風及各種批判運動不斷上演并且一切都進行的順理成章,因為在第一次文代會將具有政治色彩的《講話》精神推為文藝權威的同時就將這種批判政治化、合法化、規范化了。在當代文學的發生發展過程中,政治意識形態始終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控制、規范著文學的發展,對于那些符合意識形態要求的作品馬上樹立為“榜樣”,并號召向之看齊,反之對于那些偏離意識形態要求的作品則加以嚴厲的批判和否定,這樣一來,文學創作的個性被完全扼殺,文藝工作者們帶著“鐐銬”進行創作,文學的多樣性成為夢幻,從而使50~70年代的當代文學走上了一體化的道路。面對當代文學那些近似于整齊劃一的文學文本,我們不得不感慨: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2.2行業的壟斷
在當代,作家協會是唯一的作家組織機構,作家協會從產生之日起就已然異化為準官僚機構,可以說,這是一種潛在的“行業壟斷”。作家進入到作協,通常有兩種情況,大部分的作家進行專業寫作,一小部分人擔任文學刊物的編輯,而幾乎所有作家都把自己的“戶口”也遷到了作協,這就意味著作協不只是一個普通的工作單位,還是作家們在社會上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可以說所有的作家都在組織的掌握安排之中。在建國之初,就有幾位“另類”作家(胡風、沈從文等人)惶惶不可終日,他們沒能進入官方的法眼,沒有被政府認可、安排,于是連起碼的寫作安全感都無法確立。這么看來,作家等于是被政府“養”起來了,被“養起來”的作家馬上就會失去自由說話的能力,作協作為知識者專業組織應具有的獨立性已經明顯喪失,對于這種意識形態對作協的控制、壟斷,一些有識之士也曾提出大膽的質疑,吳祖光曾指出“就文學藝術的角度看來,以為組織力量的空前龐大使個人的力量相對地減少了。假如是這樣,對于文藝工作者的領導又有什么必要呢?誰能告訴我,過去是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誰領導莎士比亞、托爾斯泰、貝多芬、莫里哀?”這種聲音是積極而又可貴的,然而面對意識形態所構建的牢不可破的體制,又能如何呢?美國總統杰斐遜曾說“:出版自由比言論自由更重要,通往真理最有效的途徑就是出版自由。”偉大的導師馬克思也曾強調:“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出版自由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然而當時的中國,意識形態把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作為一切工作的首要目標,一切都要為政治服務,出版自由作為其中一部分也被無情的犧牲了,早在1942年,中共中央書記處就發出《關于統一延安出版工作的通知》,統一出版的體制從戰時一直沿襲下來,1954年“出版自由”作為公民的權利被莊嚴地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部憲法,但近半個世紀之后并無一部出版法將出版自由作出具體規定,更甚的是到了后來所有的出版物都被簡單地劃分為“香花”和“毒草”兩大類了。可以說寫作和出版是文學這一行業最為重要的兩個環節了,然而這兩種自由完全被意識形態所控制、管理,文學這一行業被意識形態粗暴地壟斷,陷入了一個狹小的空間里,失去了多元化發展的可能性。
2.3評價的權威性
文學批評從本質上講,本應是一種藝術審美活動,別林斯基認為“批評家應當解決的首要問題是———這篇作品是優美的嗎?這個作者是詩人嗎?”普希金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認為文藝批評“是揭示文學藝術作品的和缺點的學科,它是以充分理解藝術家或作家在自己作品中所遵循的規則,深刻研究典范的作用和積極觀察當代突出的現象為基礎的。”普希金要求批評家保持“對藝術純潔的愛”,“哪里沒有對藝術的愛,哪里就沒有批評……努力愛藝術家,發現他創作中的美吧!”然而別林斯基和普希金對文藝批評的論述我們也許只能從魯迅、李健吾等人的文字中去印證了,當文學從屬于政治時這種要求就顯得尤為奢侈了,在20世紀50~70年代的文學批評中,專業性的批評和非專業性的、政治的干預相互交錯,很難加以區分,一些文學批評家本身又擔任政治職務,這樣曖昧的身份也使文學批評變得更加復雜,更重要的是對文學批評起決定性作用的往往不是這些文藝專家,特別是在涉及到一些重大問題時或是出現某些問題爭議時,最終決定權掌握在政治權力擁有者手中,而這種評價(政治權力擁有者的評價)是絕對權威的,只要他們發表一下看法,問題就定性了,根本沒有再討論或商量的余地,剩下的問題就是在文藝界如何具體的貫徹了。這種權威的評價對許多文學作品的高低正誤進行了一種近似于暴力的批判,比如對電影《武訓傳》、小說《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戲劇《海瑞罷官》等等,這些都能反映當時文藝批評界的真實情況,這種批判發展下去差不多已經變成一種政治行為了,詩意的感覺和對文藝作品中美的強大感受力在這時也顯得毫無意義,當然更談不上愛藝術和愛藝術家了。可以說意識形態控制下的文學評價機制以其最有效也是最粗暴的方式引導當代文學走上了“一體化”的道路。
3“一體化”的深層原因
對當代文學的發生發展,意識形態為何控制的如此嚴厲,而面對意識形態近似于粗暴的干涉,文藝界主流為何又坦然的接受甚至于有些人很是愉快的去迎合呢?關于這其中的原因應當是很復雜的:首先,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共產黨人在經歷了無數艱辛與磨難之后,好不容易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在建國初期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代里,意識形態需要利用一切力量幫助自己鞏固政權,而文學本身就具有的宣傳、教育、感染大眾的特殊作用,所以被意識形態格外的關注,或者可以說是為了更好的鞏固政權、建立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意識形態要求文學藝術幫他實現民族的全民動員,這一目標的確立使得意識形態把文學的發展始終規約在一定的范圍內,當藝術發展超出這個范圍時,意識形態就會及時的對文學施加影響使文學重新回到允許的范圍內。這種情況下的意識形態對文學的作用就像亞當斯密形容資本主義市場調節作用一樣,是一只“看不見的手”。其次,蘇維埃政府的確立標志著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這也就意味著后來者對他的模仿和學習,顯而易見新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也就難免要從各個方面向蘇聯進行學習和借鑒。文學盡管不是一種社會制度,但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共同信仰和對上層建筑、意識形態、經濟基礎的共同看法,再加上蘇聯社會主義社會走在中國前30年,使中國文學在很多方面都自覺不自覺地步蘇聯的后塵,中國當代文學的創作在最深層面受到蘇聯的影響,尤其是文學創作、閱讀、批評被認為是上層建筑中的意識形態,文學和政治性、黨性相結合這些方面,使中國當代文學的發生發展和政治聯系的尤為密切,沒能保持文學的相對獨立性。第三,中國傳統知識份子自由主義的缺失。中國知識份子歷來就有一種深沉的憂患意識,中國傳統士大夫素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優良傳統,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名言,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警句一直被知識份子奉為立身行事之準則,士大夫強烈的入世精神和參政意識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古訓一直延續至今,這種憂患意識從某種角度上可以說體現了中國傳統文人的愛國、憂民的高尚情懷,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也可以說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自由主義的缺失,中國的知識份子讀書學多是為了參與政事,報效國家,在中國幾乎很少有真正的自由主義學者,從屈原到李白、杜甫還有關漢卿,他們致學的目的是為了受到統治者的賞識,從而可以參政治國,只要統治者向他們伸出友誼之手,他們便會不假思索的為之效勞。中國的知識份子強烈的渴望承擔一些社會責任,在20世紀50年代,當振興國家、民族的機會擺在他們面前時,他們中的大多數熱情高昂并懷著感激的心態接受了,他們幾乎沒有拒絕的能力和理由。正是這些復雜的原因造成了意識形態對當代文學的控制規約,從而使當代文學走向了“一體化”。
作者:張丹 單位:遼寧現代服務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