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歌曲育人優越性的表現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經典歌曲育人優越性的表現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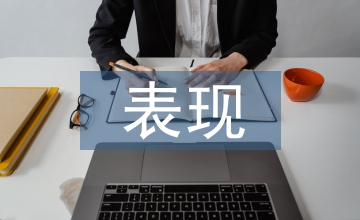
本文作者:蔣曉雷 單位:商丘職業技術學院
經典歌曲演唱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其育人效果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肯定。經典歌曲演唱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之所以能夠發揮其獨到的育人作用,除其自身歌詞所蘊含的豐富的思想內容外,其中音樂藝術因素所起的作用絕不能低估。一方面,“音樂和其他人文藝術是人類了解自己和他們的世界的一個基本途徑;它們是認知的一種模式。”[1]另一方面,較之其他藝術形式,音樂藝術在育人方面又具有不可比擬的優越性。2500多年前的教育家孔子總是把音樂作為他教學工作的一個最后階段,以培養有益于社會的弟子。此外,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音樂學院保羅•哈克教授更是堅定地認為:“音樂是人類生活的基礎,這一點毫無疑問。”[2]恩格斯更是高度評價音樂的作用,認為音樂是生活中最美好的一面。之所以如此,關鍵在于較之繪畫、雕塑、文學等其他藝術形式音樂藝術在育人方面具有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集中表現為音樂藝術表現感情的優越性、表現美的優越性、所起社會功能的優越性等三個方面。
一、音樂表現感情的優越性
“其他藝術說服我們,音樂突然襲擊我們”[3]。在表現人類的情感方面,沒有任何一種藝術形式能夠超過音樂藝術的表達力,這是音樂藝術的最大優越性。它通過聽覺直接和心靈接觸,能夠直接深入人類的情感進而影響人的精神、陶冶人的情操,因而它最能夠表達人類的感情。所以“音樂是情感的藝術”[4],被譽為“表情藝術的皇冠”[5]。不僅如此,在音樂體驗中還可以感受到其他藝術形式所無法達到的三種感情狀態,即美的感情、特殊感情以及基本感情。第一種是音樂中由美喚起的感情,強調外觀形式;第二種是在音樂作品中具有表現情感性質特點的感情,強調作者的感情狀態;第三種感情由于是在音樂體驗的根底里就存在著的感情,所以可以把它稱作基本感情。我們在聽經典歌曲音樂的時候,事實上能夠感受到不具有特殊色彩的那種精神上的高揚狀態。在這里,主要按照表達感情的邏輯性來論述第三種感情與第二種感情。
(一)音樂的基本感情
與視覺對象引起的感情相比,產生音樂的基本感情要同時具備至少四個條件。其一,感情和音樂同時在時間過程中運行;其二,感情和音樂同是一種非物體;其三,感情和音樂均與視覺的固定性無關;其四,感情和音樂均內含動力性運動特征。因此,在音樂的體驗過程中,音樂作品與)主體以獨特的方式非常緊密地融合在一起———音與心理狀態直接相融合。所以,音的主客一致不只停留于知覺,而且直到“內心”領域都能夠體現出來。在美的體驗中,主體與客體盡可能地取得深刻的一致是它本來的傾向,而樂音具備了實現這一點的所有條件。之所以如此,乃在于感情在時間過程中的狀態特性。感情在本質上,既不像知覺那樣只把握外部的表象,也不像思考那樣只把握思考的內容。感情是把對象作為動機來展開自己的,并且是有時間限制的。感情在關系到對象的情況下,是不能使自己得到展開的。感情是從其它的東西那里借力、生長,造成自己,然后減弱、再重新從其它東西那里借力。“感情這種不穩定性,一般把它稱作感情的動的性格。”[6]即使是在時間上有變化的視覺對象,由于它不能脫離開物的性格,所以只能在知覺方面與主體相接觸。而只有在本來是知覺的對象,而又能在心靈深處發現一致的音樂里,感情才能與之直接相接觸。
(二)音樂的特殊感情
音樂的特殊感情其實來自于它的基本感情。在我們聽完全不能理解的異文化的音樂時,甚至連音樂的基本感情也不會產生,更不會產生音樂的特殊感情,在這種場合里,由于不能理解它的意義,與聽完全不懂的外國語一樣。而聽取作為知覺對象的音,不外是為了獲得獨特的安定感與充實感。這種舍棄現實世界、完全歸于純粹內心的安定感,在其它藝術的享受中是沒有的。但這種基本感情變成意味內容的情況,決不是變成非現實性。這是由于這里所體現的象征作用是事實象征的緣故。茵格爾頓說,音樂形象造成的感情性格只不過是現實感情的相似物,是現實感情的特殊的變化體。
關于音樂特殊感情的現實性與非現實性的問題,應該從兩方面來看。第一是引起感情的對象是現實的還是非現實的問題。虛構的小說的主人公不是實在的,他所經歷的事件是虛構的,然而他卻能使我們或感到悲傷,或感到喜悅,這種場合是非現實性的對象引起的感情。但是即使是在這種場合里,在能夠引起感情的范圍內,必須具有一種事實性。這種感情不是知道這是虛構所引起的感情,而是忘記了這是虛構所引起的感情。第二是引起感情的對象是具體的還是抽象的問題。文學作品和繪畫等的描寫內容是具體的,而建筑、音樂、抽象畫等是非具體的,它們的意味也是抽象的。但是這個區別與現實的或非現實的沒有關系。從感情的本性來說,它沒有能力決定這種場合里的對象是現實的還是非現實的。但感情本身總是現實的,它本身不能變成非現實的。而某種事實,由于它能變成單詞,成為概念,因此可能采取一種非現實性的存在方式。但是感情卻不同,即使它像在音樂的場合里那樣被對象化,成為意味內容,然而由于它不能成為概念,所以由事實象征的作用所產生的東西總是現實的。反過來說,由于感情只能是感情,所以它不能脫離事實性。
二、音樂表現美的優越性
“只有通過音樂的美感,人們才可在身心愉悅的前提下深刻地感受音樂、鑒賞音樂、表現音樂,音樂的其他功能才有實現的可能。”[7]孔子非常推崇音樂美的獨到作用,他的“樂以治性”、“成性亦修身”的觀點是基于音樂、對人的德性的培育不是靠外在的強制,而是以音樂之美感化人的性靈,使“仁”成為內在情感的自覺要求。較之其他藝術形式表現美的特點而言,音樂表現美的優越性有以下幾點。
(一)音樂表現內在意味作用內容的美
我們一般通過三種方式把握存在于外界的感性事物。一是對把握感性對象的本體,二是把握感性對象的屬性和樣態,三是把握某種感性對象的意味性內容。所謂意味性內容,是指感覺對象的本體和屬性以外的東西,美的成立就可以體現出這種意味作用。音樂的美在四個方面具備了作為意味作用的內容的條件。第一,美是與對象的屬性明顯不同的東西,然而它卻還是關于對象的什么內容。第二,美與顯示它的感性對象存在著必然性的關聯。第三,含有美的知覺對象都具有作為符號的性格。第四,美的體驗具有終極性的性格。意味體驗在對知覺對象的把握之后,還要對其背后的意味內容加以把握。意味體驗以把握它的意味作為目的,只有這樣才是完成了的體驗。當我們從某種對象身上感到美的時候,獲得一種滿足感,作為體驗本身就不再前進了。
音樂的美盡管不是屬性,而是意味作用的內容,卻也會像屬性那樣被人們接受。這是因為,在音樂美的體驗中,體現意味的東西和意味內容不僅渾然地融合在一起,而且后者還一面籠罩著前者,一面與前者共存于一體。美在對象中具有一種在超越性的意味作用中看不到的浸透性和飽和性。它呈現出好像給對象覆蓋上一層色彩那樣的狀態,在這點上也可以說美是為對象染色。當然,本來的色彩是對象本身的屬性,而不是意味內容,這也是不言而喻的。進行內在的象征體驗時,在意識中象征體與象征內容的結合方式有下面兩種。一種是完全或接近于完全的結合,為此象征體的知覺特點完全被象征內容所掩蓋。在偶像崇拜的信仰中,偶像不是意味著神而是被看作神的本身,就屬于這種情況。因此,在這種場合里,在體驗的內部,所謂象征則沒有被意識到。另一種結合方式比較松散,在看到象征體的知覺特點與本來的存在的同時,象征內容的性格對象征體給予影響,好像象征體的性格那樣被接受。例如,誰也不會把作為愛的符號的紅玫瑰看作是愛的本身,但是玫瑰本身接受了愛的性格,也被看作是“可愛的”、“溫柔的”。
(二)音樂的單純感覺美與綜合形式美
可以把音樂的美明確地區分為兩種。一種是單獨的音響本身所具有的美,另一種是由許多音在時間過程中的組合關系所產生的美。這里把前者稱作單純感覺美,把后者稱作綜合形式美。通常,如果說起音樂的美,首先想到的主要還是作為后者的綜合形式美,然而前者單純感覺美的存在也是不能否定的。只就音樂中所用的音來看,它也是與日常的雜音不同的一種美的音。這種情況在人聲的場合里是特別明顯的。這種單純的音的感覺美,只是一個音的美。在音樂體驗中所感到的美,主要是音與音相互關聯的美,是形成音的形式的構成美。當然,單純感覺美是造成音樂的中心美這一點也是不能否定的。
除指示發音體的日常音,指示意味作用的語音之外,只有在具有美的意味的場合里,音才能成為感覺的對象。既不是第一種日常音,也不是第二種語音,而且又不具有美的意味的音,不能成為我們的感覺對象。第一種日常音的意味,或是第二種語音的意味,它們的意味之所在,都超越了感覺性的音。音只是意味內容的媒介體,正是由于美,音樂才能保持著與語言不同的音的感性性格。在音樂體驗中,從發出最初的音開始,它就已經具有了美的性格。音樂中單音本身所具有的美,不單是音的性格,而且是它的必然的存在方式。美的音是音樂的唯一素材,用非美的音創作音樂是不可能的。這是由于非美的音不能夠保持感覺性的緣故。正是由于保持了這種感覺性,才使得對于音樂體驗來說更為重要的綜合形式美成為可能。不具有美的意味的音,其本身沒有任何存在的意味。當然它在物理上無疑是存在的,然而對于傾聽它的主體來說,由于完全沒有意味,所以和不存在是一樣的。
在一般情況下這種美的音,如果從音響學上說就是樂音。作為素材的樂音,對于音樂來說具有雙重的意味。一方面是現在所說的,由于有美的性格而保持著感性的性格。另一方面是為了使音樂的形成變為可能,要求它具有單純的抽象性的性格。后一方面可以和單純用抽象的線來描畫圖形最為方便的事實進行類比。而且,這種性格即使是沒有音樂中的樂音那樣徹底,但是在語言的聲音中還是存在的。因此可以把語言作為準樂音。但是在語音的場合里,只要是能夠根據語音造成明確的形式,并且能夠傳達意味也就夠了,而上面所說的第一種性格,即具有美的性格對于語言來說是不必要的。與此相反,在樂音的場合里,由于保持感覺性是必要的,所以具有美的性格也是必要的。由于語言中的音的確具有超越性,所以內在的美的性格相反地倒成為一種干擾。而對于音樂來說,音的美卻是一種必要的條件。但是,音樂本質性的美是具有單純感覺美的音有機組合后新形成的綜合形式美。
(三)音樂性格的美
音樂美是在完形之上建立的。這種完形具有與視覺美的完形不同的狀態。而且,這種狀態當然也就規定著音樂本身性格的美,也就是說在音樂中,作為其象征內容的美與作為其象征體的音自然而密切地緊緊融合在一起。美與音的密切融合的第一個原因是,音并不像視覺對象那樣在空間里占有一定的位置,因此音樂的音也就把作為美的象征體———即作為符號———的性格,純粹而且單一地保持了下來。美與音的密切融合的第二個原因在于,音樂是處于時間的過程之中的這個特性。關于這一點,還必須首先說一下在視覺美的體驗中美的獨特的時間性。我們知道,美的對象實際上轉瞬即逝,由于再次獲得的新鮮印象,美的對象所呈現的狀態才不斷地重復出現。而且美的體驗與知覺不同,它雖然很快地會被證實,但是由于這種狀態的持續具有價值,所以會產生一種盡可能地使這種狀態持續下去的要求。知覺對象在它確立的瞬間就完成了任務,然而美的對象卻不能這樣。這是由于美的對象如果在瞬間就完成了任務,那它就不是美的體驗對象,而只不過是知覺和認識的對象。這時它就不是內在的意味作用,而變成超越的意味作用了。由于美只是在與知覺對象的關聯中成立的,所以它一離開知覺對象,就不能長久地生存下去。美的內在象征是一種非常微妙的狀態,如果沒有精神深處的活動它就不能持續存在下去。內在象征如果經受不住這種緊張的活動,它就會迅速消失。但是由于美的體驗本身具有使其繼續存在下去的必然要求,所以知覺對象會再一次變成新的,并且再一次體現象征作用。
三、音樂社會功能的優越性
早在我國春秋戰國時期,《荀子•樂論》和《禮記•樂記》就已詳細論述了音樂的社會功能,反復說明“人不能無樂”的道理,主張建立心靈秩序上的樂與建立社會秩序上的禮互相配合,并認為禮者,天地之序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史記•樂書》亦云:“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歡心,故天下治。”[8]這也是任何一種其他藝術形式所不可比擬的優越性。音樂所起社會功能的優越性可以分為非傾向性功能與傾向性功能兩種。
(一)音樂的非傾向性功能
人們之所以在欣賞音樂時能夠獲得一種直接情緒上的刺激,是因為音樂本身具有一種潛在的功能。這種功能來自于人類的生理性生物需求,由于它沒有基本的任何社會傾向性,故稱為非傾向性功能。這種功能是由于人的天然生理性生物需求與音樂作品結構當中包含的情緒類型之間被音樂的知覺第一階段溝通的緣故。漢斯立克認為,音樂之所以能夠對人的神經刺激起作用,它完全以聽覺印象影響神經的某種特定方式為基礎。因而,音樂才能夠完全“象一股沒有形態的魔力向我們全身神經激烈地進攻”,[9]并且還能夠對于人們過分激動的心情施加一種安靜、愉快的影響。所以,在人們欣賞音樂的時候,往往在還沒有來得及用自己的美感經驗去判斷的時候,內心就已經被立刻打動了。
(二)音樂的傾向性功能
人們在欣賞音樂的時候往往還會獲得某種情感體驗。這是由于人們的音樂知覺處在了深化階段,音樂作品中包含的客觀的情感內容與人們對音樂藝術具有的某種社會性需求達到了主動而自覺的相互溝通,在此基礎上,人們又往往對音樂展開了體驗性想象與聯想,使那些在音樂中固有的抽象性情感內容進一步具體化,并賦予了具體的豐富的社會性內容。人們的社會性需求因此得到滿足,這就是音樂的第二個功能。由于這種功能具有明顯或暗含的社會傾向性,被稱為音樂的傾向性功能。
“音樂傾向性功能的實現需要音樂中的情感內容和非音樂因素兩個客觀條件”[10]。一方面,音樂并非直接影響人們的各種社會活動,而是以情感的方式間接影響人們的社會性精神生活。不過,音樂的情感內容是一種總體的精神特征,它是一個國家民族的、時代的以及富有個性的某些藝術家對于某個特定的社會事件綜合反映出來的一種概括性的精神內容。因而,音樂的傾向性功能,只能僅僅體現在以總體的精神特征給予人們某種抽象的社會性需求的滿足上。另一方面,能夠引起主體想象和聯想的依據同時還包括非音樂因素。音樂中的非音樂因素包括限定性與非限定性因素。限定性因素主要指包括歌曲的歌詞、歌劇的劇情和唱詞等等在內的確定性的文學性內容,這些明確的音樂因素與相應的音樂表現密切地結合在一起,為聽者指定了聯想的確定性方向。非限定性因素是比較廣義的社會內容,主要體現為音樂作品產生的特定條件,例如音樂作品產生的思想傾向、時代特點和概括性的社會含義等。不過,通過音樂表現出來的這些社會內容暫時還只是一種概括性的精神特征,只有當其被聽眾作為聯想依據的時候,才可還原為具體的社會性內容。相較而言,在非音樂因素與感情要素中,非音樂因素永遠要附屬于音樂中的感情內容。唯有音樂中的情感特點與非音樂因素所限定的內容相統一與吻合的時候,聽者才有可能沿著非音樂因素所指定的方向進行聯想。
音樂的傾向性功能實現的主觀條件是欣賞者借助音樂作品提供的依據進行聯想以及把概括性、抽象性的情感內容轉化為具體性的能力大小。這種能力包括三個方面。其一,欣賞者對音樂的非音樂因素的理解和掌握能力,主要體現為對音樂以外的歷史、文化等方面修養的程度上。其二,欣賞者欣賞音樂之時所具有的情感體驗的能力。音樂根本不可能通過對某一具體對象的聯想來獲得感情,與此相反,它以情感體驗為聯想的前提,情感體驗愈強烈,聯想也愈活躍,對情感內容的認識也愈深刻。因而,人們在欣賞音樂時情感體驗的程度,對于其依靠非音樂因素所提示的定向聯想有直接的影響。其三,人們在體驗情感的同時,怎樣根據其判斷沿著非音樂因素所指定的方向進行聯想的能力。相較而言,音樂的聯想較為特殊,它由抽象的情感特征聯想起具體的情感內容,或者由音樂中的情感回憶起以往經歷中產生的類似情感,從而來把握音樂中情感內容的精神實質。
必須指出的是,音樂的傾向性功能受一定的歷史和社會條件所制約,其包含的社會內容是在特定歷史與現實條件下的社會反映。由于音樂的傾向性功能具有某種特定的社會政治意義,因而在這方面占優勢的音樂題材和音樂形式就很容易為當時社會政治的需要利用。不過,人們的政治觀點如果與非音樂因素的社會內容不符合,他就不可能受其政治傾向的影響,只能從音樂中得到非傾向性的功能和審美功能。所以,音樂反映社會生活現實的間接性特點決定了它對社會政治方面的影響一定要與廣泛的社會因素緊密結合在一起。也只有在相應的社會思想基礎之上,音樂才能對社會的政治、教育等活動起到不同程度的輔助作用,而單純僅僅依靠音樂根本不可能達到某種政治或其他教育的目的。
綜上所述,經典歌曲之所以能夠發揮對大學生獨到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中蘊含的音樂藝術因素。在所有的藝術形式影響人的程度方面,音樂藝術以其表現感情的優越性、表現美的優越性、所起社會功能的優越性等三個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這是任何其他藝術形式所不可比擬的。因此,恰當并充分挖掘和利用經典歌曲中隱含的音樂因素對于加強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