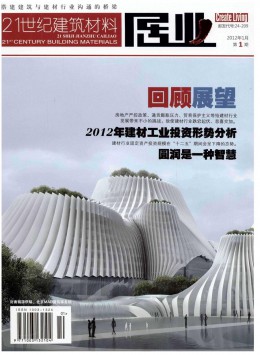建筑材料和結構形式選擇探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建筑材料和結構形式選擇探究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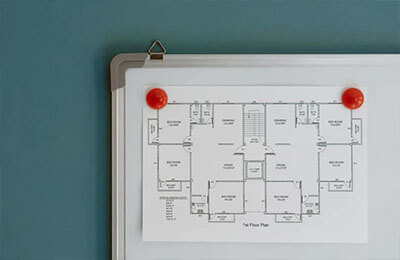
摘要:建筑材料與結構形式對建筑而言至關重要,二者相輔相成,建筑材料的創新會推動結構形式的發展和升級,而結構形式的發展同樣會促進建筑材料的推陳出新。本文通過對某紀念碑設計的建筑材料和結構形式的選擇、運用進行分析,論述建筑材料和結構形式的選擇、運用與紀念碑(建筑)設計的重要關聯性。
關鍵詞:建筑材料;結構形式;紀念碑;關聯性
1引言
從古至今,每一種新型建筑結構形式的出現都會伴隨著與之相適應的新型建筑材料的誕生,而每一次新型建筑材料的出現同樣也會推動建筑結構形式的升級發展。無論是早期人類居住的天然洞穴,還是經發展而產生的人工洞穴,或是進一步發展運用樹枝、樹葉、泥土、茅草等材料建造的簡易地面建筑,再到后來伴隨人類文明不斷進步而出現的更高層次的木結構、磚石拱券結構等,無不是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對建筑材料和結構形式的不斷發掘運用而將建筑技術逐漸推向成熟的。不同建筑材料和結構形式的選擇運用,將直接促進建筑工程技術向前發展。比如,我國古代由于自然環境未遭破壞,因此擁有充足的木材資源,而木材具有便于就地取材和易于加工的優良特性,使得木材被廣泛運用于木結構建筑的建造,從而創造出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木結構建筑建造技術,也為大批享譽中外的木結構建筑瑰寶能夠保留至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相比之下,西方更注重對石材的運用,并創造了磚石拱券結構等建造技術,乃至后來因發現火山灰而發明了水泥,進而促成了現代重要建筑材料——混凝土材料的出現,由此發展產生了現代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剪力墻結構、剪力墻復合結構等廣泛運用的結構形式。西方人對于堅固和永恒的追求,使得石材逐漸取代木材而成為主要建筑材料。石頭堅固、恒久的特性自然地與紀念碑性聯系在了一起,西方大量著名的紀念碑性建筑都用石材建造而成[1]。建筑材料和建筑設計總是互相推動和促進的,新的建筑材料的出現給建筑設計的發展帶來新的推動,如建筑結構的創新等。而建筑設計的發展又對建筑材料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2]。隨著可供選擇的建筑材料和結構形式越來越多,人類對各種建筑形式的追求目標不斷得以實現。正因為有了成熟的建造技術作為支撐,才使得建造復雜多樣的紀念性建筑成為可能。古埃及的方尖碑、金字塔,中國古代歷朝修建的祖廟、祭壇及陵墓都可算是宗教紀念性建筑的開端。現代建造紀念性建筑的目的是保存歷史中人、事、物的記憶。其空間造型的藝術美感和可長久屹立不毀的特點,恰恰符合紀念活動的需求,從而成為人類紀念活動的重要手段,并且形成了特有的建筑文化[3]。正是由于建筑材料與結構形式相互選擇和相互支撐,才促成了古今中外許多不朽的紀念性建筑在世界各地長久屹立的景象。
2材料選擇與紀念碑設計
建筑材料不僅是建筑工程的物質基礎,同時也是建筑工程質量的前提保障,建筑材料的質量與性能對建筑工程的安全性與耐久性有著直接的影響[4]。然而,在現代建筑設計和建造過程中導致不同建筑材料選擇運用的因素卻是多方面的,有氣候環境的影響、結構形式的影響、工程技術的影響、建筑功能的影響、建筑造型的影響,等等。但歸根結底都是為適應建筑形式和結構形式做出的合理選擇。例如,某紀念碑的建設地點為熱帶、亞熱帶季風氣候,該地一年只分為旱、雨兩季,其中雨季較長,一般為5至10個月,最大年降水量達3750mm,年平均氣溫為10~20℃。從氣候條件來看,該地區建構筑物所處的環境為濕熱環境,設計主要考慮建構筑物的脹縮和防潮采取應對措施。氣候的差異性導致自然環境的多樣性,自然環境的多樣性產生人類文化及建筑形式的豐富性,建筑是對氣候環境、地形、地貌條件的被動適應與主動創造的結合[5]。為使紀念碑較好地適應濕熱氣候環境,紀念碑主體建筑材料選用鋼筋混凝土澆筑,這充分利用了混凝土材料在潮濕環境中的耐久性和適應性,同時又兼顧了紀念碑對建筑材料的堅固性要求。由于紀念碑主體的截面積較小,僅為2.36m×2.36m,因此材料脹縮對結構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除主體結構本身的建筑材料外,出于對氣候環境的適應性考慮,紀念碑的外墻采用30mm厚外掛花崗巖石材對碑體進行外裝飾。此外,紀念碑的碑頂采用能迅速排水的四坡頂形式,并采用釉面小青瓦作為坡屋頂的裝飾材料,確保紀念碑具有較好的防水性能和耐久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設計對建筑材料的選擇運用均已考慮到與紀念碑的適應性(見圖1)。建筑材料的選擇在滿足環境氣候要求的同時,還應滿足紀念碑建筑的造型要求。由于該紀念碑坐落于整個紀念園的中心位置,是整個紀念園的視線焦點,同時也是制高點,再加上該紀念園的建設地點為境外,紀念碑的方案設計應著重突出中國元素,這一點無論從建筑形式還是建筑材料的選擇使用上均得以充分體現。比如:屋頂均采用具有顯著中國傳統建筑風格的坡屋頂設計并采用傳統釉面小青瓦裝飾,墻面采用灰白色涂料裝飾,勒腳則采用傳統清水磚墻裝飾,等等。同時,設計為了充分表達出紀念碑的中國元素,采用傳統三段式設計將整個紀念碑造型分為基座、碑體和碑頂三大部分。其中基座底部截面尺寸為4.66m×4.66m,高3.91m(含浮雕部分),整個紀念碑基座建在1.2m高的平臺上,進一步增強其作為視覺中心和制高點的作用。在紀念碑基座的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分別設計鑲嵌了4塊尺寸為3.06m×1.30m的主題淺浮雕,進一步表達出紀念碑的設計主題及其所蘊含的歷史含義。主題淺浮雕采用120mm厚的漢白玉石材雕刻,選擇漢白玉材料是為了有效突出淺浮雕的紀念主題內容,以及與紀念碑主體裝飾材料協調一致。同樣,在碑體正面中心位置鑲嵌一塊書寫紀念主題文字的寬1.4m,高6.0m的漢白玉材料,也是出于與紀念碑主體裝飾材料相適應的考慮。
3結構形式選擇與紀念碑設計
結構形式與建筑材料選擇的區別在于建筑材料注重與建筑形式的匹配性與環境的適應性,與材料力學特點的符合性,以及與建筑美學和藝術要求的一致性;而結構形式則更多地從建筑的安全性和耐久性出發,綜合考慮建筑結構體系的受力特點及建筑材料的力學性能后做出合理選擇。“對于高聳結構,與地震作用相比,風荷載起控制作用。而混凝土結構自重大,抗傾覆穩定性更好。綜合考慮以上因素,最終采用混凝土剪力墻結構。”[6]正是因為剪力墻結構體系具有較好的承載能力和整體性,所以可將其選擇作為紀念碑等高聳建筑的結構形式。同時剪力墻結構還具有側向剛度大,在水平荷載作用下側移小的優點(見圖2)。而紀念碑作為高聳建筑,承受風荷載或地震作用引起的水平荷載較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正好符合剪力墻主要承受風荷載或地震作用引起的水平荷載和豎向荷載(重力),防止結構剪切(受剪)破壞的特點,還要兼顧紀念碑所處環境等因素。因此,綜合分析各相關因素,紀念碑的主體采用鋼筋混凝土剪力墻筒體結構體系。紀念碑主體為2.36m×2.36m的正方形剪力墻筒體布置,剪力墻厚度為250mm,在四面剪力墻的交角處均設置了構造邊緣轉角柱,起到改善受力性能的作用。同時設計在紀念碑主體豎向每隔3m布置一道水平樓板與剪力墻連接成整體,進一步增強結構整體性和穩定性。為較好地滿足紀念碑穩定性要求并進一步減少地基承載力弱的影響,紀念碑的基礎形式采用平板式筏板基礎(見圖3—圖6)。
4關聯性分析
通過以上對于某紀念碑的設計分析可知,紀念性建筑在不同氣候環境、不同經濟、社會和技術背景下,所采用的材料、結構形式會存在一定的差異。但無論采用何種結構形式均會有特定的建筑材料與之相適應,而新型結構形式的采用則必然會對建筑材料提出更高的新要求,二者相輔相成密不可分。正如在建筑歷史長河中逐漸發展成熟的木材對應木結構,磚、砌塊、水泥、沙石等對應砌體結構,鋼筋混凝土對應框架結構、剪力墻結構及框剪混合結構,鋼材對應鋼結構等一樣,正好形成建筑材料與結構形式一一對應的關系。縱觀我國古代建筑歷史,建筑用材大多以木材為主,以石材、磚土為輔。究其原因,其一是古代具有保護完好的自然資源,建造者在未遭破壞的自然環境中易于就地取材;其二是木材具有延性等優良的結構性能;其三是木材易于加工,可以按照特定建筑模數定型化批量加工,以及木構件可拆卸和可更換的優越性,大大提高了木結構建筑的建造速度。因此,對于木材建筑材料的選擇運用,正是我國古代木結構形式與木材建筑材料相互適應的印證。從結構形式來看,我國古代采用木材建造的梁柱式木結構建筑中,各個構件之間均以榫卯構造連接,構成一個富有彈性的框架整體。榫卯構造節點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活動性,以及木材自身具有延性的特點,可以把巨大的震動能量在彈性結點上有效消減,從而大大降低地震對建筑的破壞。這對于地震較多的我國大部分地方來說是極為有利的。這也正是木結構建筑在我國古代得以大范圍推廣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見,木結構形式與木材建筑材料的相互依存和密切關聯的關系,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古代各類木構件(建造材料)的創新和發展,并進一步發展成為成熟的木結構建筑形式。
5結語
在眾多的建筑設計和建造過程中,無論是大體量、超高層、大跨度建筑,還是精巧如雕塑般的景觀建筑,無論是享譽中外的著名建筑,還是默默無聞的一般建筑,最終采用何種建筑材料和結構形式建造,都不能片面地說哪種建筑材料和結構形式是最優的。只有適合的、可持續的才是最好的,只有充分發揮材料自身優勢并能與結構形式相匹配,與其所處時代、環境、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相適應的才是最優的。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為不斷涌現的新興材料提供了廣闊空間,也給建筑結構形式的發展帶來了無限機遇和挑戰。總而言之,在建筑結構形式和材料選擇時,我們應當綜合考慮建筑所處地理氣候環境、建造技術、建筑造型及體量、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條件等諸多因素,才能創造出建筑材料與結構形式完美結合的時代建筑。
參考文獻
[1]陳勝疆,關瑞明,季宏.淺談中西方古代建筑中的“紀念碑性”:兼論中西方文化差異[J].藝術與設計(理論),2020(03):74-76.
[2]劉宇鵬,建筑材料與建筑設計關系淺析[J].現代裝飾(理論),2014(02):42-43.
[3]裴建釗.當代紀念性建筑設計手法初探[D].西安建筑科技大學,2010.
[4]李愷希.淺談建筑材料的發展與創新[J].科技資訊,2018,16(20):61-62.
[5]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王必剛,王啟文,何曉雪,等.渡江戰役紀念館勝利塔結構設計中的關鍵問題[J].建筑結構,2011,41(S1):554-556.
作者:吳昊洲 單位:鄭州大學土木工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