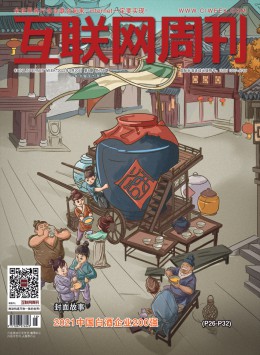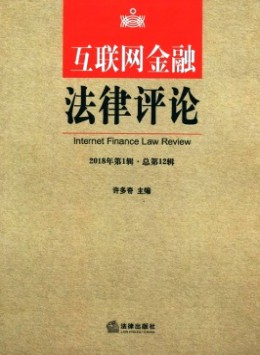互聯網+檔案利用服務工作變革思考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互聯網+檔案利用服務工作變革思考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當前,各級各類檔案部門開展了大量的數字化工作,但是數字化成果應用效果不理想。“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使得人們的信息意識、信息獲取能力和途徑、檔案本身以及檔案工作所處的環境發生了變化。變革的同時伴隨著機遇,要把握機遇,實現轉型升級,需要重新定義檔案利用服務工作,發掘其長尾市場,并且依托新媒體讓檔案走進大眾日常生活,在安全、保密的基礎上實現最大限度的開放和共享。
關鍵詞:互聯網+;檔案利用服務;信息資源開發
“互聯網+”時代,檔案信息化的最終目標和檢驗標準是要促進檔案信息的廣泛流動、分享和使用。“信息的使用存在邊際收益遞增性,即信息/數據只有在流動、分享中才能產生價值,流動的范圍越大,分享的人群越多,價值越大。”[1]實現檔案信息最大程度的流動、分享和使用,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檔案價值。
一、傳統檔案利用服務工作的局限
傳統的檔案利用服務工作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被動性,往往建立在“坐等上門,你查我找”的狀態,通過嚴格的申請與審批流程后,在特定的情況與環境下,服務于特定的用戶。檔案信息始終掌握在檔案管理部門手中,服務對象僅限于前來查檔的、符合相應要求的現實用戶。雖然近年來在檔案信息化浪潮中,在國家檔案局等部門各項政策鼓勵下,檔案數字化工作開展得如火如荼,積累了大量的數字化檔案信息資源,但是服務力度和情況仍然不盡如人意。筆者通過網絡瀏覽的方式,調研了我國23個省、4個直轄市、5個自治區,共32個檔案信息門戶網站。截至2019年2月底,這些門戶網站中提供目錄檢索與著錄信息的僅17個,提供全文檢索與閱讀的僅3個,雖然部門檔案館有“檔案薈萃”“專題檔案”“網上展廳”之類的欄目,但是基本只展示少量圖片。檔案利用服務工作沒有得到實質化的提升,“社會認知度較低,服務創新能力較弱,內容質量較差,用戶活躍度較低”[2]“四座大山”仍然存在。長此以往,在“互聯網+”時代的沖擊下,檔案工作將舉步維艱。
二、“互聯網+”帶來的變革
(一)信息意識的改變,促進檔案部門主動作為“互聯網+”時代,信息的獲取和傳播變得簡單而快速,人們的信息需求不斷地得到滿足,工作、生活中的很多問題也在信息的獲取和處理中得到快速解決。正是這種受益,使得人們意識到信息的重要性,新的信息需求不斷涌現,對信息的敏感力和洞察力也不斷提升。在這樣的沖擊下,一味宣傳和告知人們“檔案具有重要價值”的方法已經難以實現認同。“如果檔案服務部門仍固守傳統的檔案思維,沿用傳統的檔案服務方式,那么檔案將失去其存在的意義,檔案服務也將無務可服。”[3]相反,檔案相關部門只有將檔案信息足夠多地推送到人們眼前,引起關注,甚至引導其共同開發、傳播,才能促使檔案信息在流通與處理中得到社會認可。
(二)信息獲取能力和途徑的改變,促使檔案部門改變工作模式“人們獲取信息的能力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和發展而得到不斷的提高。”[4]電子計算機和互聯網發展之前,人們主要通過語言交流、書籍、雜志、電報、電話、電視等通訊工具獲取信息。信息獲取途徑的局限性,造成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使得信息獲取效率極低。隨著電子計算機和互聯網的飛速發展,人們逐漸從依賴專業人員進行搜索、指引、提供信息,到主動地提取關鍵詞、自行搜索發掘,再到面對海量信息快速進行篩查與過濾,人們的信息獲取能力不斷增強。加之信息源巨大,信息的易獲取性已經成為決定是否獲取相應信息的首要因素。在此沖擊之下,檔案部門傳統的“層層審批、你查我找”的工作模式顯然難以維系,檔案部門目前只公開部分目錄數據、專題展覽形式單一、粗略的信息化成果,難以引起關注和重視。
(三)“互聯網+”擴大了檔案征集的外延正如馬云在阿里巴巴的一封內部郵件中所判斷的:“我們正在從以控制為出發點的IT(信息技術)時代,走向以激活生產力為目的的DT(數據技術)時代。”[5]在DT(數據技術)時代,檔案的概念本身也泛化了,大檔案觀念逐步形成。在“存量電子化,增量數字化”的信息化進程中,檔案“數據化”越來越引起人們重視,尤其是在油氣地質檔案等專業檔案領域,科研人員需要數字化的成果報告、各類測井綜合圖滿足跨時間、空間的查看,更需要數據化的測井、錄井數據等,實現信息重組、圖件重繪等。另外,“互聯網+”帶來了跨界融合,網站數據、社交媒體數據、個人日志等網絡數據也逐漸被納入檔案數據的范疇,使檔案的外延不斷擴大。在這樣的沖擊下,檔案部門需要樹立“大檔案”的管理思維,改革和調整檔案工作方式與目標,變革檔案工作收、管、用等環節的工作思維與模式。
(四)“互聯網+”給檔案工作所處環境帶來的改變“信息公開,即向公眾提供已公開和可公開的現行文件及已開放和可開放的檔案,已經成為我國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社會進步的重要潮流。”[6]開放、良好的政策環境給檔案利用服務工作帶來了機遇。在傳統的檔案工作中,檔案信息主要來自并集中于特定的組織群體,由檔案部門進行統一管理和提供利用服務,交互方式相對單一,服務方式和服務內容具有較強的針對性。進入互聯網時代,在“三位一體”的網絡環境下,每個人都可能是檔案信息的使用者,又是生產者和傳播者。檔案利用服務交互方式更加復雜,公眾對檔案利用服務的多樣性、準確性、便捷性、新穎性等有了更高的要求,對檔案信息價值及其呈現方式的期待值上升,容忍度下降,給檔案利用服務工作帶來了巨大的沖擊。
三、“互聯網+”時代檔案利用服務工作的重點
需要看到的是,不僅僅是檔案工作面臨“互聯網+”時代的沖擊,各行各業,政府、企事業單位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互聯網+營銷”實現了企業與消費者的交互,實現了目標人群的準確定位和對小眾用戶的開發;“互聯網+金融”提升了支付清算效率和形成了完善的征信系統,適應了當前資金需求小型化、大眾化的發展特點,擴大了傳統金融的供給方式,朝著“隨身獲得金融服務”方向發展。大量成熟的案例,不僅在無形中使廣大群眾養成了互聯網信息獲取、使用的習慣,還使得大眾對于“互聯網+檔案利用”有更多的期待和更高的接受度。而檔案利用服務工作如何抓住“互聯網+”機遇,實現自我革新、轉型升級,則是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
(一)以人為本,重新定義檔案利用服務工作“‘互聯網+’環境下,被動式的服務理念已逐漸被各行各業所拋棄,取而代之的是主動式的服務理念。”[7]主動式服務理念的中心思想是“以人為中心”,重新定義檔案利用服務工作,使之最大限度地滿足并激發用戶的信息需求。此即必須明確檔案工作的價值,不僅局限于傳統的為領導層面、特定人員提供憑證參考,還應“對政府部門的治安管理、企事業單位的商業決策、創新創業等發揮重要的信息支持作用”[8];不僅局限于被動滿足上門查閱者的利用需求,更要主動為社會大眾提供檔案信息資源,既滿足娛樂休閑的信息需求,又滿足增長知識見聞的信息需要;充分尊重不同群體的多樣信息需求與信息權力,“積極踐行以人為本的核心服務觀,為用戶提供一個廣泛參與、社會協同的開放型空間,解決用戶的顯性需求,激發他們的隱性需求,促進檔案服務的縱深發展”[9]。
(二)開放共享,發掘檔案利用服務的長尾市場在傳統檔案利用服務工作中,“各級檔案館以自身為中心進行孤立、封閉式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檔案的利用和服務缺乏廣泛性與普遍性,受眾面小”。[10]并且按照管理權限等提供查詢和利用的方式,開放共享程度有限,即便是上門查閱的用戶,能接觸到的檔案也有限,缺乏選擇的空間和機會,難以激發出隱性需求。互聯網憑借其強大的資源整合、技術融合、信息與交互等功能,給檔案利用服務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一方面依托強大的資源整合與存儲功能,提供一個無限的“貨架空間”,實現海量的數字化檔案資源處于可用狀態;另一方面依托強大的運算及信息與交互等功能,提供便捷的檢索方法、實時的在線瀏覽、友好的用戶互動體驗,使海量的數字化檔案資源處于易用狀態。用戶能看的越多,感興趣的就越多。當沖破傳統的、煩瑣的檔案查閱限制,面向極其高效、便捷的搜索與利用方式時,檔案意識和需求都將得到進一步的激發,檔案的價值也將在共享中,實現最大化。
(三)依托新媒體,讓檔案走進大眾日常隨著互聯網應用的深入,“三微一端”(微博、微信、微視頻和客戶端)逐漸成為人們必不可少的信息獲取、和共享交流的平臺。加強檔案信息資源的開發集成,將這些新媒體用戶范圍廣、傳播途徑多、成本低廉等的相關優勢,與檔案信息資源豐富、內容真實可靠等資源優勢強強聯合。“立足自身館藏資源,發揮集體智慧,在實踐中明確自身定位,清楚自己的功能、性質以及服務對象,結合自身實際,開設有特色的個性化欄目,面向公眾提供服務。”[11]針對當前用戶偏好圖文并茂、短小精煉、更新及時等的信息獲取習慣,相關檔案部門要對平臺進行及時的更新,盡可能地呈現更多的內容;同時支持檢索、訂閱與在線咨詢,確保在用戶需要時能夠及時提供相關信息和服務;鼓勵用戶通過客觀的點評、討論、注釋說明、補充、轉載等方式進行二次傳播,擴大受眾面,增加信息流動性和交互性;依托大眾常用的新媒體平臺,讓檔案盡可能地走進大眾日常。
(四)做好安全、保密工作,堅守檔案工作底線安全、保密是檔案工作的底線之一。開放和共享是在安全、保密基礎上的、有條件的開放和共享。處理好兩者的關系,不僅需要國家層面、各級檔案機構層面的相關立法與政策細則,加之軟硬件的防護,更需要與個人征信相結合,充分利用“互聯網+信用”所建立起來的完善、可靠的互聯網誠信體系。用戶的檔案利用情況既受個人征信情況影響,又被納入到個人征信體系中去,以加強“互聯網+檔案利用服務”環境下,檔案信息的安全、保密。不論檔案內涵、外延以及檔案的傳播交互形式如何變化,其作為真實的歷史記錄的本質始終不變。這是檔案信息區別于網絡數據的真假難辨、泛濫成災最大的優勢和核心競爭力。
參考文獻:
[1]阿里研究院.互聯網+從IT到DT[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6.
[2]王協舟,王露露.“互聯網+”時代檔案工作改革的幾點思考[J].檔案學通訊,2016(5):96.
[3]林杰.面向互聯網+時代的檔案信息公共服務[J].山西檔案,2016(1):43.
[4]吳曉堯.信息獲取的變遷及信息獲取能力的培養[J].圖書館理論與實踐,2007(3):48.
[5]阿里研究院.互聯網+從IT到DT[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5:30.
[6]黃存勛.走向公開:創新檔案利用服務機制的最佳切入點[J].檔案學通訊,2005(1):47.
[7]沙洲.“互聯網+”環境下我國電子文件服務方式變革研究[J].北京檔案,2018(5):17.
[8]王協舟,王露露.“互聯網+”時代檔案工作改革的幾點思考[J].檔案學通訊,2016(5):97.
[9]徐潔.“互聯網+”背景下的智慧檔案服務建設[J].山西檔案,2018(4):58.
[10]夏明輝.“互聯網+”環境下檔案管理模式探析[J].北京檔案,2019(7):38.
[11]倪麗娟,陳陽.“互聯網+”環境下檔案微信建設的Swort分析——基于全國檔案微信公眾號的調查[J].檔案學研究,2017(3):46.
作者:孫沁 單位:中國石化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