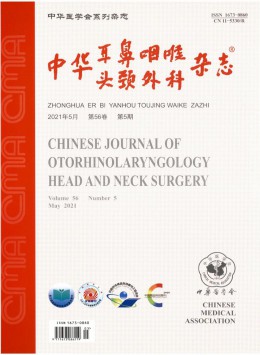咽喉反流性疾病中醫思考認識分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咽喉反流性疾病中醫思考認識分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該文通過探討咽喉反流性疾病喉痹、喉瘖在中醫病因病機、病位、臟腑關系、證型及用藥等方面的不同之處,挖掘咽喉反流性疾病的中醫獨特屬性,認為將咽喉反流性疾病作為中醫獨立病種進行臨床實踐及研究具有必要性及科學性,有利于規范中醫診療,提高臨床療效。
【關鍵詞】咽喉反流性疾病;喉痹;喉瘖;病因病機;病位;臟腑;證型
咽喉反流性疾病(laryngopharyngealrefluxdisease,LPRD)是耳鼻咽喉科常見病及多發病。研究顯示,將近10%的耳鼻咽喉科門診患者及超過50%的聲嘶患者存在咽喉反流[1-2]。快速的生活及工作節奏、不規律的生活方式及飲食習慣,是引起LPRD高發的重要因素,該病嚴重影響人們的健康與生活質量。目前中醫對LPRD的病因病機認識還不夠全面,尚無中醫專屬病名,亦無統一的辨證分型。因LPRD與急性喉痹、慢性喉痹、急性喉瘖、慢性喉瘖、梅核氣在癥狀上有較多相似性,且并無特異性,僅從癥狀上難以區分,故在中醫臨床實踐中常易混淆。隨著LPRD被逐步認識及重視,部分學者提出,LPRD是否有必要從喉痹、喉瘖等中醫病證中剝離出來,單獨成為一個病種。在中西醫結合臨床診療的大背景下,任何一個中醫病種或病證的產生及形成,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一是與之相對應的西醫疾病在病理機制、臨床診斷及治療方法等方面與已知疾病存在特異性;二是具備特有的中醫病因病機、臟腑關系及治療原則、用藥特點等,并在指導中醫臨床實踐中具有較好療效。通過回顧及分析咽喉反流性疾病已有研究,結合本院開展的咽喉反流性疾病中醫證候及證型分布規律研究結果,筆者認為目前LPRD在中西醫臨床中已具備上述基本條件,可作為中醫單獨病種進行臨床實踐及研究。
1LPRD的西醫研究
LPRD指胃內容物反流至食管上括約肌以上部位(包括咽、喉、鼻腔、氣管等部位),造成局部黏膜損傷,表現為咽異物感、咳嗽、聲嘶等癥狀的一類疾病[3]。LPRD的發病機制主要包括:①反流發生的動力學機制:食管下括約肌功能減弱、食管上括約肌功能減弱、體位及其他因素。②咽喉部黏膜損傷機制:咽喉部黏膜缺乏碳酸氫鹽,胃酸-胃蛋白酶對咽喉部黏膜及周圍組織的損傷,炎性因子對咽喉部的損傷。③反流物刺激遠端食管引起迷走神經反射[4]。目前LPRD的診斷方式有反流體征指數量表(RFS)、反流癥狀指數量表(RSI)、質子泵抑制劑診斷性治療、24hMII-PH監測、胃蛋白酶檢測等,治療主要有生活飲食的調節、藥物治療、手術治療。藥物治療為LPRD的主要治療手段,其中質子泵抑制劑(PPI)治療是目前國際上公認的首選方案,其他藥物包括H2受體阻滯劑、促胃腸動力劑、胃黏膜保護劑等。LPRD的診治涉及多學科、多系統,不僅在耳鼻咽喉疾病中,與聲帶小結、聲帶息肉、喉接觸性肉芽腫、聲帶白斑、任克氏水腫、喉狹窄、喉癌、鼻炎、鼻竇炎、假性變應性鼻炎、復發性中耳炎等有密切的關系,也與呼吸科哮喘、特發性肺間質纖維化等,消化科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等,兒科慢性咳嗽、喉痙攣、厭食等有關。2015年版《咽喉反流性疾病診斷與治療專家共識》及解讀中提出,LPRD的診療中存在認識不足或過度診斷等情況,尤其是抑酸治療作為LPRD最常用的治療策略被過度使用,出現藥物耐受,停藥后酸分泌反跳性增多,抑制鈣的吸收而導致骨質疏松,增加艱難梭菌感染的機會和胃癌風險等。由于LPRD癥狀復雜多變、體征輕重不一,而且無特異性,臨床工作中很難實現客觀診斷及病情分級,成為臨床診治工作的難題。
2中醫治療LPRD的臨床療效研究
隨著LPRD被逐漸認識及重視,中醫藥治療LPRD可以發揮中醫辨證的個體化特點,根據不同中醫證型,選擇不同的方劑治療。劉鐵陵等[5]采用單純中醫藥分型論治咽喉反流患者,治療后3個月的顯效率達70.7%。張新玲等[6]采用參苓白術散加減治療咽喉反流作為觀察組,與蘭索拉唑片對照組比較,結果顯示,觀察組總有效率顯著高于對照組,不良反應發生率低于對照組。李瑛等[7]隨機選取200例LPRD患者,對照組給予奧美拉唑治療,觀察組在對照組基礎上聯合院內自擬中藥湯劑治療,結果顯示,觀察組治療總有效率顯著高于對照組,且隨訪3個月復發率明顯低于對照組。可見,在已有研究中,中藥治療LPRD具有療效確切、不良反應小、復發率低等優勢。
3LPRD的病因病機及臟腑相關研究
查閱分析LPRD相關中醫及中西醫文獻,發現該病在病因病機、病位、臟腑相關等方面與喉痹、喉瘖有所不同,而且具有一定規律性及獨特性。李平[8]提出LPRD與肝膽失調關系密切,由于肝膽位置較深,難以直接清晰地觀察,通過中醫問診,可以發掘出很多細微病變,幫助定位脾、胃、肝、膽病變。李斐[9]認為,肝強脾弱、氣機阻滯、升降失常、上漬咽喉是LPRD的主要病機。鐘艷萍等[10]認為,LPRD在中醫中歸于“吞酸”“喉痹”“喉瘖”“嘈雜”及“梅核氣”等疾病范疇,一般認為其發病與邪氣侵擾、情志失調、脾胃虛弱、胃陰不足、酒食所傷、痰氣郁阻等有關,該病的病機為肝失疏泄、肝胃不和、胃氣上逆。陳建能等[11]認為LPRD與脾胃關系密切,病位在咽喉,實責之于脾胃,以中虛氣逆為病機之本,痰火上壅為標,治宜遵循健脾化痰、降氣利咽的原則。叢品教授認為,LPRD實證及虛實夾雜患者病程較短,正氣受損不明顯,進一步發展,氣郁日久,脾胃功能逐漸減弱,脾失健運,痰濕、濕熱等病理因素自內而生,故以虛實夾雜證為主;該病后期以虛證為主,久病失調,正氣損傷,機體生理功能下降,抗反流能力下降,黏膜修復能力下降[12]。所以,在治療LPRD時,早期應以疏肝、解郁、清熱為主,中期應健脾益氣兼以祛邪,晚期則以補益脾胃為主。從上述研究可見,LPRD病因病機主要有以下幾方面:①飲食不節,損傷脾胃,運化失職,或氣血津液生化乏源,氣血虧虛,咽喉失養;②脾胃虛弱,內生痰濕,嗜食辛辣厚味酒恣,濕熱內生,痰熱互結,上犯咽喉;③情志不暢,肝郁脾虛,氣機失調,胃氣上逆,滯塞咽喉。咽司吞咽,下接食管,直貫于胃,咽是水谷入胃的必經之路;胃為水谷之海,主受納及腐熟水谷;脾主運化水谷精微。三者同屬一門,咽與脾胃在水谷的受納、消化與輸布上,構成了三者關系的軸心。咽主地氣,與脾胃相通,為脾胃之候[13]。該病病位在咽喉,與胃、食道密切相關,病變臟腑在肝、脾、胃,治則以疏肝健脾、和胃降逆為主。
4LPRD中醫證型研究回顧
中醫辨證施治,證型是其核心。目前中醫對LPRD的病因病機認識還不夠全面,證候發生、發展、轉歸的規律,以及證候與不同因素之間的關系有待進一步完善。國內已有學者對LPRD中醫證型及用藥規律進行了有效的探索及研究。鐘秀婷[14]調查195例LPRD患者,共得出7種常見的中醫證型,其中以肝胃不和證及肝郁脾虛證為多,其次為脾胃虛弱證、肝胃郁熱證、痰氣交阻證,胃陰虧虛證及氣滯血瘀證相對少見。李平[8]將LPRD中醫證型歸納為5個:肝脾不和、氣郁痰阻、肝火犯胃、濕阻中焦、脾胃濕熱及胃陰虧虛,分別以半夏厚樸湯、丹梔逍遙散合左金丸、三仁湯合半夏厚樸湯、甘露消毒丹、沙參麥冬湯為主方進行加減治療。蔡燕文等[15]歸納LPRD的3個中醫證型,分別是氣滯痰凝、肺胃濕熱及肺胃陰虛,分別以半夏厚樸湯、甘露消毒丹及沙參麥冬湯作為主方進行加減治療。劉鐵陵等[5]收集近年來臨床中有慢性聲嘶、咽異物感、咽喉燒灼感、咽喉部隱痛、頻繁清嗓、慢性咳嗽、吞咽困難及痰液增多或咽喉干燥等癥狀,并經纖維鼻咽喉鏡檢查證實有喉炎存在,懷疑與咽喉反流有關的咽喉炎患者,根據其主癥及兼癥分為氣滯痰凝、肺胃濕熱、肺胃陰虛3種證型,分別給予半夏厚樸湯、甘露消毒丹、沙參麥冬湯為主方進行加減治療。
5LPRD中醫證候及證型分布規律研究
深圳市中醫院耳鼻喉科年門診量超10萬,其中LPRD患者在咽喉疾病患病人群中占近1/3。筆者選擇深圳市中醫院門診初診為喉痹、喉瘖的204例患者,其中男98例,女106例;年齡19~77歲,平均38歲;病程最短2d,最長20年;參考《咽喉反流性疾病診斷與治療專家共識2015》,RSI評分>13分和/或RFS評分>7分者做出LPRD初步診斷。204例患者中,RSI評分203例,RFS評分110例,RSI評分>13分88例,RFS評分>7分52例,RSI評分>13分且RFS評分>7分18例。統計結果如下:①中醫證型分布(排名前5位):88例RSI評分>13分患者中,證型以濕熱蘊脾證及胃熱熾盛證為多,依次為19例(22%)和15例(17%),其次為肝郁脾虛證、脾虛濕盛證、肝胃不和證,依次為9例(10%)、9例(10%)、9例(10%)。52例RFS評分>7分患者中,證型以濕熱蘊脾證、肝郁脾虛證為多,依次為11例(21%)和9例(17%),其次為胃熱熾盛證、肝胃不和證、脾虛濕盛證,依次為5例(10%)、4例(8%)、3例(6%)。18例RSI評分>13分且RFS評分>7分患者中,證型分布前3位分別是濕熱蘊脾證、肝郁脾虛證、肝胃不和證,依次為5例(28%)、3例(17%)、2例(11%)。②中醫證候分布(排名前5位):88例RSI評分>13分患者癥狀描述,以咽部異物感、咽干、咽癢、咳嗽、痰多癥狀多見。52例RFS評分>7分患者與18例RSI評分>13分且RFS評分>7分患者癥狀描述,以咽部異物感、咽干、咽癢、咳嗽、聲嘶癥狀多見,與RSI基本一致。通過對204例LPRD患者的中醫證型進行初步分析,其中以濕熱蘊脾、肝郁脾虛、胃熱熾盛、肝胃不和、脾虛濕盛5個證型較為多見,與國內研究基本一致。但與《中醫耳鼻咽喉科學》中喉痹、喉瘖、喉咳的證型特點有明顯不同[16],說明LPRD在中醫證型上有其獨特性。雖然LPRD在證候上與上述疾病無特異性,但仍具有一定規律性,主要以咽部異物感、咽干、咽癢、咳嗽、聲嘶癥狀多見。
6小結
綜上所述,LPRD與喉痹、喉瘖比較,在病因病機、病位、臟腑關系及治療原則、方藥等方面存在特異性,且已在臨床實踐中得到療效驗證,因此將LPRD作為中醫單獨病種有其必要性和科學性。同時我們應該深刻認識到,在西醫對LPRD的發病機制、診斷方法及治療仍存在一定爭議之際,LPRD的中醫臨床診療的規范化、標準化研究應有緊迫性。在疾病臨床診療及研究工作中,往往是一個西醫病種的產生直到臨床規范化應用及推廣后,中醫才開始進行相關臨床及科研工作,導致研究進展相對滯后。因此,借助現代醫學技術,開展LPRD中醫病名、病因病機、證候、證型、治療原則、方藥等規范化、標準化研究,更好地發揮中醫藥在LPRD臨床診療中的作用及優勢,造福廣大患者。
作者:禤達科 劉元獻 李許娜 郭賽 葉美婷 單位:廣東省深圳市中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