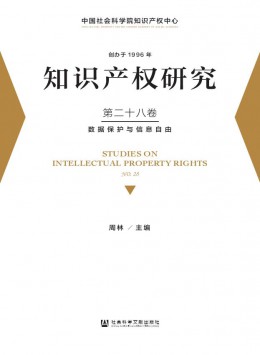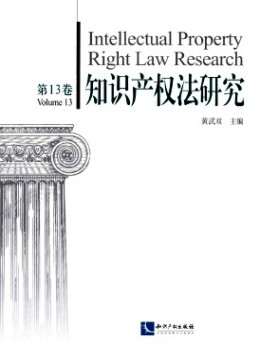談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制度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談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制度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本文提出國內知識產權損害賠償機制要基于實體法、程序法與對應配套機制三個維度展開健全。基于實體法層面,應該優化知識產權損害賠償方式的法律位序與適用關聯性,建立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付標準、取締契合損害賠付方式的法律位序界定等,同時明確所對應的判賠倍數的程度。基于程序法層面,制定出在知識產權損害賠付訴訟證據匯集環節確定訴訟證據公布準則及其對應的保全準則[1];在訴訟庭審環節中確定舉證妨礙準則與減少證明規范的健全意見。在對應配套機制層面,應該重點呈現出知識產權損害賠付司法方針的引導效應;加強知識產權案例引導機制的司法典型效應,并在明確損害賠付額度時運用知識產權損害賠付評價體制與司法會計體制[1]。
關鍵詞: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制度研究
一、研究背景及意義
伴隨《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的落實,以及《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國務院關于新形勢下加快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若干意見》等知識產權大國戰略的驅動和落實[1],知識產權體制系統的建設和體現影響逐漸獲得了政府的高度重視,這對建立、強化國家經濟、科技以及文化建設的關鍵;知識產權通過私權客體的整體認知的形式已經被廣泛接受,其管理效果也逐漸凸顯,社會大眾的知識產權理念獲得大幅度提高。加強知識產權保障應該看作是保障權利人正當權益的核心方式,特別是呈現在侵權判定和損害賠付這兩方面。需要重視的是,國內學術領域和司法實務領域一直注重執行活動屬性的界定,但極少把探究核心聚焦于損害賠付中,更不用說知識產權這類新式損害賠付問題。探究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機制的理論價值集中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基于系統探究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機制,繼而探究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機制的系統建立和構成;二是梳理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本體機制的基本理論,特別呈現在機制職能和基礎準則兩方面;三是明確知識產權損害賠付契合準則和明確損害賠付金額的判定方式。本文中提出,系統探究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機制的實證價值便于引導法官制定出契合司法公平的判定與保障權利人的正當權益。
二、我國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制度使用現狀與問題
(一)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制度適用現狀1.法定賠償方式的適用呈泛化態勢旨在明確把握國內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方法的應用狀況,筆者在“OpenLaw裁判文書搜索”網站中匯集了國內2013年1月1日到2018年9月13日范圍的知識產權侵害損害賠付判定材料為探究樣例,總共有2842份。筆者在統計環節中去除了4種無線案例,其中有系列案例、裁判不具備侵權條件案例、超過規定訴訟周期駁回原告訴訟案例、無過錯不賠付經濟損害只提供合理費用案例[1],最后得到有效裁判樣例1769份。通過上述案例,研究了當前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方式的應用狀況;另外,旨在確保實踐信息的探究結論具備說服力,引用了我國非常典型的實踐信息進行佐證。2.判賠金額與訴請金額間差距較大國內目前的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機制還沒有體現出立法人和社會參與者期待的機制職能,在實際運用環節中產生了相應的偏移,導致機制運營環節中表現出和填平救濟準則相違背的機制職能異化情況,具體裁判金額無法彌補權利者獲得的損害。3.緣于“舉證難”致使審理周期較長權利人獲知市場里面產生知識產權活動,繼而通過法院要求司法救濟,其原本意愿是基于司法方式快速制止侵權活動、賠付獲取到的權益損害[1]。但實際上權利人第一時間維護得到的結果或許會較差,對應的核心因素是國內現階段知識產權侵權損失賠付的“裁判時間長”,經常會使權利人無法基于司法方式得到對應的價值,導致權利人市場占有率降低,減少其對司法救濟的期許和評估。
(二)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制度適用存在的問題1.缺失制度特有的基礎理論指引知識產權損害賠付基本理論具備關鍵的“提綱挈領”效應,直接決定著立法群體、司法群體、探究群體、實務群體對損害賠付在知識產權范疇中的認知和支出[1]。本文研究的基礎理論,不會重點突出損害賠付的基本定義,只針對知識產權損害領域在立法闡述學的表述下作出統一的解讀。實際上,國內推行的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機制來源于傳統民事,導致知識產權損害賠付的機制職能與基礎準則無法很好地處理知識產權損害賠付的實際問題[1],對應的能呈現和想要呈現職能間擁有很大的差距;事實上,產生這類情況的因素并不是“實然和應然”間的差距,是基礎理論和實際問題產生的“錯位”而形成的[1]。2.賠償方式未能彰示其工具價值國內法院裁定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付案件集中于運用法定賠付方法,其他三類損害賠付方法被實際運用次數較低。但是,法定賠付方法普遍運用的實際現象一直被學理界和實務界所質疑。換句話說,大頻率運用法定賠付一方面難以降低國內知識產權侵權情況增長的趨勢,另一方面也難以呈現出其他三類賠付模式的科學化和優勢,同時導致國內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付司法效應的總體評估受損。換句話來說,國內目前推行的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付方法還沒有體現出立法群體所期望的實際價值。必然要承認的是,導致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方法“工具失靈”的情況并不可能都追究于法官,因為這是國內知識產權市場沒有健全、權利人消極舉證、社會對待知識產權意識缺乏等原因導致的[1]。3.法定賠償適用的裁量空間過大國內現階段司法標準還沒建立起具體的、能夠參照的判定準則,只是有確定損害賠付額度的考慮要素,法官必然要在比較寬泛的賠付單位中確定較為平衡的額度值。在運用法定賠付裁定損害賠付金額時,法官通常會按照自身的主觀意愿作出選擇,在大量的判定材料中沒有有效呈現出怎樣界定損害賠付金額,基本上是運用簡略詞匯進行概括,導致當事者無法認同法院制定的最后賠付金額,其實這降低了國內司法的權威作用。所以,法院在運用法定賠付模式展開裁定時,務必要呈現出司法的智慧與價值,在明確損害賠付金額時給予全面的說明,并非旨在提升訴訟效率而忽略了司法公正的價值思想。4.缺乏專門的知識產權證據規則導致這種問題的核心因素是因為知識產權客體的非物質化特點所形成的,在實際案件中[1],知識產權損害賠付訴訟證據呈現出無形化、專業化、隱蔽化、有限化等特點。另外,國內法律推行把知識產權侵權看作是普通侵權范圍,繼而在侵權損害賠付職業證明維度運用普通民事訴訟的證據準則。然而,按照國內推行的民事訴訟證據準則,肯定又提升了權利人收集證據、舉證、證據證明的難度。換句話說,一般民事訴訟證據準則難以有效處理知識產權損害賠付證據采集和舉證證明,其實是無法平衡訴訟當事者間的訴訟定位。實際上,國內缺少單獨的知識產權損害賠付證據標準是導致其損害賠付裁定時間長、賠付金額少、泛化運用法定賠付等弊病的核心因素。
三、我國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制度的完善對策
(一)實體法維度的完善對策第一,修正知識產權損害賠償方式的法定位階及適用關系[1]。實際上,國內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方法適用維度的標準塑造始終被學理界和實務界質疑的弊病,對應形成的消極作用直接干擾了國內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付的司法質量。所以,應當優化國內目前現行的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方法的法定次序限定,并確定國內多樣知識產權損害賠付形式的適用關聯性,從而能夠改善知識產權損害賠付的司法效應[1]。同時,建立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付的遵守準則。取締適用損害賠付方法的法定次序限定。優化所有損害賠付方法間的各自排斥關聯性。第二,優化我國知識產權許可使用費賠償規則的立法規范。首先,反思國內現行“許可運用費賠付準則”的組成要素、核算基準等標準化成分;其次,制定出改善國內知識產權許可運用費賠付標準的優化意見,提升所有知識產權單行法里許可費賠付的許可費準則與取消以許可費的“倍數”界定損害賠付金額的限定兩個調整建議。優化意見事實上是參照國際上先進國家立法經驗的探究信息,提升所有知識產權單行法中許可費賠付的許可費標準,取消以許可費的“倍數”界定損害賠付金額。第三,調整我國知識產權法定賠償的賠償幅度與規范內容。目前,知識產權法定賠付方法在國內司法實證中體現出了關鍵的適用價值。所以,法定賠付方法的合理性會直接作用到法規標準的適用效應中。反觀當前推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修訂草案送審稿)》《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修訂草案(送審稿)》,上述立法判定于立法草案針對“法定賠付”的界定信息并不一致,并不便于國內知識產權法定賠付的一體化司法適用。要特別說明的是,筆者沒有否決所有知識產權損害賠付中法定賠付的特別化,只是認為應該優化法定賠付的界定程度與規范范圍,從而利于法律適用。第四,構建我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適用的基本要件[1]。實際上,立法草案和既有制定法在同一問題中產生了較高差別性呈現的狀況,其核心原因是所有單位法草案的編撰者出于對標準認知和各個維度的利益而考慮的。或許,法院對各個權利種類的裁判金額或許存在差別,但在適用損害賠付方法間應該保持一致標準化。換句話說,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機制一方面要認同各個權利種類知識產權的實際特征,另一方面在知識產權懲治化賠付適用準則維度一體化。本文側重于論述知識產權懲治化賠付的契合標準和計算標準的立法意見和改善意見。
(二)程序法維度的完善對策第一,完善知識產權損害賠償訴訟證據規則的必要性[1]。知識產權是典型的私權,即便對應的知識產權損害賠付證據特點明顯,探其實質依然是民事訴訟范圍,依然要恪守民事訴訟流程的常規證據準則。然而,既有的民事訴訟證據準則與關于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案件證據的法規限定與司法解釋依然形成了諸多較為模糊的問題,并不便于合理進行知識產權損害賠付訴訟。國內知識產權損害賠付證據采集和保全準則并不標準,知識產權損害賠付舉證職責和規范配置也不科學。第二,優化知識產權損害賠償的證據收集與保全規則。由于知識產權損害賠付證據的特別性與證據對案件判定的關鍵性,國內立法群體和司法群體一定要通過“體制創新”的模式來解除知識產權損害賠付中無法獲取“權利人損失”或是“侵權人獲利”證據的司法現象。所以,國內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案件機制的證據采集和保全環節應當進行合理創新,圍繞現行民事訴訟法的普通標準進行合理優化,從而匹配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案件證據的特別化。第三,調整知識產權損害賠償的證明責任與證明標準[1]。知產損害賠償訴訟案件仍存在收集證據材料不易的情況,以致知產侵權損害賠償的證據材料不時出現證據間因果鏈條不完善、證據材料真實性不足,數額認定難達“高度蓋然性”的民事訴訟標準。溯其根源,導致知識產權損害賠償訴訟證據事實與證明標準不匹配的實際原因,是由于證據距離、取證難度與證據能力等問題所致。一般情況下,知識產權侵權損害案件是屬于民事案件的“子種類”應該恪守民事案件的常規化界定,只是因為知識產權損害賠付證據的特別化,才要圍繞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案件的證明職責和證明準則標準進行合理創新和優化[1]。繼而合理調節權利人的證據證明壓力,降低了所采集的證據事實和損害賠付事實間的差距。
(三)相關配套制度的完善對策第一,發揮我國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司法政策的指引作用[1]。我國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機制和司法方針具備高契合度。司法方針即使不具有“法院”的定位,但是在實證中依然體現出了關鍵的宏觀引導與導向價值。所以,國內必須要依托于司法方針引導、標準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機制解決在司法環節中的問題。第二,強化我國知識產權案例指導制度的司法示范作用。最高人民法院指導化訴訟體制的建立環節是完成統一司法共同認知與完成“同案同判”的公正目標而展開決策的環節,其體現為“目標—方式”的運營架構。一是國內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指導化訴訟的應然價值和現狀;二是完成國內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指導化訴訟引導價值的核心點;三是把“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歸入指導化訴訟的覆蓋范疇;四是判定宗旨應該明確損害賠付機制的理論價值和適用準則。第三,引入知識產權損害賠償評估機制及司法會計制度。由于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方案中“具體損失”“侵權收益”核算對專業能力要求較高,所以最高人民法院應當注重在損害賠付案件中結合專業的評價、堅定機構公布專業報告信息,方便法院進行賠付金額的界定,繼而出具科學的界定結果。合理建立知識產權價值評價體制,合理建立知識產權司法會計體制。
四、結語
本文對國內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機制要圍繞實體法、程序法與對應配套機制三個方面展開研究。基于實體法層面,應該優化知識產權損害賠償方式的法律位序與適用關聯性,建立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付標準、取締契合損害賠付方式的法律位序界定等;刪掉許可運用費科學倍數里的“倍數”的法律措辭,通過“合理許可運用費”的賠付方法進行替換[1];合理調整法定賠付的最小判定界定和最高單位,一體化“法定賠償”的法律措辭;基于程序法層面,制定出在知識產權損害賠付訴訟證據匯集環節確定訴訟證據公布準則及其對應的保全準則;在訴訟庭審環節中確定舉證妨礙準則與減少證明規范的健全意見[1]。在對應配套機制層面,應該重點呈現出知識產權損害賠付司法方針的引導效應;加強知識產權案例引導機制的司法典型效應[1],并在明確損害賠付額度時運用知識產權損害賠付評價體制與司法會計體制。基于以上健全方略的落實,推動知識產權損害賠付機制體現出最高的立法效應與社會效應。
參考文獻
[1]董凡.知識產權損害賠償制度研究[D].華南理工大學博士論文,2019.
作者:劉友誼 單位:北京大成(南昌)律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