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chuàng)造社戲劇藝術(shù)論文
前言:想要寫(xiě)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創(chuàng)造社戲劇藝術(shù)論文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lái)靈感和參考,敬請(qǐng)閱讀。

一、創(chuàng)造社諸君初赴日本的時(shí)間
基本集中于20世紀(jì)第一個(gè)十年,正是求知若渴的青年學(xué)子,資質(zhì)聰穎,意氣風(fēng)發(fā),甚至有些年少輕狂。又恰逢日本近代史上第二次民主思潮,以及由此而彰顯的時(shí)代新氣象,對(duì)天才的期許和崇尚、對(duì)個(gè)性和創(chuàng)造力的謳歌、對(duì)人性的呼喚與伸張,這種開(kāi)放的時(shí)代氛圍令來(lái)自封建傳統(tǒng)國(guó)度的創(chuàng)造社諸君,滿(mǎn)心激蕩、心馳神往。正如郁達(dá)夫所描述的,“兩性解放的新時(shí)代,早就在東京的上流社會(huì)———尤其是智識(shí)階層,學(xué)生群眾———里到來(lái)了。”置身在這樣的社會(huì)氛圍,創(chuàng)造社諸君也將目光投向男女戀愛(ài)、婚姻等兩性話(huà)題,再加上自身的性格和心態(tài),以?xún)尚詾橹鞯膭?chuàng)作占他們作品總量的大成。他們以大正時(shí)期的女性解放熱潮為背景和參照,讓他們所熟悉的中國(guó)女性成為作品的主角,批判的矛頭對(duì)準(zhǔn)她們被壓抑的靈魂和被遮蔽的命運(yùn)。在對(duì)光明和希冀的熱切渴望中,因時(shí)代、社會(huì)、個(gè)人等因素而難以調(diào)和的“靈肉分裂之苦惱”成為包括戲劇界在內(nèi)的日本文壇頗感棘手的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日本惠特曼研究權(quán)威有島武郎就在《出生的煩惱》、《死及其前后》等作品中寫(xiě)出靈肉分裂的深刻痛苦。這種矛盾糾結(jié)的苦惱情緒引起了創(chuàng)造社諸君的共鳴,他們?cè)谠缙趧?chuàng)作中也表現(xiàn)出“個(gè)人的靈活與肉體的斗爭(zhēng)”。
田漢在談?wù)撃且浑A段的創(chuàng)作時(shí)說(shuō):“無(wú)論創(chuàng)作劇,還是翻譯劇,都有一種共通的‘靈肉生活之苦惱’的情調(diào)。”《咖啡店之一夜》中的林澤奇,不知自己是“向靈的好,還是向肉的好”,他的生活“是一種東偏西倒的生活”,“靈-肉;肉-靈;成了這么一種搖擺狀態(tài),一刻子也安定不了”。《靈光》中的張德芬,也因婚姻問(wèn)題上“靈肉的交戰(zhàn)”而感到難以擺脫的“煩悶”。同時(shí),日本新劇在觀照人類(lèi)情感命題的同時(shí),還有很多題材直接源于日本民族的現(xiàn)實(shí)生活,精神上更契合日本的民族文化心理。取材于現(xiàn)實(shí)生活的創(chuàng)作,為當(dāng)時(shí)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提供了新的方向,即如何將文學(xué)的藝術(shù)功能與社會(huì)功能結(jié)合起來(lái)。一向標(biāo)榜藝術(shù)至上的創(chuàng)造社諸君在婚戀題材之外也開(kāi)始嘗試著用戲劇形式表現(xiàn)工農(nóng)大眾的生活狀態(tài),如田漢的《午飯之后》。還有一些作品,將戲劇的眼光投向下層民眾的苦痛和對(duì)社會(huì)黑暗的揭露上,在一定程度上增強(qiáng)了戲劇反映現(xiàn)實(shí)生活的能力。如郁達(dá)夫的《孤獨(dú)者的悲哀》、張資平的《軍用票》、成仿吾的《歡迎會(huì)》等。然而,日本文學(xué)畢竟是有別于中國(guó)的文學(xué),因此,創(chuàng)造社諸君在接受日本戲劇的過(guò)程中,不可避免地會(huì)受到“中國(guó)因素”的制約。這不僅僅是因?yàn)樗麄兊奈膶W(xué)啟蒙是在中國(guó)本土完成,更在于中國(guó)文化在他們心理和情感塑造上所占有的“先機(jī)”。這一點(diǎn),我們可以從審美情調(diào)的角度進(jìn)行理解。日本新劇非常重視抒情,這種抒情不是郭沫若《女神》中撼天動(dòng)地、響徹云霄的無(wú)節(jié)制的情感宣泄,而是承襲了日本“物哀”的美學(xué)精神。“物哀”是日本傳統(tǒng)的文學(xué)觀念和美學(xué)思想,講究“真情流露”,即情感主觀接觸外界事物時(shí),自然而然或情不自禁地產(chǎn)生的幽深玄靜的情感。“物哀”的美學(xué)傳統(tǒng)不僅深深根植于日本文學(xué),而且支配著日本民眾精神生活的諸多層面。創(chuàng)造社諸君敏感多情的心性、內(nèi)在的藝術(shù)修養(yǎng)、以及中國(guó)漢民族與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相通性,使得他們更容易領(lǐng)會(huì)“物哀”的美學(xué)精神,從而在創(chuàng)作中與之呼應(yīng),呈現(xiàn)出深沉淡泊的美學(xué)風(fēng)格。
二、大正時(shí)期的日本文學(xué)界異常活躍
西方自文藝復(fù)興以來(lái)的各個(gè)時(shí)期的文藝思潮和文學(xué)流派在這一時(shí)段集體涌入,對(duì)日本文壇造成極大的沖擊并呈現(xiàn)出活躍而紛繁的局面。創(chuàng)造社諸君在日本所受的影響,除了日本本國(guó)文化和文學(xué)的影響外,還有以日本為媒介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影響。“日本在中國(guó)文學(xué)的現(xiàn)代化過(guò)程中比任何的國(guó)家都更為重要,它發(fā)揮了雙重的作用,既是啟蒙的導(dǎo)師,又是輸入西方文學(xué)的中間人。”這正是“日本機(jī)制”的第一重機(jī)制———環(huán)境機(jī)制之外,創(chuàng)造社戲劇藝術(shù)中“日本機(jī)制”所發(fā)揮的第二重功能———中介機(jī)制,或稱(chēng)媒介機(jī)制。自明治第二個(gè)十年之始,一股翻譯文學(xué)的風(fēng)潮開(kāi)始在日本文壇盛行,“在這個(gè)時(shí)期里,翻譯和介紹過(guò)來(lái)的有英國(guó)的莎士比亞、李頓、迪斯雷利和司各脫的作品,法國(guó)方面的有凡爾納、費(fèi)爾隆、大仲馬和雨果,還有俄國(guó)的以虛無(wú)黨的活動(dòng)為中心的虛無(wú)黨文學(xué)等等。”許多的日本作家和學(xué)者致力于翻譯的再創(chuàng)造過(guò)程。正是得益于這樣濃郁而開(kāi)放的文化氛圍,不僅為創(chuàng)造社諸君打開(kāi)了接觸西方文學(xué)的窗口,同時(shí)因日本文化界的推介,讓他們?cè)谖鞣轿膶W(xué)的選擇上獲得某種導(dǎo)向性的引領(lǐng)作用。如他們所推崇的歌德、盧梭、尼采、惠特曼、泰戈?duì)枴⒉ㄌ厝R爾等,都是通過(guò)日本文壇的推介而進(jìn)一步接觸的。這樣,創(chuàng)造社諸君通過(guò)日本這個(gè)窗口間接地向世界文學(xué)潮流靠攏。歷史劇是五四時(shí)期很受作者青睞的戲劇類(lèi)型,創(chuàng)造社諸君中郭沫若和王獨(dú)清都有歷史劇存世。他們的歷史劇帶有鮮明的自我色彩,借“古事古詩(shī)”以表達(dá)個(gè)人對(duì)“今事今人”的思考。郭沫若在創(chuàng)作戲劇之前,曾閱讀莎士比亞、歌德、席勒、泰戈?duì)柕热说淖髌贰K麑⑹穭》譃閮深?lèi),“一種是把自己去替古人說(shuō)話(huà),如莎士比亞的史劇之類(lèi),還有一種是借古人來(lái)說(shuō)自己的話(huà),譬如歌德的《浮士德》之類(lèi)。”并強(qiáng)調(diào)自己的史劇觀更多地來(lái)自歌德浪漫主義史劇觀的影響,目的是“借古人的皮毛說(shuō)自己的話(huà)”,“借古人的骸骨來(lái),另行吹噓些生命進(jìn)去”。王昭君不再是歷史中那個(gè)被迫遠(yuǎn)嫁的無(wú)法掌握自身命運(yùn)的悲情女子,而化身成一個(gè)封建斗士和理想女性。王獨(dú)清創(chuàng)作歷史劇的興趣也不僅限于歷史事實(shí)本身,他要“把這中間的主要人從那已死的形體中復(fù)活了起來(lái),投以特殊的新鮮的生命”,“用我的清熱把生命的水力吹進(jìn)它們的身中,使它們成為我的新的建筑的新的原料。”
楊貴妃不再是紅顏禍水的形象,而是以“甘為民族甘為自由犧牲的人物”。正是這種個(gè)人對(duì)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主觀感受,這種將個(gè)人抒發(fā)融于史劇創(chuàng)作的方法,形成了創(chuàng)造社史劇創(chuàng)作中反傳統(tǒng)的浪漫主義風(fēng)格。在此還要提及的是創(chuàng)造社對(duì)“新浪漫主義”的美學(xué)追求。日本文論家廚川白村在《近代文學(xué)十講》中對(duì)新浪漫主義的源流、成因、特征的闡述,極大地影響了創(chuàng)造社諸君新浪漫主義文藝觀的形成。田漢在寫(xiě)給郭沫若的信中談及自己是如何通過(guò)戲劇去體驗(yàn)新浪漫主義的,“我看新羅曼主義的劇目從《沉鐘》起,至今羅登德蘭海因利希的印象還是活潑潑的留著,同時(shí)一股神秘的活力也從那時(shí)起在我的內(nèi)部生命的川內(nèi)流動(dòng)著。”他將寫(xiě)于1920年的《梵珴璘和薔薇》標(biāo)注為“一部新浪漫主義的四幕悲劇”。陶晶孫自稱(chēng)是“一直到底寫(xiě)新羅曼主義作品者”。他的劇作《黑衣人》是用日文寫(xiě)成的作品,后被譯成中文發(fā)表于《創(chuàng)造季刊》。劇中的“黑衣人”痛恨毫無(wú)公道可言的社會(huì),手握武器,卻無(wú)所適從。社會(huì)在劇中被描繪成一個(gè)“無(wú)物之陣”,無(wú)論采用什么方法與之對(duì)抗,依然難逃宿命。“在這個(gè)很短的劇本里,他描寫(xiě)孤獨(dú),寂寞,恐怖和瘋狂,描寫(xiě)在特殊時(shí)候的凄涼和失望的,而仍然含著神秘的美麗的向往的心情是值得贊賞的。里面的情調(diào),非常緊張而且靜默,而從這緊張與靜默中傳出美和理想和現(xiàn)實(shí)底幻滅。”他的另一劇作《尼庵》則表現(xiàn)的是人物在夢(mèng)境與現(xiàn)實(shí)沖突中的迷惘與覺(jué)醒。兄長(zhǎng)苦勸萬(wàn)念俱灰的妹妹,妹妹雖然聽(tīng)從兄長(zhǎng)的勸告從尼庵中走出,卻不愿再入塵世的紛擾,“寧肯進(jìn)第二的尼庵”———湖水之中。兩部劇作都是以新浪漫主義手法造就,劇作手法之新穎,反映之深刻,無(wú)不映射出作者的藝術(shù)積累,以及對(duì)所學(xué)創(chuàng)作手法的自覺(jué)運(yùn)用。確認(rèn)地說(shuō),創(chuàng)造社諸君接受的西方文化,是經(jīng)由日本“過(guò)濾”或“中轉(zhuǎn)”后的西方文化,不論這個(gè)過(guò)程中存在怎樣的轉(zhuǎn)換過(guò)程,其實(shí)現(xiàn)的重要途徑正得益于“翻譯”的手段。許多的日本名家,佐藤春夫、谷崎潤(rùn)一郎、森歐外等在創(chuàng)作之余都極為重視對(duì)以西方文學(xué)為主的外國(guó)文學(xué)的翻譯和推介。創(chuàng)造社諸君目睹了日本文壇對(duì)西方文藝的積極譯介從而對(duì)本國(guó)文壇所產(chǎn)生的積極影響和促進(jìn)作用,也開(kāi)始重視“翻譯”的功效,身體力行地做了大量的翻譯工作。他們通過(guò)“日本之橋”完成了離開(kāi)第一文化語(yǔ)境(母語(yǔ)文化語(yǔ)境)后,思想觀念和文學(xué)修養(yǎng)在第二文化語(yǔ)境中的二次積淀和儲(chǔ)備,郭沫若就曾翻譯過(guò)歌德的重要詩(shī)篇、小說(shuō)及戲劇。田漢也“目睹了日本話(huà)劇家接受外來(lái)話(huà)劇樣式的經(jīng)歷和艱辛”,非常重視譯介在文學(xué)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的促進(jìn)和啟發(fā)作用,他出版翻譯劇本15部、改編外國(guó)劇本原著5部,還發(fā)表外國(guó)文學(xué)評(píng)論50余篇。
三、外界因素可以承擔(dān)觸動(dòng)和啟發(fā)的功能
但自我精神的內(nèi)在訴求卻是無(wú)法被替代的。深刻的人生體驗(yàn),是文化環(huán)境、藝術(shù)交流這些外因所不能悉數(shù)詮釋的。只有從這樣的角度,或許才有可能將創(chuàng)造社諸君進(jìn)行獨(dú)立精神創(chuàng)造的過(guò)程給予生動(dòng)描繪。正如王富仁對(duì)文化互動(dòng)的一種描述那樣,“文化經(jīng)過(guò)中國(guó)近、現(xiàn)、當(dāng)代知識(shí)分子的頭腦之后不是像經(jīng)過(guò)傳送帶傳送過(guò)來(lái)的一堆煤一樣沒(méi)有發(fā)生任何變化。他們也不是裝配工,只是把中國(guó)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不同部件裝配成了一架新型的機(jī)器,零件全是固有的。人是有創(chuàng)造性的,任何文化都是一種人的創(chuàng)造物。”筆者在此討論的正是創(chuàng)造社戲劇藝術(shù)中“日本機(jī)制”的第三重———體驗(yàn)機(jī)制。這一機(jī)制也可以概括為“留學(xué)體驗(yàn)”或“海外體驗(yàn)”。這是一種“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作家的生存、發(fā)展、成就以及歷史地位,起到重要作用的留居他國(guó)學(xué)習(xí)的經(jīng)歷,以及這種經(jīng)歷經(jīng)過(guò)學(xué)人個(gè)體特殊的精神轉(zhuǎn)化后所形成的,對(duì)現(xiàn)代作家人生道路和創(chuàng)作領(lǐng)域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一種支援意識(shí)和背景因素。”創(chuàng)造社諸君的留學(xué)體驗(yàn)是以出生國(guó)(中國(guó))為基礎(chǔ)的內(nèi)在知識(shí)、思維、情感,以某一個(gè)外在機(jī)緣(留學(xué))為契機(jī),通過(guò)另一個(gè)文化語(yǔ)境(日本)重新選擇、整合、塑造的精神活動(dòng)過(guò)程,而這個(gè)新的文化語(yǔ)境正是現(xiàn)代生活、現(xiàn)代思維、現(xiàn)代文化的一個(gè)新的傳播地和創(chuàng)造地。初涉異域的創(chuàng)造社諸君,出國(guó)前大多生活在封閉保守的鄉(xiāng)鎮(zhèn),受教的是傳統(tǒng)儒家文化,來(lái)到日本后他們的內(nèi)心無(wú)疑受到一股與既有思想體系全然不同的心靈沖擊。“他們的文章和見(jiàn)解,難免受到留學(xué)所在地時(shí)髦的思想或偏見(jiàn)所感染。”日本社會(huì)的都市化刺激了他們年輕敏銳的神經(jīng),他們流露出對(duì)現(xiàn)代都市、物質(zhì)主義的認(rèn)同和傾心,看時(shí)報(bào)、泡溫泉、觀電影、談戀愛(ài),甚至去酒坊買(mǎi)樂(lè)。郁達(dá)夫、田漢等人就對(duì)作為“日本的風(fēng)俗漸漸歐化的象征”的咖啡館充滿(mǎn)了想象,暗香疏影的咖啡館成為他們?cè)缙趧?chuàng)作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空間設(shè)定。如田漢的劇作《咖啡館之一夜》就是“以咖啡情調(diào)為背景,寫(xiě)由頹廢向奮斗之曙光。”這樣的精神體驗(yàn)已經(jīng)不僅僅是生存空間的變更或者延伸所能簡(jiǎn)單解釋的,而是“從傳統(tǒng)中國(guó)向現(xiàn)代西方的轉(zhuǎn)換中所產(chǎn)生的雙重或多重情感空間、價(jià)值空間、審美空間的對(duì)立轉(zhuǎn)化、矛盾發(fā)展或者自我超越。”內(nèi)心所經(jīng)歷的復(fù)雜的心理體驗(yàn)和精神活動(dòng),就不可避免地讓從“老中國(guó)”走出的創(chuàng)造社諸君時(shí)刻處于一種時(shí)空變換所造成的比對(duì)中。他們直面日本社會(huì)的資本主義化,社會(huì)風(fēng)尚開(kāi)放、現(xiàn)代文明發(fā)展,再反觀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中國(guó),新文化運(yùn)動(dòng)落入低谷、新文化陣營(yíng)已然分化,以及身為被侵略國(guó)子民所受的屈辱和日本軍國(guó)主義、侵略行動(dòng)所造成的民族自尊心的極大傷害。因而,創(chuàng)造社諸君在“日本機(jī)制”下的創(chuàng)作心理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充滿(mǎn)了矛盾的復(fù)雜性。其實(shí),日本文化和文學(xué)對(duì)中國(guó)新文學(xué)的影響遠(yuǎn)在創(chuàng)造社之前。“創(chuàng)造新文學(xué)之一人”的梁?jiǎn)⒊谕砬逦膶W(xué)改良運(yùn)動(dòng)中提出的“文界革命”、“詩(shī)界革命”、“小說(shuō)界革命”就是蒙受日本留學(xué)經(jīng)歷的啟示。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指導(dǎo)者中,陳獨(dú)秀、、魯迅、周作人皆是20世紀(jì)初期的赴日留學(xué)生。
他們?cè)谌毡舅艿降乃枷雴⒌现苯佑绊懥怂麄兓貒?guó)后所引領(lǐng)的中國(guó)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和新文學(xué)思潮。啟蒙思想、自由平等思想、“人的思考”的時(shí)代意識(shí)、國(guó)民創(chuàng)造精神,在日本社會(huì)中備受推崇的新興思想如星星之火,在同時(shí)代的廣大青年學(xué)子間燎原。創(chuàng)造社諸君在赴日前后都與這些新興觀念擦碰出思想的火花。郭沫若在早期歷史劇《三個(gè)叛逆的女性》中,遵循批判的精神擊打封建綱常倫理的腐朽枷鎖,提出女子“三不從”的“新性道德”。郁達(dá)夫感嘆“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gè)人’的發(fā)見(jiàn),以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現(xiàn)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特別是日本的國(guó)民創(chuàng)造精神,既與新文學(xué)所弘揚(yáng)的“創(chuàng)造”精神一致,也與郭沫若所言“脫胎換骨地獨(dú)立自主地開(kāi)始創(chuàng)造”的主張契合,是創(chuàng)造社同人集結(jié)的思想基石,更是創(chuàng)造社結(jié)社的根本精神。另一個(gè)原因則在于,“戲劇藝術(shù)本身的實(shí)踐性決定了中國(guó)的戲劇家不可能‘置身世外’作純文字的陶醉,藝術(shù)的實(shí)踐過(guò)程必然讓他們更多地‘進(jìn)入’到日本當(dāng)下的生存狀態(tài)。與他們頻繁交往的編導(dǎo)、演員與觀眾都是具體的人,頻繁而廣泛的人際交往令他們深入地體察到了生存與心靈的細(xì)微意義,對(duì)于當(dāng)下生存與人類(lèi)(觀眾)精神需要的準(zhǔn)確把握才是戲劇藝術(shù)成功的保證,這一切都構(gòu)成了留日中國(guó)戲劇家重要的戲劇資源,較之于小說(shuō)家的純文學(xué)吸取,為日本戲劇資源包裹的中國(guó)戲劇家有了更為深刻的生存體驗(yàn)。”這正是創(chuàng)造社諸君異域———故國(guó)雙重體驗(yàn)的真實(shí)寫(xiě)照。他們把“人的解放”作了富有個(gè)性色彩的張揚(yáng)與渲染,顯示了獨(dú)特的文化心態(tài)。他們所擴(kuò)張的自我,不再只是擺脫了身心枷鎖的“個(gè)體的人”,而是要讓這“個(gè)體的人”充滿(mǎn)主觀戰(zhàn)斗的激情。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cè)谌樟魧W(xué)期間被日本國(guó)內(nèi)高漲的國(guó)家意識(shí)和民族意識(shí)所感染,也開(kāi)始自覺(jué)地將個(gè)體體驗(yàn)和對(duì)國(guó)家、民族的思考緊密結(jié)合,不再囿于自己狹小的天地和多愁的心緒。有學(xué)者曾將創(chuàng)造社的文學(xué)描述為“青年文學(xué)”,“代表了中國(guó)現(xiàn)代的青年文化和青年文學(xué)的獨(dú)立形態(tài)的形成。”創(chuàng)造社諸君無(wú)疑是20世紀(jì)初期青年群體中的幸運(yùn)兒,他們的青年文學(xué)夢(mèng)孕育且受哺于兩個(gè)不同的國(guó)度———中國(guó)賜予他們最寶貴的生命和情感的最初積累,日本賦予他們更全面的文化養(yǎng)分、更豐厚的生命體驗(yàn)和他們結(jié)社之始就無(wú)比崇尚的先鋒精神與創(chuàng)造使命。文學(xué)創(chuàng)作是一個(gè)復(fù)雜的精神活動(dòng)過(guò)程,是無(wú)法僅靠理論的鋪陳或概念的移植就可以“制造”出爐的,而是創(chuàng)作主體發(fā)自?xún)?nèi)心深處的體驗(yàn)與表。
作者:譚蘇 單位:湖北民族學(xué)院 華中師范大學(xué)
相關(guān)文章閱讀
- 1戲曲演員創(chuàng)造思維的培養(yǎng)
- 2石濤在繪畫(huà)中的創(chuàng)造活動(dòng)
- 3藝術(shù)設(shè)計(jì)中的創(chuàng)造思維探析
- 4探究戲劇對(duì)兒童創(chuàng)造力的影響
- 5影視動(dòng)畫(huà)藝術(shù)的角色創(chuàng)造
- 6兒童美術(shù)創(chuàng)造力保護(hù)與培養(yǎng)途徑
- 7幼兒教育中滲透創(chuàng)造思想
- 8審美鑒賞與創(chuàng)造能力探析
- 9創(chuàng)造進(jìn)攻角度拳擊步伐訓(xùn)練淺析
- 10美術(shù)欣賞活動(dòng)中幼兒創(chuàng)造力培養(yǎng)
相關(guān)期刊推薦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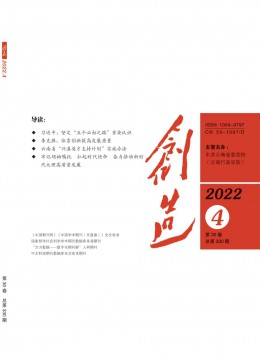
創(chuàng)造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學(xué)苑創(chuàng)造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社科雙效期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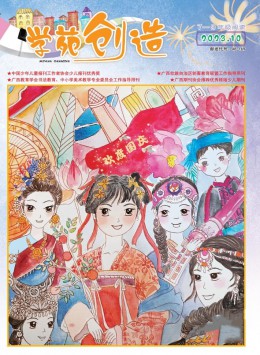
學(xué)苑創(chuàng)造·7-9年級(jí)閱讀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學(xué)苑創(chuàng)造·3-6年級(jí)閱讀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
-

學(xué)苑創(chuàng)造·1-2年級(jí)閱讀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榮譽(yù):中國(guó)優(yōu)秀期刊遴選數(shù)據(jù)庫(k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