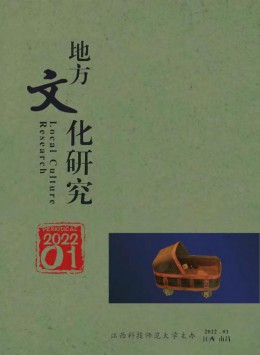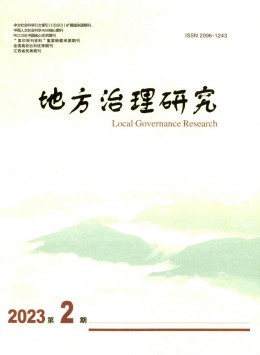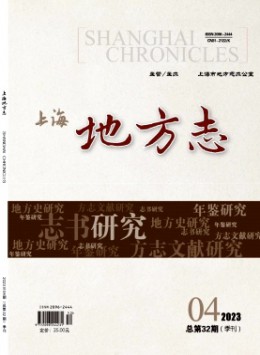地方師范院校古代文學教學改革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地方師范院校古代文學教學改革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地方師范院校的古代文學課程教學應致力于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而應用型人才需側重學生創新能力及應用能力的養成,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學生人文素養的熏染與提升。要達到這一教學目標,關鍵是在教學活動中解決好以下幾組關系:一是教師點撥與學生自學的互動關系,二是文學史與作品選講解的主次關系,三是課堂教學與課外研讀的內外關系,四是教材講授與知識延展的辯證關系。
關鍵詞:應用型人才;古代文學;人文素養;任務驅動;點線面結合;自我教育
為適應社會對應用型人才的需求,六盤水師范學院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在制訂人才培養方案時,特別凸顯應用型人才的培養這一目標。這既是地方本科院校加快轉型發展的立足之本,也是社會對于畢業生綜合素質的具體要求。廣大教師在教學活動中,應當側重于學生的創新能力與應用能力的培養。古代文學作為中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開設的一門重在培養學生人文素質的專業核心課程,有必要轉變教學理念和改革教學模式。筆者認為,關鍵是在教學活動中解決好以下幾組關系。
一、教師點撥與學生自學的互動關系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高等院校課程改革的深入,高校專業課程的設置呈現出多樣性與時效性的趨勢,壓縮傳統課程學時,幾乎成為高等教育界的共識。目前大部分師范院校已將中國古代文學這門課程的總學時數縮減到200學時左右,有的甚至不到100學時。而古代文學這門課程的時間跨度甚為久遠,課程內容涵蓋了從先秦到漢魏六朝,經唐宋而至元明清的長達數千年的文學遺產,不僅本學科的教學內容十分繁雜,而且還涉及到史學、哲學、語言學、文獻學、文藝學及美學等多學科的綜合知識,這就構成了一種深刻的矛盾,因此必須改變傳統教學模式,才能完成教學任務,達到應有的教學效果。而改革的關鍵,乃在于師生關系的徹底轉變。傳統教學通常是教師采取一言堂的灌輸方式,學生則機械地記筆記(現在的很多大學則多表現為教師在臺上播放教學幻燈,而學生在臺下用手機拍照再埋頭抄成筆記形式,更有甚者,學生直接拷走教師的幻燈片,然后學生在課上自己玩手機),考前一周熬更守夜狂背式復習,考后一周忘得一干二凈。很顯然,這樣的傳統教學方式已遠不能適應社會對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要求。新型的高校師生關系應該是這樣的:教師不應當僅僅是知識與學問的輸出者,更應該是方法與思路的點撥者。教師最偉大的地方,不是站在講臺上機械地播放幻燈片和靜態地灌輸知識,而是將學生培養成善于自學并在大學畢業之后還能堅持自學的人,學生的自學能力很大程度上是由教師有意識的引導與充滿智慧的點撥而漸次達到的,而這也是判斷一個教師優秀與否的首要標志。199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1世紀教育委員會了德洛爾報告《學習:內在的財富》,其中提出:教育應圍繞四種基本學習加以安排,即學會求知、學會做事、學會共處及學會做人,學會求知乃是首當其沖需要學會的本領。無獨有偶,日本作家白取春彥在其《獨學術》一書中也如是強調:“不靠自己念書,你什么都學不會。”他說:“無論你進的是語言學校,還是去上大學,如果自己不念書,終究什么都學不到。換句話說,如果不靠自己獨學打底,甚至可能連基本的課程都跟不上。”[1](P24-25)因此,一個真正稱職的高校教師在他授課的過程中,務必使學生樹立起自學的信念,培養起自學的習慣,讓學生懂得一些自學的方法和門徑,進而讓他們走上獨學的道路。學生好比大地上縱橫恣肆的流水,缺乏的不是流動的力而是引導之方,而教師好比挖溝渠的鋤頭,鋤頭過處,流水亦趨。世俗一般認為是水到而渠成,卻不知在師生關系中,實為渠成而水到,由此可見,教師的引導之功,無論怎樣夸張都不為過。具體到古代文學的教學,筆者以為,應當由教師先行講解一段時間,使學生略知學習的方法;再漸次培養學生自學的本事,可運用一些教學上的手段(如任務驅動法)布置一定的自學任務,教師可抽樣檢查并作點撥式講解。經由此種教師點撥與學生自學相結合的方式,一個或幾個學期下來(在有的高校,教師可連上兩段,如筆者所在的高校,有的教師就能連上唐宋文學與元明清文學兩段),建立起一種新型的師生關系,真正達到如古人所謂“教學相長”的理想境界。
二、文學史與作品選講解的主次關系
經過幾代人的研究與實踐,中國古代文學教學業已形成了一種類型化的授課模式,即以文學史為線索而適當穿插作品講解。但在具體的授課過程中,因為授課內容偏多而課時不斷縮減,為了完成所謂的教學任務,不少高校教師有意無意將這門課程變成了只講文學史而不講具體作品這樣一種授課模式,老師所有的授課似乎都是為了幫學生拉通文學的史的流變,這樣一來,在學生的心里,歷代詩人作家便只是一個個抽象的名字,他們所遭遇的時代只是一些印象式的描述,他們的生平與思想成了一種無關痛癢的概述式的介紹,而他們的作品則成了文學史這條長河里跳蕩生滅的一片片浪花,觸目所及,全是一種稍縱即逝的印象。至于那些作家作品的寫作方式與藝術特色,其所受傳統作家的影響,及其在整個文學史上的大概定位(此即“考鏡源流”或“追源溯流”),基本是付諸闕如,或照著教科書宣講而已。毫無疑問,這樣一種授課模式,教學效果是大打折扣的,也是跟應用型人才培養方案格格不入甚或背道而馳的,這既是古代文學教師普遍面臨的尷尬困境,也是他們急需解決的首要問題。我們認為,解決此問題的關鍵,應該是重新審視文學史與作品選講授的主次關系。古代文學教學在課時減少、教學內容增加的情況下,應根據古代文學發展的規律和特點,優化文學史內容(注意:是“優化”而不是“縮減”),正確處理文學史與作品選的主次關系,以突出重點,合理分配文學史和作品選的授課時數。借用數學上的點線面關系而論,竊以為古代文學課的授課方式亦當作適當調整。眾所周知,因點成線,因線成面,如果說文學史是一條長線的話,那么組成這條長線的就是一個個具體的作家及其作品,此即點。點有粗細之別,正如作家有高下之分,一流的大作家及其作品就是文學史這條長線上的重點(一般而言也是學生理解的難點),如先秦段的《詩經》與《楚辭》,漢魏六朝段的陶淵明,唐宋段的李白杜甫蘇東坡,元明清段的四大名著,都是文學史上一流的作家作品,師生務必重點對待。二流作家的重要性則次之,教師當引導學生學會自學,可采取教師授課為主學生自學為輔的方式展開教學。至于文學史上的三四流作家,雖然也是一個個具體的點,但因其重要性逐漸減弱,故不必平均用力進行講授(容易費力不討好),教師可適當點撥自學之法,然后安排學生課后完成。至于面,一般多見于文學史每編之緒論,故需簡明扼要進行講述,最好讓學生課前預習緒論部分的內容,然后繪制出某一時期的文學生態圖。除此而外,文學史中的面,還有一種情況,即時代相近或風格相類或影響力相當的幾個作家可使學生進行面的把握。如講授唐宋文學時,可將初唐四杰作為一個面,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是一個面,以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派是一個面,乃至韓孟詩派,元白詩派,大歷詩風,晚唐詩歌,都可從面上進行講授。至如宋代文學,則江西詩派,豪放詞,婉約詞,唐宋八大家等,都可從面上進行點撥式講授,如此則綱舉目張,化繁為簡,從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文學史的主體是一個個具體作家的文學創作,因此,中國古代文學課應當自覺回到文學文本世界,教師要有分析文學作品的自覺意識,對作品的分析導讀不應少于總學時數的3/5。只有引導學生閱讀盡可能多的古代文學作品,并學會分析和鑒賞文學文本(需要結合文藝學、古代文論、古代文體論、美學、歷史學、禪宗佛學乃至闡釋學的相關知識),從而使學生積累較多的原始材料,有助于學生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將知識轉化為能力。這需要教師自己對于各作家作品都有比較深入的理解,并能采取靈活多變的教學方認真施教。而文學史的講授不宜超過總學時數的2/5,而且不必過多按照教材照本宣科地復述,可適當讓學生參與完成文學史的拉通(可采取任務驅動法,讓學生繪制一張文學史流變圖,或讓學生編寫作家生平與創作年譜),從而培養學生的自學研讀與歸納總結能力。需要注意的是,教師在講授文學史的過程中,應當自覺地反復引導學生回到教材的目錄,并教學生讀懂教材目錄所蘊含的學術信息,把握其中的重點難點。姑以隋唐五代文學為例,袁行霈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將隋唐五代文學編排為第四編,除了緒論,共分十二章。從教材目錄即可看出,李白、杜甫、白居易(含元白詩派)、李商隱為本編重點,各占一章的篇幅,因而應是講授和學習的重點。而王孟、高岑及王昌齡和王翰諸人,共占一章的篇幅,重要性自不能與李杜及白居易李商隱相比。至如唐傳奇與俗講變文,雖專設一章,但只有兩節的內容,教師完全可以讓學生課后完成。
三、課堂教學與課外研讀的內外關系
大學生以自學為主,這既是高等學校教學規律的客觀要求,也是應用型人才培養方案的具體體現。這就需要教師解決好課堂教學與課外研讀之間的關系,要將課外研讀視為課堂教學的自然延伸。鑒于當代大學生普遍厭學的情況(學生厭學,一方面跟物質功利主義的時代思潮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跟學生缺乏自學方法的指導有很大關系),教師應在授課過程中自覺注入自學方法的探討與點撥。對于那些不需要精講的次重點(如大歷詩風和韓孟詩派),以及一些簡單的詩詞文學作品,教師可采取自學指導法,提前布置好自學的任務,讓學生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可獨立完成,亦可分組完成)。當學生在自學中發現問題產生疑問時,教師要及時予以點撥。因此,教師不僅要重視課堂教學,還要注意課后與學生之間的雙向交流。雙向交流的方式可以靈活處理,如可網上答疑(教師可組建一個學習交流群),也可每周定一個時間面對面答疑,還可以利用導師制與學生分享自學經驗與讀書心得。教師應鼓勵學生堅持寫讀書札記,或組建古代文學興趣小組,并進行有針對性的引導。總之,教師在具體教學中,要根據不同的狀況而采取不同的教學方法。一個優秀的高校教師,既要讓課堂教學成為師生交流互動的絕佳場所,更要讓課外研讀變成學生的入門捷徑,從而為學生畢業之后的自我教育奠定一個良好的基礎。
四、教材講授與知識延展的辯證關系
學生如能在教師指導下成功進入課外研讀的軌道,那么教師將贏得課堂教學的寶貴時間。教師在課時縮減的情況下又該怎樣進行課堂教學呢?應該說這里面既有一個認識上的問題,也有一個技巧上的問題。首先,教師應該轉變觀念,要從傳統以灌輸知識為主的教書匠角色轉變成以點撥自學方法為主的引導者角色。因此,教師必須做到既要深刻理解他需要講授的內容,又要懂得鉆研的方法并有意識地提煉出方法論原則以分享給學生。如果教師自己都只是滿足于做知識流水線上的傳輸者,那么他就不可能做到方法論的點撥。學生畢業之后,很可能會迅速忘記他在大學學習的具體知識,而方法則能幫助他較好地完成從學校教育向自我教育的轉化。當然,教師只講方法是不對的(那會造成對于方法的過分依賴從而扼殺方法本身),但是只講一個個具體的知識點而不涉及方法,恐怕也不是成功的教學。最正確的方式應該是:教師借助于某些知識點的講解從而引導學生上升到方法論的高度,知識可以淡化甚或遺忘,而獲取知識的方法卻能在學生心底變成智慧的種子,作用于他的未來。這就要求高校教師不僅要研究知識與學問,更要自覺鉆研獲取新知與整合思想的方法,方能在課堂教學中有所顯示和彰明。舉例而言,《古典文學知識》雜志就常刊登名家的治學方法(如臺灣學者張高評先生的治學門徑專欄文章,頗值得研讀效法),教師應著力推介給學生,課堂上亦可結合教材知識點而略作詮解。他如臺灣學者杜松柏先生所著《國學治學方法》,雖是專論治國學的方法,但其中亦有不少可資古代文學教師借鑒者。至如笛卡爾之《方法論》,杜威之《思維術》,都可研究。總之,治學方法與具體知識的辯證關系,誠如杜松柏所云:“自思想的方法言,方法是手段而非目的,自治學研究言,方法是明道的工具,所以道固然應重,而方法亦不可或忽。”[2](P228)其次,在課堂教學的技巧方面,教師應在講授教材知識點(包括3/5學時的作品選和2/5學時的文學史)的同時,適當拓展知識面,而不能拘囿于教材本身(否則有照本宣科之嫌)。教師應旁搜博采,以擴大學生的知識視野。如講初唐四杰,可引張志烈《初唐四杰年譜》、駱祥發《初唐四杰研究》、王明好《盧照鄰研究》及陳于全《楊炯研究》中的相關研究成果。講孟浩然,則可提及王輝斌先生的研究。他如郁賢皓先生的李白研究,葉嘉瑩的唐詩研究,莫礪鋒的杜甫研究和江西詩派研究,袁行霈的盛唐詩壇研究,龔鵬程的唐代思潮研究,魏耕原的盛唐名家研究,甚至羅宗強和張毅先生的文學思想史研究,王運熙先生、顧易生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張伯偉先生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周裕鍇先生的中國古代闡釋學研究,程千帆先生的問題意識等等,都是需要教師在課堂上有意識貫穿講解的拓展內容。這就要求教師樹立終身學習的高度責任感,如此既有教材中的講解與分析,又有知識的拓展與延伸,更有自學方法的點撥與熏陶,配合學生課外的廣泛研讀,我們相信,是有助于提高古代文學課程的教學效果的。
注釋:
[1]張富玲、戴偉杰譯,白取春彥:《獨學術》,臺北:麥田出版,2014年版。
[2]杜松柏:《國學治學方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衛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