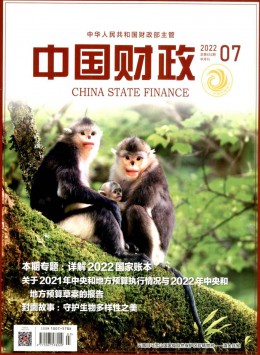財政分權及地方工業發展分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財政分權及地方工業發展分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本文基于1998-2018年我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省級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財政收入分權和財政支出分權對地方工業發展的影響。結果顯示,財政收入分權和財政支出分權均會顯著的促進地方工業發展,且財政收入分權的促進作用更強。此外,這種促進作用還具有區域異質性,表現為:將財政支出分權作為財政分權的衡量指標,財政分權顯著提高了東部和中西部地區的工業發展水平,但當將財政收入分權作為財政分權的衡量指標時,財政分權顯著提高了東部地區的工業發展水平,而對中西部地區的影響并不顯著。
關鍵詞:財政分權;地方工業發展;地方政府;異質性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而工業是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也是實體經濟的主體,其對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我國工業具有較好的發展基礎,也不斷面臨著新的挑戰。而工業快速增長的同時還伴隨著財政體制安排的持續調整,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實行推動了我國經濟的繁榮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國經濟奇跡(張軍和范子英,2018)[1]。在財政分權的背景下,各地政府的財政自由度顯著增強,擁有了一定的決策自主性,也具有事權以及支出責任,明確了其利益主體地位。因此,在財政分權的體制下以及上級政府的績效考評制度下,地方政府官員會綜合考慮地方經濟發展以及稅收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與此同時產生的問題是地方政府官員任期是一定的,在理性人的假定下,其必將“短視”,可能會存在投資偏好行為,傾向于發展能較大幅度增加稅收收入的行業,如工業;而不愿意進行科技創新方面的投入,因為技術創新投資具有周期長、風險大、回報率低且易產生外溢性的特點。因此,本文將重點關注財政分權對地方工業發展的影響,從財政收入分權和財政支出分權兩個角度入手,使用1998-2018年的省級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來探究。此外,還將樣本劃分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以解決模型的異質性。田艷平等(2018)[2]認為中國式分權式導致我國工業粗放式增長的重要制度原因。范劍勇和莫家偉(2014)[3]發現,地方政府舉債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和壓低工業市場用地價格以吸引投資,其動機同樣源于中國特色的財政分權和地方政府競爭。財政收入激勵地方政府開拓收入來源,過度、低價供給工業用地,導致工業產能過剩(陶然,汪暉,2010)[4]。嚴思齊和彭建超(2019)[5]發現,財政分權對工業用地利用效率的影響會因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而有所差異,當人均生產總值或高技術產業占比較低時,展現為負向影響,而當人均生產總值或高技術產業占比達門檻值以上時,財政分權對工業用地利用效率的影響顯著為正。基于此,本文可能的貢獻如下,一是系統性的研究財政收入分權和財政支出分權對地方工業發展的影響;二是將全國劃分為東部和中西部地區進行分樣本回歸,分析是否存在區域異質性。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與數據來源本文的研究期間選取1998-2018年,本文的研究樣本為我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本文的數據來自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國泰安數據庫。
(二)模型設定根據本文的研究目的,構建計量模型如下:yit=α+βFDit+γXit+δi+μt+εit其中yit表示i年t省份的工業發展水平,FDit表示i年t省份的財政分權程度,Xit表示控制變量,β為財政分權系數,γ為控制變量系數,εit為擾動項,δi和μt分別代表省份和時間固定效應。
(三)變量定義1.被解釋變量本文的被解釋變量是地方工業發展水平(Company),用地方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單位數來衡量。2.核心解釋變量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是財政分權程度(FD),用財政收入分權(FDin)和財政支出分權(FDex)來衡量。其中財政收入分權(FDin)用一般預算收入占全國一般預算收入的比重來表示,財政支出分權(FDex)用一般預算支出占全國一般預算支出的比重來表示。3.控制變量(1)產業結構(STRUC):用工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2)實際人均地區生產總值(GDP_cp):用實際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來衡量。(3)交通便捷度(ROAD):用鐵路與公路的里程數之和來衡量。(4)人口數(POP):用地區生產總值與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衡量。(5)外貿依存度(OPEN):用進出口總額占該地區GDP的比重來表示,對進出口總額以相應年份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折算成人民幣計價。
三、實證分析
(一)全樣本回歸分析本文運用stata15軟件對方程進行回歸,以考察財政分權對地方工業發展的影響。根據Hausman檢驗,模型適合固定效應模型,表1是對全樣本回歸分析得到的結果。模型1~模型3將財政支出分權作為財政分權的衡量指標進行回歸,模型4~模型6將財政收入分權作為財政分權的衡量指標進行回歸,其回歸結果表明,財政分權與工業發展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且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說明將財政收入分權作為財政分權的衡量指標是較為穩健的。其中模型6的擬合程度最好,表明地方政府財政分權程度每增加一個百分點,本地國有及規模以上單位數會增加2518個。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分權程度越高,財政自主性也越高,為贏得“政治錦標賽”就會將更多的資金應用于給企業的資金補貼以發展地方工業,還可能會挪用公共服務支出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等生產性投資領域(范子英,2016)[6],對工業規模的擴張產生促進作用,進而提高地方工業的發展水平。最后,就其他控制變量而言,實際人均GDP(GDP_cp)在模型3和模型6中,控制了省份效應和年份效應后,其系數僅在10%的水平下顯著且為負,意即實際GDP對工業發展有抑制作用。人口數(POP)在模型1~6中,其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且為正。表明人口數的增加會促進工業的發展,因為人力資本是發展工業的重要因素。外貿依存度(OPEN)的回歸系數在模型中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多數為正,表明當外貿依存度增加時,會顯著的促進工業增長,其內在原因是進出口同樣是拉動工業增長的馬車。產業結構(STRUC)的回歸系數在10%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優化產業結構有利于工業的發展。而交通便捷度(ROAD)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故交通越方便的地區,其工業發展水平越高(見表1)。
(二)分樣本回歸分析從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得知,在全國范圍內,財政分權顯著促進了工業的發展,因此,為觀察這種促進作用是否具有區域異質性,在同時控制省份效應和年份效應的情況下,我們將樣本分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并分別進行回歸,得表2的回歸結果。模型1和模型3是將財政支出分權作為財政分權的衡量指標,財政分權顯著提高了東部和西部地區的工業發展水平,但當將財政收入分權作為財政分權的衡量指標(模型2和模型4)時,財政分權顯著提高了東部地區的工業發展水平,而對中西部地區的影響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表明財政分權對工業發展水平的促進的確具有區域異質性。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1998-2018年我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省級面板數據,實證分析了財政收入分權和財政支出分權對地方工業發展的影響。結果顯示,財政收入分權和財政支出分權均會顯著的促進地方工業發展,且財政收入分權的促進作用更強。此外,這種促進作用還具有區域異質性,表現為:將財政收入分權作為財政分權的衡量指標時,財政分權顯著提高了東部地區的工業發展水平,而對中西部地區的影響并不顯著。根據以上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兩點政策建議:第一,進一步完善財政收支管理體制,主要是省以下的財政收支管理體制。加快推進部門細化預算和財政集中支付制度,進一步規范財政收支的核算管理,增加預算的透明度和約束力。第二,完善地方官員的晉升制度,注重完善地方官員的政績考評體系,進而優化地方的產業結構,提高居民幸福度,滿足居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和社會進步與發展的需要。
參考文獻:
[1]張軍,范子英.再論中國經濟改革[J].經濟學動態,2018(8).
[2]田艷平,徐瑋,顧賈能.影響工業高質量增長的制度性因素——基于中國式分權的研究[J].學習與實踐,2018(5).
[3]范劍勇,莫家偉.地方債務,土地市場與地區工業增長[J].經濟研究,2014,49(01).
[4]陶然,汪暉.中國尚未完成之轉型中的土地制度改革:挑戰與出路[J].國際經濟評論,2010(02).
[5]嚴思齊,彭建超.財政分權對工業用地利用效率影響的門檻效應——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研究[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19(01).
[6]范子英.土地財政的根源:財政壓力還是投資沖動[J].黨政視野,2016,440(02).
作者:李雪瑜 單位:鄭州大學國際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