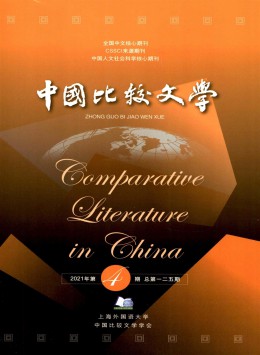比較文學傳播嬗變分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比較文學傳播嬗變分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一、單向輻射傳播模式
早在比較文學學科形成之前,比較文學“借用理論”的奠基人德國學者特奧多爾•本菲就曾于1859年憑借其對印度《五卷書》的長期實證研究,宣稱印度文學中的部分寓言、童話與民間故事是在中世紀經(jīng)由歐洲得以傳播,繼而傳遍世界的。此后,經(jīng)過本菲的諸多追隨者的共同努力,比較民間故事學中注重研究傳播路徑的“傳播學派”得以確立。對此,季羨林先生曾指出:“從此奠定了一門新學科的基礎(chǔ):比較童話學或者比較文學史,兩者都屬于比較文學的范疇”①。在比較文學學科誕生之初興起的法國學派的主導研究范式中,對于跨越國界的文學傳播而言,其路徑主要體現(xiàn)為立足于傳播者的直線模式。該派素以倡導影響研究法而著稱,然而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如果要對法國學派的研究傾向和特點加以概括的話,我認為將它們稱為‘傳播研究’更合適些。梵•第根等人所推介的國際文學之間的‘經(jīng)過路線’的研究,伽列、基亞等人所主張的‘國際文學關(guān)系史’的研究及其方法,嚴格地說,都是傳播研究方法”②。事實的確如此,梵•第根曾在其專著《比較文學論》中表明:“在作那對于一位作家、一件作品、一種文體或一個國家的整個文學在外國的成功以及總括的影響的任何比較文學研究之前,我們有著一個條件:對于這些作品的多少要廣闊一點的知識。人們所謂一部書或一系列的書的‘傳播’,是可以由原文直接地傳播的;對于只有少數(shù)人懂外國文的某一些國家,這種情形當然是少有的;如果是說一部法文作品在十八世紀或十九世紀的意大利、荷蘭、俄羅斯等國的傳播,這種情形卻是更多一點。”③鑒于此,該著述將傳播“媒介”劃分為“個人”、“社會環(huán)境”、“批評;報章和雜志”以及“譯本和翻譯者”等。在梵•第根看來,“在兩國文學交換之形態(tài)間,我們應(yīng)該讓一個地位———而且是一個重要的地位———給促進一種外國文學所有的著作、思想和形式在一個國家中的傳播,以及它們之被一國文學采納的那些‘媒介者’”④。由此可見,他賦予了個人媒介,也就是傳播者,以極高的地位。其后,法國學者基亞承續(xù)了梵•第根的學說,在其《比較文學》一書中倡導研究“有助于國與國之間或文學與文學之間了解的人士或典籍”的“文學世界主義的”,具體涉及如下層面,即:語言知識或語言學家;翻譯作品或譯者;評論文獻與報章雜志;旅游與觀光客;一種因為地理與文化特殊情況所造成的國際公民;等等⑤。毋庸諱言,該派的確對于國家之間的文學傳播活動及其相關(guān)現(xiàn)象頗為關(guān)注。然而,必須承認的事實是,時過境遷之后,對于該派的傳播研究予以重審,可以看出其中的諸種歷史局限。首先,該派囿于其時的社會條件將傳播的環(huán)境限定為“朋友的集團”、“文學會社”、“沙龍”以及“宮廷”,此種劃分方式與現(xiàn)代實際情境之間不免存在差異;其次,盡管該派的傳播研究并非僅強調(diào)孤立的影響,而是憑借輻射研究策略呈現(xiàn)出發(fā)散研究的模式,但是,其研究是以放送者為本位的,明顯缺乏對于受眾以及傳播效果的應(yīng)有關(guān)注,因而主動轉(zhuǎn)播者與被動接受者的實際關(guān)系無疑暴露出該派有關(guān)傳播的研究來而不往且有去無回的宿命。由此,該派僅關(guān)注信源與信道,而忽略了反饋渠道的研究實際上隸屬于單向直線的文學傳播模式。
二、雙向互動傳播模式
1958年9月,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第二屆年會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教堂山(ChapelHill)召開,期間耶魯大學教授雷納•韋勒克通過題為《比較文學的危機》的學術(shù)報告向其時掌握比較文學學科話語權(quán)的法國學派的諸位權(quán)威發(fā)起挑戰(zhàn)。其后,以解構(gòu)法國學派及其影響研究法為己任的美國學派逐漸興起,進而曾長期居于比較文學學科的領(lǐng)軍地位,并且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后,韋勒克曾在其《比較文學的危機》、《今日之比較文學》等文章中數(shù)次強調(diào)他否定的只是導致學科陷入危機的僵化認知模式與方法論所存在的不恰當之處,而“令人遺憾的是,它被理解成為美國比較文學學派的宣言,并且是對于法國學派的攻擊,盡管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它所針對的并非是一個國家而僅僅是一種方法”①。由此,韋勒克及其美國學派的諸位同仁以平行研究法為圭臬,反對把比較文學研究僅局限于確有直接影響的不同民族文學之間的實證分析,主張對于文學與其他文化現(xiàn)象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予以探討,提倡從美學的角度分析各民族文學的異同,并且廣泛涉及對于主題、題材、文體、人物形象、技巧、思潮與文學史等方面所存在的類同與差異的研究。客觀而言,該派的平行研究法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法國學派的“一言堂”方式所帶來的諸種痼疾,在其時的確堪稱是力挽狂瀾之舉,從而為比較文學學科史書寫了可圈可點的一頁。此外,該派奉行對等原則,不考慮事實聯(lián)系,因而不再如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法那樣強調(diào)放送、流傳與媒介,轉(zhuǎn)而倡導總結(jié)異質(zhì)文化的發(fā)展規(guī)律,涉及不同作家、流派、團體、國家之間的文學文本與現(xiàn)象,從而較為充分地體現(xiàn)了諸國文學之間的雙向互動。然而,隨著比較文學學科的發(fā)展,該派對于法國學派矯枉過正,其盲目排斥傳播研究與實證方法等弊端逐漸暴露無遺。鑒于此,其后比較文學學科的發(fā)展逐漸表現(xiàn)出跨文化互動的強烈訴求,基于各國文學的傳播研究不僅重新成為該學科的一個重要考察維度,而且呈現(xiàn)出兼顧放送者與接受者的循環(huán)傳播模式。以中國比較文學領(lǐng)域的相應(yīng)研究為例,有關(guān)中外文學與文化關(guān)系的諸種雙向闡釋突顯了傳播者與接受者的互動特征,在內(nèi)容的深廣度與成果的豐厚性等方面均彰顯出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延拓。自20世紀上半葉起,有關(guān)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文學的跨文化交流問題即引發(fā)了諸位杰出學者傾盡心力的研究。如針對中西交通史研究而言,陳垣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張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向達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以及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等著述相繼問世。基于中外古代文學的關(guān)系研究來看,季羨林的《〈西游記〉里面的印度成分》、陳寅恪的《西游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以及楊周翰的《彌爾頓〈失樂園〉中的加帆車》等無疑堪稱典范之作。新時期以來學界有關(guān)中外文學的交互傳播以及對話與交流的諸種研究呈現(xiàn)異軍突起之勢。首先,針對中外文學關(guān)系進行雙向觀照的著述陸續(xù)問世。例如:《中印文學關(guān)系源流》(郁龍余編,1987年)、《中日古代文學關(guān)系史稿》(嚴紹璗著,1987年)、《近代中日文學交流史稿》(王曉平著,1987年),《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論》(于語和主編,1997年),《20世紀中西文藝理論交流史論》(殷國明著,1999年),《中外文學交流史》(周發(fā)祥主編,1999年),《二十世紀中外文學交流史》(李岫主編,2001年),《中西文化交流史論》(何兆武著,2001年),《中西戲劇文化交流史》(李強著,2002年),《中英文學關(guān)系編年史》(葛桂錄著,2004年),《中外文學關(guān)系史資料匯編(1898—1937)》(賈植芳、陳思和主編,2004年),《中外交流史事考述》(蔡鴻生著,2007年),《冷戰(zhàn)•民族•文學:新中國“十七年”中外文學關(guān)系研究》(方長安著,2009年)等。其次,有關(guān)國外文學與文論在中國的傳播情況的論著可分為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一方面是對于國外文學思潮、流派與團體以及國別文學的整體引介,例如:《東方各國文學在中國:譯介與研究史述論》(王向遠著,2001年),《20世紀法國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與接受》(許鈞等著,2007年),《走向全球化:論西方現(xiàn)代文論在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界的傳播與影響》(馮黎明著,2009年),《俄蘇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陳國恩等著,2009年),《“誤讀”的方法:新時期初西方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傳播與接受》(葉立文著,2009年)等。另一方面是針對國外具體作家及其文本在中國的傳播情況的著述,例如:《屠格涅夫與中國:二十世紀中外文學關(guān)系研究》(孫乃修著,1988年),《普希金與中國》(張鐵夫主編,2000年)、《荒原之風———T•S•艾略特在中國》(董洪川著,2004年)等。再者,關(guān)于中國文學在國外的傳播情況的著述相繼出現(xiàn)。例如:由北京大學與南京大學合作出版的“中國文學在國外叢書”,自20世紀90年代初起,先后刊行了數(shù)種專著,包括:《中國文學在朝鮮》(韋旭升著,1990年),《中國文學在日本》(嚴紹璗等著,1990年),《中國文學在俄蘇》(李明濱著,1990年),《中國文學在英國》(張弘著,1992年),《中國文學與法國》(錢林森著,1995年),《中國文學在東南亞》(饒芃子主編,1999年),《中國文學在德國》(曹衛(wèi)東著,2002年),《中國•文學•美國———美國小說戲劇中的中國形象》(宋偉杰著,2003年)等。此外,針對具體個案展現(xiàn)中外文化交匯狀況的專著先后完成。如《跨文化溝通個案研究叢書》(樂黛云主編,2005年)選取王國維、吳宓、錢鍾書、朱光潛、林語堂、梁實秋、馮至、卞之琳、梁宗岱、聞一多、陳銓、宗白華、穆旦以及劉若愚等中國近現(xiàn)代學術(shù)名家進行了個案研究。
三、多元系統(tǒng)傳播模式
目前,傳播媒介的發(fā)展的確堪稱日新月異,媒介的更替并非僅為工具、手段乃至渠道的變化而已,而是導致了閱讀方法、思維方式甚或價值觀念的轉(zhuǎn)變。由此,比較文學學科層面的文學傳播同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zhàn)。
(一)文學傳播的媒介更新與變革
針對文學與時代的關(guān)聯(lián)性問題,劉勰曾在其《文心雕龍•時序》篇中指出:“時運交移,質(zhì)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①由此論及因文學的載體置換所導致的文學形態(tài)的時代變遷,鑒于文學必須通過媒介在文本與社會、文本與作者、文本與讀者、作者與讀者、創(chuàng)作與閱讀、生產(chǎn)與消費、傳播與市場之間實現(xiàn)溝通與交換,媒介對于文學自身的發(fā)展無疑具有不容忽視的影響。人類歷史進入20世紀以來,信息傳播不再僅依靠傳統(tǒng)的紙質(zhì)媒介,而是轉(zhuǎn)為兼用相繼誕生的第二媒體電波、第三媒體電視、第四媒體互聯(lián)網(wǎng)以及第五媒體手機等。與之相應(yīng),曾經(jīng)憑借傳統(tǒng)的紙質(zhì)文本獨霸天下的文學存在方式、傳播方式以及接受方式發(fā)生了具有革命意義的轉(zhuǎn)變,出現(xiàn)了傳統(tǒng)媒介與新興媒介整合的局面,而將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融為一體的數(shù)字媒體使文學的體裁、類型、生產(chǎn)、溝通與交流都發(fā)生了數(shù)次轉(zhuǎn)型。1999年,博客(blog)被正式定名。諸種新型媒介隨即相繼應(yīng)運而生,例如:維基網(wǎng)(Wikipedia)、第二人生(SecondLife)、聚友網(wǎng)(MySpace)、播客網(wǎng)(Podcast)、臉譜網(wǎng)(Facebook)、掘客網(wǎng)(Dig)、優(yōu)視網(wǎng)(YouTube)以及推特網(wǎng)(Twitter)等。與之相應(yīng)的諸種載體硬件也紛紛出現(xiàn),例如:iPad平板電腦,黑莓手機、iPhone手機以及其他智能手機等。與此前的傳播媒介相比較而言,“新媒體的用戶不得不等待被人生產(chǎn)的內(nèi)容,比如從亞馬遜書店買書、在iTunes播放器上下載歌曲就不得不等待。相反,新新媒介的用戶被賦予了真正的權(quán)力,而且是充分的權(quán)力;他們還可以選擇生產(chǎn)和消費新新媒介的內(nèi)容,而這些內(nèi)容又是千百萬其他新新媒介消費者-生產(chǎn)者提供的”②。基于未來的媒介走向與前景來看,“這樣的媒介不是‘后’新新媒介,也不是‘新’新新媒介,而是新新媒介的‘超級版’,也就是新新媒介的‘仿生版’”③。
(二)比較文學學科的應(yīng)對策略
陳寅恪曾倡導:“一時代之學術(shù),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shù)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④上述治學理路對于不斷受到新興媒介沖擊的比較文學學科而言,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值此數(shù)字媒介時代,面對層出不窮、模式翻新的傳播媒介,比較文學學科只有與時俱進,有效利用傳播媒介這把雙刃劍,才是其謀求生存與發(fā)展的明智之舉。
首先,堅守傳媒語境中比較文學學科的文學本位。“傳媒時代”所帶來的諸種困惑與焦慮使有關(guān)“文學終結(jié)論”、“理論終結(jié)論”以及“批評終結(jié)論”的激烈論爭頻繁交鋒。由紙質(zhì)閱讀到屏幕閱讀再到拇指移動閱讀的歷史變遷,使文學研究的對象與方式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嬗變。正如伊格爾頓在其《理論之后:文化理論的當下與未來》中所指出的,“輕聲細語的中產(chǎn)階級學生勤奮地聚集在圖書館里,努力地研究著駭人聽聞的題材,例如吸血鬼、挖眼球、半機械人或色情電影”。在他看來,“顯而易見的事實是,研究乳膠的文學或肚臍環(huán)的政治涵義,是完全依據(jù)一句古老且睿智的箴言字面義———學習應(yīng)該是充滿樂趣的;這就如同你可以選擇全麥威士忌的口味比較或終日躺在床上的現(xiàn)象學作為碩士學位論文的選題一樣。由此,知識生活與日常生活之間不再有任何罅隙。不用離開電視機就可以撰寫你的博士論文是有很多好處的”①。由此,他認為,“在今天,研究彌爾頓文本中的經(jīng)典表述的老頑固輕視沉浸在亂倫與賽伯空間中的女性主義的激進分子;專注于論述戀腳癖或男性緊身褲前飾袋史的年輕學者,則帶著懷疑的眼光望著膽敢主張簡•奧斯汀(JaneAusten)比杰佛瑞•亞契(JeffreyArcher)更為偉大的老學究”②。與之相應(yīng),日益更新的媒介語境使比較文學范圍內(nèi)的文學史、文學理論與批評的研究取向面臨著艱難的抉擇與嚙合。新型媒介語境中的文學傳播憑借迅捷、便利、高效與廣泛等優(yōu)勢逐漸贏得了受眾的青睞。電子傳播載體對于受眾的自主性與能動性的有效調(diào)動以及對于傳播的深廣度的提升,無疑是功不可沒的。然而,其負面影響也是必須予以警覺的。鑒于此,針對比較文學學科而言,在文學傳播范式的蛻變中,如何甄別良莠不齊的文學現(xiàn)象,如何更好地利用諸種數(shù)字化媒介而不是為其所囿,進而在堅守中彰顯與提升文學性,無疑是研究者無法回避的課題。一方面,新媒介自身在功能與效力等方面的特點帶來了文學生產(chǎn)與接受方式的變化,傳媒的發(fā)展為大眾文化廣泛、快速的傳播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載體,影像、電子媒介使個體的原創(chuàng)文學作品能夠迅速轉(zhuǎn)換為大批量的復制品。此外,傳統(tǒng)的靜態(tài)閱讀轉(zhuǎn)換為動態(tài)閱讀,深度消平后的文學閱讀方式呈現(xiàn)出平面化、碎片化等傾向,而對于文學性的解構(gòu)則致使文學的內(nèi)容與形式發(fā)生錯位,由此導致了傳統(tǒng)的文學經(jīng)典遭遇了閱讀危機,進而直接阻礙了經(jīng)典得以確立與傳播的路徑。另一方面,新媒體的商業(yè)化傾向也帶來了無以回避的負面效應(yīng),不僅導致文學觀念與使命意識的淡化,而且促使文學的擴容與泛化現(xiàn)象的滋生。數(shù)字媒介的市場化運行模式致使文學的超功利性被純粹功利性所取代,提升精神價值的訴求被迎合受眾品位的目標所取代,追求審美愉悅的目標被追求物質(zhì)利益的動機所置換。由此,就對于文學傳播的評判標準而言,傳播方式勝于傳播內(nèi)容,傳播范圍勝于審美意義,媒體創(chuàng)新勝于文本創(chuàng)新,因而不免流于淺表化和噱頭化。
其次,關(guān)注新興傳媒構(gòu)成的比較文學研究領(lǐng)域。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逐漸普及與手機等通訊工具的廣泛使用,網(wǎng)絡(luò)、手機等新興載體逐漸成為現(xiàn)代傳媒中的后起之秀。2011年,第八屆茅盾文學獎首次向網(wǎng)絡(luò)文學敞開了大門,共有七部網(wǎng)絡(luò)小說參選,其中《遍地狼煙》還在首輪中勝出,雖最終未能折桂,但標志著電子媒介進入現(xiàn)代中國主流文學。又如,誕生于美國的“第二人生”是一個基于因特網(wǎng)的虛擬世界,剛開始被認為與其他具有游戲功能的媒介并無二致。然而,由于其不斷加快自身的真實化進程,并為作家開設(shè)了網(wǎng)絡(luò)虛擬書店,從而為各國文學作品在全球范圍內(nèi)的傳播提供了平臺。目前,不僅美國最大的在線書店Amazon書店業(yè)已進駐“第二人生”接受網(wǎng)友購書申請,而且路透通訊社也進入該網(wǎng)站開辟分社,為其網(wǎng)友報道新聞。再如,手機小說發(fā)端于日本,該國不僅較早將傳統(tǒng)小說搬進手機,而且率先推介原創(chuàng)手機小說。《深愛》、《戀空》等手機小說的實體書先后在書籍銷售排行榜上獨占鰲頭,并且陸續(xù)被拍攝成影視作品且反響良好,進而對于其他國家的相關(guān)創(chuàng)作與傳播領(lǐng)域形成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正是依托日本手機小說的發(fā)展空間與市場優(yōu)勢,美國作家貝瑞•約克魯(BarryYourgrau)與其日語譯者合作,專門針對日語手機閱讀群體創(chuàng)作超短篇小說。他的作品被稱為“快速小說”或“瞬間小說”,以善于描寫家庭關(guān)系,具有戲劇性著稱,并且風靡日本。此種創(chuàng)作行為與傳播方式同林紓當年所從事的譯介活動在傳播方式與操作路徑等方面具有跨越歷史時空的相似之處。
再者,拓展中外文學交流的傳播路徑。加拿大著名的傳播學領(lǐng)軍學者麥克盧漢曾在其《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一書中明確指出:“在機械時代,我們完成了身體在空間范圍內(nèi)的延伸。今天,經(jīng)過了一個世紀的電力技術(shù)(electrictechnology)發(fā)展之后,我們的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又得到了延伸,以至于能擁抱全球。”①事實的確如此,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學創(chuàng)作、閱讀與傳播不再局限于個體、地域、民族與國家的范圍之內(nèi),而是構(gòu)成了一種跨文化的文學場域。目前,作家無論身處何地都可以通過BBS、博客、播客或手機等媒介直接、宣傳與推廣自己的作品,并參與其他作者的類似活動,從而既是創(chuàng)作者,又是傳播者、發(fā)送者與接受者。與之相應(yīng),文學參與方式的變化、傳播速度的加快使傳播空間得以拓展,進而不斷為建立新的多元化世界文學格局提供了諸種可能性。以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為例,在以傳統(tǒng)傳播方式為主導的時代,盡管《中國文學》雜志、“熊貓”叢書等媒介都曾為中國文學在國外的譯介與傳播做出過篳路藍縷的貢獻,可謂功不可沒,但是以往因囿于媒介與方式等因素的限制,最終能夠在國外獲得認同的中國文學作品數(shù)量甚少,反響也極為有限。在新興傳播媒介不斷更替的當下,諸種新型傳播渠道使中國文學的對外輸出得以強化與發(fā)散,相關(guān)影響也日益擴展。2011年,王安憶與蘇童同時入圍著名的布克國際文學獎(ManBookerInternationalPrize)的最終候選人名單。盡管并未奪魁,但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國作家正在日益贏得海外的關(guān)注與肯定。近年來,中國作家榮獲國際文學界各類獎項及提名的現(xiàn)象屢見不鮮,除作家實力、作品質(zhì)量之外,傳播媒介的作用無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綜上所述,比較文學學科范圍內(nèi)的文學傳播范式經(jīng)歷了由單線向復線進而趨向多元的歷史變遷。目前,對于身處日新月異的傳媒環(huán)境中的比較文學學科而言,如何憑借學科在視角與方法等層面的諸種優(yōu)勢,合理、有效且充分地彰顯文學與傳播的諸種關(guān)聯(lián)性,無疑是該學科的未來發(fā)展策略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