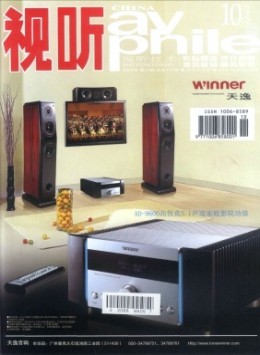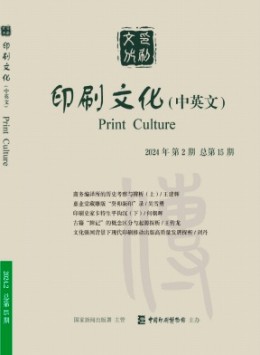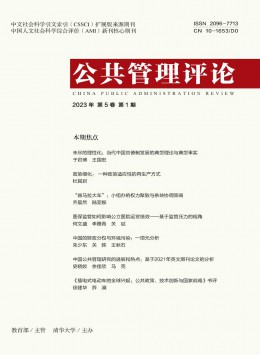跨文化溝通論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跨文化溝通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跨文化溝通論文范文
[關鍵詞]對比修辭 翻譯研究 關系
[中圖分類號]H31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1)05-0041-02
引言
對比修辭學可謂是當今語言學研究的熱門領域之一,它主要通過對修辭模式的差異分析來研究跨語言、跨文化寫作的異同,與第二語言寫作、翻譯教學及英語多元化研究有密切聯系,對認識了解跨文化語言和寫作上的文化差異有重要影響。近年來,出現了將對比語言學與翻譯理論結合研究的趨勢。這種結合形式的研究主要探究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在句法、篇章結構方式上存在的文化異同,尤其是比較其間的主要差異。本文將結合國內外的有關研究成果及作者的認識,從以下幾方面對對比修辭與翻譯研究進行概括性評述。
一、對比修辭研究概述
對比修辭學(Contrastive Rhetoric)是應用語言學領域的一個跨學科研究分支,它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創于1966年,以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母語的修辭模式對第二語言寫作的影響為主要研究對象。美國應用語言學家Robert Kaplan可算這一領域的拓荒者和領路人。“對比修辭”這個概念是他在對近六百篇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所寫作的英語作文進行系統的比較研究后率先提出的。Kaplan認為“每一種語言及其文化都具有獨特的修辭傳統,邏輯與修辭是相互依賴的,在特定的語言中思維與語法是互相聯系的”。同年,他發表了《跨文化教育的文化思維模式》這一奠基性文章,率先對母語的語篇結構和修辭方式在第二語言中的表現進行研究(楊玲,2002:1)。Kaplan提出假設:向美國學生(指英語作為第一語言的學生)和外國學生(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生)教授閱讀和寫作的方法不應相同。這一教學方法上的差別主要是由于修辭性質上表現出來的文化差異所致(胡曙中,1989:40)。同時指出:學生的第二語言創作會受到母語、文化、修辭模式和修辭傳統的影響(這影響主要體現在干擾方面)。Kaplan認為修辭模式不是普遍存在的,它是依附于文化而產生的,并將修辭模式歸納為以下幾種:英語的直線式模式,東方語言的螺旋式模式、閃族語的平行式模式、俄語的偏離式模式和羅曼語的拐彎式模式(見圖1)(穆從軍,2007,22)。
實際上,每一種語言都向其使用者提供了其對所處文化氛圍的現成的解釋。譬如像中國人在表達自己感想的時候會通常使用“我們認為/得覺……”這類的具有集體色彩的句子,這表示了中國人往往把作用于自身的感官印象主要以委婉間接的集體活動形式來表現,而美國人在表達自己觀點的時候不說“We think/believe…”,而以更為直接的表達方式“I think/believe…”,這里的差異源于印歐語系語言使用者與漢藏語系語言使用者文化傳統的不同。不同的文化傳統繼而影響到表達方式的不同,當然表達方式包括各種修辭的使用。由此可以說不同的文化傳統、不同語言的表達方式,會產生不同的修辭模式,而修辭模式對人們交際、理解和翻譯有一定的影響。正如Clayann Panetta所指出的,成功的交際不是天生的,也不是普遍的,而是文化的、修辭的。
二、翻譯研究概述
翻譯研究這門學科在20世紀后半期才正式出現:Holmes在1972年發表的文章《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首次提到“翻譯研究”。他主張把作為經驗科學的翻譯劃分為純理論的翻譯研究和應用翻譯研究兩大類。前者后來逐漸發展為理論翻譯研究和描述翻譯研究。理論翻譯研究包括翻譯訓練、翻譯輔助和翻譯批評三大應用分支。描述翻譯研究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功能、過程和導向上。總體說來,翻譯研究主要是對翻譯的理論與實踐進行系統性的跨學科研究。它的歷史較短,其理論基礎建立在許多其他學科上,其中主要包括比較文學、計算機科學、歷史學、語言學、文字學、哲學、符號學、傳播學、心理學以及認知科學等等,是一門歸屬于人文學分支的整合性學科。
塞萊斯科維奇指出,“翻譯的對象是借助語言表達的意義,而不是語言本身”,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翻譯的對象是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之間所要表達的意義,在這個過程中語言只是一種必要的媒介。翻譯的任務和目的是成功地促成交際(對于目標語言的使用者來說,一個好的翻譯除了要保留原有的意思外,還應該要能像是以母語使用者說或寫得那般流暢,并要符合目的語的習慣):把一種熟悉的語言信息轉變成另一種原本不熟悉的語言信息的活動。它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問題,尤其涉及兩種不同語言和文化的比較研究。楊自儉曾指出“翻譯是以符號轉換為手段,意義再生為任務的一項跨文化的交際活動”,作為意義再生的跨文化交流活動的翻譯,首先“需要克服的是其語言障礙”(許鈞,2003,76)。因為這些語言障礙通常是由文化差異而產生的,所以語言中所蘊含的文化差異就成為翻譯研究的主要對象,這里語言中所蘊含的文化差異當然也包括修辭模式、修辭方法及修辭傳統的差異。
三、對比修辭學與翻譯研究的關系
張會森在《修辭學通論》一書中提到:“對比修辭學的對象是翻譯藝術的規律。”“翻譯理論的任務在于揭示兩種語言功能上雷同的內在資源。揭示這種資源的科學應該稱為對比修辭學”。(張會森,2002:251)
費道羅夫指出:“翻譯理論作為一門語言學科,首先與修辭現象有關,因此它的基本點是語言功能和語言單位功能的概念、意義功能和藝術功能的概念。這些概念,對于以比較分析譯文和原文為其研究方法的對比修辭學的那一分支來說,也是根本性的概念,因為它的任務恰恰在于系統地描寫譯文語言,為充分再現原文語言單位所執行的意義功能和藝術功能而擁有的那些修辭手段和修辭潛力。”(李維琦,1984:35)
我國的對比語言學家在對比修辭與翻譯研究這些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嘗試。李定坤在《漢英辭格對比與翻譯》一書中通過全面、透徹地比較分析漢英辭格,提出了直譯、代換、意譯、直譯與意譯相合等譯法;袁昌明在《英漢修辭比較與翻譯》一文中從形合與意合、動態與靜態、人稱與物稱、主動與被動和復合與簡單五個方面對比了英漢語在表達方式上的差異,并論述修辭比較對翻譯的指導作用;朱麗田則在《英漢比喻修辭格的對比與翻譯》一文中分析英漢比喻修辭格的異同和翻譯技巧。(李東輝,2006:114-119)
修辭不是普遍存在而是依附于文化的,作為意義再生的跨文化交流活動的翻譯也受到文化差異的影響。文化即是對比修辭與翻譯研究兩門學科的聯系紐帶之一。雖然對比修辭與翻譯研究有著必然聯系,但對比修辭學家們的研究重點主要集中在第二語言寫作上,他們對翻譯研究的理論和研究翻譯的學者通常是不太熟悉的。同時,翻譯理論學家也似乎不清楚對比修辭學的發展。這種相互的無知是奇怪的,因為這兩類學科研究背景除了在文化上的共同之處外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相關之處,比如研究目的還有研究方法等等。兩者的研究領域都屬應用型而非理論型,它們所獲得的研究結果,可以直接用于解決一系列的實際任務如:翻譯,雙語書籍、詞典的編纂,外語教學等。因此,它們屬于語言學的應用學科。在某種意義上說,對比修辭學與翻譯研究用于各領域的實際目的是同樣的,譬如:對比修辭學幫助語言教學專家研究,而翻譯理論輔助翻譯家從事翻譯工作。無論是對比修辭學還是翻譯研究它們都以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為媒介,以語言間所要傳達的意義為研究對象。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由于受到應用語言學、人類文化學、認知心理學等學科理論的影響,它們理論研究的方法都經歷過變革。
對比修辭與翻譯研究的關系正如W.Marton在其論文《對比研究的教學啟示》中指出的“翻譯是一種典型的對比分析練習”。這里的對比分析當然是包括對比修辭學的。劉宓慶在他的《文體與翻譯》一書中專門留出一章談修辭,他談到:“翻譯學中的表達問題與修辭學關系十分密切,因為兩者都是探討運用語言的技巧。翻譯工作者要功于表達,絕不能忽視修辭學。”(劉宓慶,1998:536)由此可知對比修辭學與翻譯研究兩者之間相互聯系,互為促進發展。
四、結語
對比修辭學與翻譯研究都是比較新的研究領域,對比修辭學由Kaplan在1966年發表的《跨文化教育中的文化思維模式》中提出,而現代翻譯研究始于1972年Holmes’s的文章《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以上的評述完全有理由說明,對比修辭與翻譯研究是關聯的,它們有一些共性:都與文化息息相關,不僅具有共同的研究媒介即蘊含在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之中,而且具有相同的實用目的即正確理解文章,改進翻譯水平,促進第二語言寫作和完成交際目的。在近年的發展歷程中,對比修辭與翻譯研究都不斷吸收其他領域的新理論和新思想,拓寬了研究領域,它們相互融合的研究更有助于第二語言習得和寫作者了解和掌握目標語文化的修辭習慣和修辭取向,以滿足目標語讀者的閱讀期望達到翻譯目標,促進教學雙方的理解和溝通。
【參考文獻】
[1]穆從軍,對比修辭研究發展四十年綜述[J].修辭學習,2007(5):21-25.
[2]楊玲,對比修辭學:發展歷史與研究趨勢[J].外國語學院學報,2002(1):1-4.
[3]胡曙中,英漢對比修辭研究初探[J].外國語,1989(2):40-53.
[4]Ulla Connor,Contractive Rhetoric:Cross-Cultural Aspects of Second-Language Writing[M].Cambridge,CUP.1996:15-16,117-123.
[5]許鈞.翻譯論[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76-77.
[6]張會森.修辭學通論[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251-255.
[7]李維琦.對比修辭學與翻譯理論[J].外國語言學,1984(2):
34-36.
[8]李東輝,英漢對比研究的翻譯學視角[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6(4):114-119.
[9]劉宓慶.文體與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8:536-537.
[10]楊自儉.英漢對比研究管窺英漢語言對比研究[M].上海: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2000:45-47.
[11]朱余剛.20世紀國內英漢對比修辭研究綜述[J].贛南師范學院學報,2002(2):63-68.
[12]朱永生.鄭立信,苗興偉.英漢語篇銜接手段對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8-16.
A Survey on Contrastive Rhetoric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Liu Mingya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Hunan 411201,China)
第2篇:跨文化溝通論文范文
關鍵詞:文化傳遞模式;教學的概念
“文化”這個概念可以從三個層面加以闡釋:一是廣義的文化,即人類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二是中義的文化,是指精神財富的總和;三是狹義的文化,指生活于一定的文化共同體中的人們長期積淀而成的一套文化系統,包括價值觀念、思維模式、審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緒、民族性格等,其中價值觀念是核心。本文以狹義的文化為出發點,來研究文化傳遞方向與教學概念的演變。人們對世界有什么樣的價值觀念,就會以相應的方式表現出來,教育領域也不例外。對于“教學”概念的不同界定,就是人們在某種價值觀的支配下所做出的有意識的選擇與取舍。不同的文化傳遞模式影響著教育的價值取向,也影響著人們對于“教學”這一概念的認識。
美國文化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ead,M.)從文化傳遞模式出發,將人類文化劃分為三種基本類型:后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同喻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和前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后喻文化是指晚輩向長輩學習,同喻文化是指無論晚輩還是長輩的學習,都發生在同輩人之間,而前喻文化則指長輩反過來要向晚輩學習。梳理教學概念的歷史演變,可以看出,這三種不同的文化傳遞模式影響著人們對不同時期“教學”的認識和表述。
首先談談“教學”概念的詞源學釋義。在中國古代,“教”有“教授、教誨、教化、教訓、告誡,令使等含義。”[1]“教”字最早見于甲骨文“敎”,表示用鞭打的方式迫使孩子學習。它是指一種外存文化的灌輸,且使用了強制性的手段。《說文解字》中解釋道:“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深入分析,“其‘施’,就是操作、演示,即傳授蓍占和龜卜;其‘效’,就是模仿、仿效,即學習蓍占和龜卜。”[2]它含有“仿效前人經驗”的意思。
“學”的古體寫法為“學”,其上部為左右兩手結網之形,“結網為復雜之技能,非傳授不能獲得。”“學”就是“獲得”的意思。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學”字可以表示用手把孩子頭上的雜草除去,具有“使人聰慧”的意味。[3]《說文解字》曰:“斆,覺悟也”。《禮記》中說:“學者,覺也,覺民者”。 “學”就是使人覺悟,使人返回到原來的本性。可以認為,“學”在字義上具有獲得知識經驗,啟發人生智慧的意思。
“教學”二字連用為一詞,最早見之于《書·商書·說命》:“斅,學半”。意思是“教人乃益己之學半”。教人謂之學者,學所以自覺,下之效也;教人所以覺人,上之施也。《學記》引用它作為“教學相長”思想的經典依據,來說明“學,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強也。”《禮記·學記篇》:“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這里“教學”之意為“教人學”,即統治階級利用“教”的手段,使老百姓愛好學習,進而學會明白事理,以達到淳風化俗、安邦治國的政治目的。
“教”在英文中為teaching或是 instruction,兩者區分不大。嚴格說來,teaching涉及整個教學情境中的師生互動關系,范圍較廣,包括計劃、準備教材、評價等全部教學活動。 Instruction范圍較窄,專指在教室中所執行的例行技能之訓練。teach的字源有四種意義: 1.lore:為learn的字根,指用來被教的事實與信念,早期的teach與learn相同。
2.token:使用信號或符號,向某人展示某事物,或引發某人對于特定人或事物的反應。
3.imparting:給與資訊,向某人展示如何做及進行某科目的練習等。亦即由外向內地傳授。
4.inquiry:有計劃地提供學習者探究的模式。指師生間進行教育性的論辯,討論有意義的議題。[4]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論中外,“教”的基本含義是一致的,即“傳授”、“教導”和“教授”。而“學”字,無論是在中文還是在英文中,基本含義均為“學習”。可是,在人類歷史浩瀚蒼茫的長河中,隨著文化傳遞方向幾經變革,“教學”的概念也發生了轉移與更迭,超越了它的原初意蘊,被人們賦予了更多蘊涵、更深層次的意義。
一、后喻文化──教學:知識傳授說
后喻文化是一種面向過去的文化。正如米德所說的:“長輩的過去就是每一新生代的未來,他們已為新一代的生活奠定了根基。”后喻文化是一種世代復制的文化,“所有文化的連續性至少有賴于祖孫三代”。[5]人們世代相傳形成了封閉保守、認同過去、缺乏變化的文化傳統。米德認為,典型的后喻文化是孤陋寡聞的原始文化。但是也有人認為,整個農業社會都可被認為是屬于后喻文化的傳遞模式。[6]后喻文化的形成是與農業社會的經濟特征、傳統主義的思想特征息息相關的。
農業社會以單向封閉、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人們祖祖輩輩、世世代代地居住在相對固定的地理環境中,“生于斯長于斯”。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手工操作的生產技術和個人單干或家庭經營的勞動方式,決定了農業社會中教學的內容、結構和形式一直停留在相對較低的初期水平。農業社會的思想背景也呈現出宣揚穩定、排斥變化、提倡服從、壓抑個性的特征。其一,長輩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與權威,控制著社會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主宰著“教什么”即教學內容的選擇問題。其二,由于人們散居各地,重穩定性而輕流動性,造成了信息傳播的困難,遮蔽了人們了解世界的渴望和探索世界的欲求,族群中的晚輩始終處于一種被動無知的蒙昧狀態。
從教學的內容來說,主要是農業和手工業的操作技能。在中國歷史上,由于“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士之子桓為士”,“農之子桓為農”,“工之子桓為工”,“商之子桓為商”,貴族和知識分子主要從事腦力勞動,不需要技藝性教育和培訓。身份卑微的勞動人民為了維持與延續生產、生活及種族的繁衍,惟有憑借雙手將積累和獲得的生產經驗通過言傳身教一代代地傳給后人。[7]在學校教育中,長期以來沿用儒家經典著作《四書》《五經》作為教材,非常注重人倫道德教育,強調“三綱五常,禮之本也。”因為“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經也。”[8]在西方,隨著歐洲踏入中世紀的大門,披著“平等博愛”外衣的基督教迅速蔓延到整個歐洲,成為西方封建文化的主導。擁有知識壟斷權的僧侶們信奉教會的“服從”、“貞潔”與“安貧”三個宗旨,尊從神靈而鄙夷人性。“七藝”教育名存實亡,《圣經》成了涵蓋一切知識與真理的圣典。學校教育奉行禁欲主義,以殘酷的體罰壓制學生。
從教學的形式來說,農業社會更注重個別化的師傳徒受、子承父業、口耳相傳式的教與學。由于生產要素十分簡單,使得勞動者或其家庭熟悉和掌握各環節的操作技能成為可能和必須。生產的獨立性造成了“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晚輩們更多的是進行模仿和記憶,一代代復制著先輩們的經驗,延綿不絕。在西方,隨著農業經濟的發展和手工業的擴大,為了使生產經驗世代流傳下去,通常是上輩人在漫長的歲月中逐步教授后輩人,這種傳授主要是“學中干”和“干中學”,于是形成了“藝徒制”。學校教育采用灌輸注入式,要求學生死記硬背,堅信勿疑。正如《圣經》中耶穌命令的“凡我所吩咐的,你們都要謹守慎行,不可添加,也不可刪減”。無論中外,在教育發展的早期階段,都曾出現過影響后世的教學方法,如孔子倡導“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啟發式教學,蘇格拉底提出的“產婆術”等等,但是在后喻文化的傳遞模式中,這些方法畢竟不能成為主導力量,因此愈發顯得彌足珍貴。
針對后喻文化中教學的特點,我們不妨將這一時期的“教學”概念界定為:教學就是傳授知識或技能(Teaching is imparting knowledge )。[9]這種觀點是16世紀西方給教學所下的描述性定義,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教學的定義只是表明這個詞的運用范圍,“教學”的意思就是通過語言、符號、實物等向學生說明所教的內容,以激發學生的學習。他們覺得,鑒于這種定義不涉及教學過程中所采用的方式,如講授式或探究式,因而容易被大多數人所接受。事實上,在我國當代也有類似的觀點。如“教學,是教師把知識技能和熟練技巧傳授給學生的過程”[10];“教學就是經驗的傳遞。詳細點說,教學有廣狹二義。廣義的教學就是所說的經驗或知識的傳遞。凡是把知識技能傳授給他人的活動都叫做教學。狹義的教學,是指學校中教師把知識、技能傳授給學生的活動”[11];“教學一般分為廣義的教學和狹義的教學:廣義的教學是泛指那種經驗的傳授和經驗的獲得活動,是能者為師,不拘形式、場合,不拘內容,“父傳子”、“師傳徒”等活動。狹義的教學指的是學校教育中培養人的基本途徑,都是現在各類學校中進行的教學活動,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教學”。[12]誠然,教與學是通過一定內容為媒介而進行的。這種觀點強調了知識技能在教學過程中的中介作用,卻忽略了教學中的主體和對象問題,未能全面揭示教學的本質屬性。
二、同喻文化──教學:雙邊并合說
同喻文化是一種面向現在的文化。其基本特征是,全體社會成員以當今流行的行為模式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同喻文化緣起于工業文明時代的到來,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被轟鳴的大機器生產所替代。相應的,隨著人類社會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后喻文化傳遞模式也逐漸被同喻文化取而代之。米德認為“以同喻方式作為文化傳遞的唯一模式的社會寥寥無幾”,有論者曾對此提出質疑,他們認為:盡管各種類型的社會沒有一個只存在單一的文化傳遞模式,但是都有其主流的文化傳遞模式。如果說農業社會主流的文化傳遞模式是后喻文化的話,則工業社會的主流的文化傳遞模式是同喻文化。[13]
工業社會在經濟結構方面,存在著可與農業社會形成鮮明對照的基本特征,即標準化、專業化、同步化、集中化、集權化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結構中科技含量日益增多,其中心標志是技術裝備水平迅速升級,極大地提高了生產效率。由于機器的廣泛使用和工業的迅速發展,以前的“藝徒制”模式已經不能滿足生產對大量技術工人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集體性和大規模培養人才成為必需。而且,由長輩傳遞給后輩的現成經驗已經不能適應生產的變革,若想掌握更多知識和技能,人們必須向同輩學習,向現實學習。
從教學的內容來說,從與生產、生活毫不相干的人文知識改變為與現代大機器生產息息相關的人文知識與自然科學知識的結合,并特別突出了自然科學知識在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與工業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相對應,工業社會的教育是一種著眼于服務現實的制度化、規模化的教育。“制度化教育所帶來的是教育越來越專門化,……學校越來越像一個工廠,學校教育則成了生產工序,似乎未經生產便不成為社會的人。”著名的未來學家托夫勒(Tofler)曾說:“把大量學生(原料)聚集在集中型學校(工廠)里,由教師(工人)加工,整個觀念完全是工業社會思潮的表現。教育的整體管理等級是仿照工業官僚制模式發展起來的,把知識組成永久性的學科是以工業社會的設想為根據的。孩子們從一個地方轉到另一個地方,安排在指定的位置上,鈴聲宣告著時間的更替。年輕人剛走出這種教育機器,又走進工作、角色和制度等結構與學校相似的成人社會。在校學生們不僅僅學習日后可能用得上的知識,還學習并模擬過著一種他們未來將要過的生活方式。”[14]唐·庫什曼和杜·卡恩也認為,“各種活動模式與工業組織自上而下的流向并無二致,與‘裝配線式思維模式’也并無二致。在這種以權力為中心的制度下,師生關系是一種支配與服從、老練與幼稚、主動與被動的關系。”可見,工業社會中的教育被“異化”了,它不是為了教育本身,而是為了“適應”不斷擴大的資本主義生產的要求。
從教學的形式來說,這一時期產生了班級上課制,強調對同年齡學生進行同步調、同內容、同標準的教育,極大地提高了“教育工廠”的“生產效率”,同時也促進了學生的群體化生活及其相互的學習。在工業社會背景下,由于心理科學的快速發展,人們對于教學方法的認識也在不斷發展。如夸美紐斯強調教學的直觀性;赫爾巴特提出教學過程的形式階段理論,即:明了、聯想、系統、方法;杜威倡導“從做中學”,采用發現式教學;布魯納則著重教學要符合兒童的認知發展。同喻文化影響下的教學形式表現出實用主義傾向,重實際、重應用。
鑒于同喻文化中教學所表現出來的種種特性,我們可以將這一時期“教學”的概念界定為:教學即教師教和學生學的活動,既包括教,也包括學,并由教和學組成。美國教育哲學家杜威(Dewey.J)曾為教學概念作過十分形象簡明的比喻:教之于學猶如賣之于買,“教學”意味著教與學的雙方通過相互作用產生某種結果,教學就是要讓學習者掌握所教的東西。在《辭海》中,教學的定義是:“教學,指老師傳授和學生學習的共同活動”。華中師院等五院校合編的《教育學》:“教學是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所組成的一種教育活動”。[15]還有論者認為“教學是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所組成的雙邊活動”;[16]在有的教學專著中,對教學的定義也基本強調師生的雙邊活動,又如“教學是根據一定的社會的需要,按照確定的教育目的,通過教師的傳授和學生學習,完成教學任務的雙邊活動”。據此,人們給教學的含義作了一個簡要的概括即:教學是教師教和學生學,共同完成預定任務的雙邊統一活動。從表面上看來,這種說法似乎很合理,但是,教學作為一個有機的活動整體,教與學之間有著特殊的內在聯系,如果簡單地將其視為“教和學”的疊加物,豈不是忽略了作為其質的規定性之一的內在聯系?這種含義值得商榷。 轉貼于
三、前喻文化──教學:共同生長說
前喻文化是一種全新的以開拓未來為使命的文化傳遞模式。其傳遞路徑是:長輩向晚輩學習。年輕人按照自己的首創精神自由行動,他們能在未知的方向中為長者引路。前喻文化發端于后工業社會的來臨。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和未來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曾在1979年發表的題為《信息社會》的文章中明確提出:“即將到來的后工業社會,其實就是信息社會。”──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知識經濟社會”。以知識為基礎的信息革命正是后工業社會來臨的突出標志。后工業社會的特征可以概括為:知識的社會、服務的社會、公眾的社會。幾個世紀以前,弗朗西斯·培根就喊出了“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社會發展到今天,知識正變得愈加重要,它不僅是一種精神資本,更重要的是它已成為先進經濟的首要資本。由于知識不斷升值,“信息戰”(即爭奪對知識的控制)到處爆發。后工業社會中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其社會地位也不斷提升。
后工業社會在經濟結構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特征是,知識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成為社會變革的力量,并且改變了工業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后工業社會中,這種新關系的核心就是交流,對自我改變的反應和對各種要求的反應,是人與人之間的對話,而不再是工業社會中那種人與機器的交流,這正是信息社會──知識經濟社會來臨的標志。年輕一代的創新性在社會中起到重要作用,專門技術是取得權力的基礎,教育是取得權力的途徑,隨著知識的不斷普及,越來越多的人進入知識階層,他們通過知識來掌握權力,從而有計劃地對社會做出管理。但是,原來那種結構化的社會管理體制正在逐漸被網絡所消解,后工業社會帶來的網絡天地給人以充分的空間享受廣泛的民主與自由。教育更是如此,虛擬教學的出現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虛擬與現實相對應,是數字化方式的構成。它是虛擬世界在教學中的體現,即用數字化方式為人類提供虛擬教學空間或數字化的學習環境。在這樣一個日新月異的背景下,整個社會文化呈現出年輕化趨勢,“如果說工業社會逐步淘汰的是落后的機器的話,后工業社會所淘汰的將是落后的人(即無創造性的人)”[17]
從教學的內容來說,前喻文化倡導一種面向未來的“創新”教育。不僅要求學生學習一般意義的知識,而且要求學生學會如何對付飛速的變化,如何思考、決策和解決問題,如何造就自己的洞察力和創造性。托夫勒曾說過,在后工業社會中,“快速、易變和能自動調節的機器將處理信息流和知識流。……明天的技術需要的不是數百萬只有淺陋文化知識的人和在一起干無休止重復工作的人,需要的不是惟命是從,只知道自己活著就應該機械地服從上司的人,而是需要能夠當機立斷的人,能夠在新的環境中迂回行進的人,能夠在瞬息萬變的現實中敏捷發現和確立新關系的人。用C·P斯諾的話說,明天的技術需要的是‘骨頭里浸透未來’的人”。[18]可見,時代的變革迫使整個教育發生變化,教學內容也不例外。
從教學形式來看,面向未來的“創新”教育打破了學校教育與非學校教育之間的屏障,給人的學習提供了充分的時間與空間。網絡的普及使得信息的傳遞不再受到限制,教師與學生可以在相對寬松的時空內任意安排教與學的活動,教學趨向個性化和特殊化。“數字化生存之父”尼葛洛龐蒂( Negroponte,N.)在《數字化生存》一書中曾說:“在全球性的電腦國度掌握了政治領空之前,民族國家根本不需要經過一場混戰,就已經消失無蹤。……未來將越來越沒有國家的發展空間。”一種超階級、無國界的教育空間正在形成。在基于網絡的學習中,學生的主體性得到了充分的彰顯,師生關系得以重新建構,亦師亦友,平等對話。通過對話,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中介都參與到教育中來,構成“我—你”式的在場相遇,對話是一種商談,體現師生平等的關系,也是對民主精神的宣揚和民主能力的培養。[19]
前喻文化中的教學以“創新”為使命,筆者對這一時期教學的概念進行了界定。教學,就是促進教師與學生共同生長的一種活動。交流是實現師生互動的前提,教學活動本身不但是一種尋求對話的實踐活動,也是一個信息交流的過程。無論是學生知識經驗的獲得、心智的開啟、能力的發展,還是教學活動質量的提高,都有賴于教學中信息的有效傳遞和交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前喻文化的傳遞模式中,信息交流是教學活動的中心,信息交流的成效決定著教學活動的效果。只有實現了教學中人與人之間、人與環境之間自由的信息交流,才能真正實現師生互動與對話。這種師生互動是雙向的,既有教師對學生行為和發展的影響,也有學生對教師行為和發展的影響。后喻文化中的灌輸式教學和同喻文化中的獨白式教學意味著教師總是高高在上地俯視學生,充當著教學活動的主宰,可以說,教師和學生是相對立的;而前喻文化格外重視師生之間的對話,承認他們各自的內在價值和權利,因此,教師和學生是統一起來的。
在后工業社會背景下,教育的終極目的是促進人(教師與學生)的生長。這里所說的人的生長,即是指人的持久發展,而“人的持久發展應被理解為通過提高人的所有活動的質量取得的進步”。[20]對于學生而言,教學活動是其學校生活,乃至整個人生中的重要部分,它影響著學生的成長與發展;對于教師而言,教學是其職業生活的最基本的構成部分,它影響著教師對職業的感受、態度和專業水平的發展、生命價值的體現。因此,教學活動無論對于教師還是對于學生,都具有個體生命價值,蘊含著巨大的生命活力。師生的這種生命活力只有在教學活動中得到有效開掘,才能真正有助于新人的培養和教師的成長。
從師生關系來看,前喻文化更注重教師與學生的相互學習,強調民主平等,對話交流。古人云:“師無常師”。這句話在前喻文化的教學活動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教師的作用沒有被拋棄,而是得以重新建構。從外在于學生情景轉向情景共存。教師是內在情景的領導者,而不是外在的專制者。”[21]教師亦可以向學生學習,共享共創,教學相長。共享是教師與學生共同體驗和分享教學中的歡樂、成功、失望、不安;共創是教師與學生在相互適應的基礎上互相啟發,使師生的認識不斷深化。共享共創的結果是教學相長,教師和學生共同發展。
關注師生互動,就會注重交流;關注師生發展,就會在教學中創造、更新與適應。“課堂活動不僅僅是一個教學活動過程,而且還是師生生活與成長的過程,是師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經歷,是他們生命的有意義的構成部分。”[22]只有真正關注“人的生長”,挖掘人的生長功能,不斷地催生教學的動力資源,營造一個和諧穩定、積極良好的氛圍,才能使教師與學生在學習知識技能的同時,體驗到學習是一種享受,一種快樂,一種幸福,一種心靈的充實,一種情感的交融和一種生命的延續。
毋庸置疑,社會在發展,教育也在發展。今天的教育不僅要復制過去、適應現在,更要面向未來。教育概念的變化標志著人們思想的深化,當代的新觀念認為,教師活動中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主宰者”,而是“平等中的首席”(first among equals),教學不僅僅是“教”也不僅僅是“學”,而是教與學的統一,教溶于學中,而學有教的組織引導。發展到今天,教學概念涵括了教師的教授、學生的學習與師生的互動教學。
注釋:
[1] 王靜:《試論〈說文解字〉中的“教育”二字》,《教育研究》1995年第3期,第48至52頁
[2] 何啟賢:《也說“教”“育”二字》,《教育研究》1995年12期,第64至68頁。
[3] 石中英:《“教育”概念演化的跨文化分析》,《高等師范教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8至22頁。
[4] 參見: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教育學系方永泉副教授2005年11月的講稿。
[5] M·米德:《文化與承諾──一項關于代溝問題的研究》,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28頁。
[6] 張義兵:《文化傳遞模式與教育價值取向:一種社會學分析》,《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9月第5期。
[7] 張志增:《試析農業社會中職業教育與主要相關要素的關系》,《職業與教育》2005年第14期。
[8] 王炳照,閻國華:《中國教育思想通史(第3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54頁。
[9] 《簡明國際教育百科全書·教學(下)》,教育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34頁。
[10] 《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第504頁。
[11] 楊鴻昌:《教學心理講話》,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
[12] 劉克蘭:《教學論》,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第63頁。
[13] 張義兵:《文化傳遞模式與教育價值取向:一種社會學分析》,《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9月第5期。
[14] 唐·庫什曼等著:《人際溝通論》,北京,知識出版社1989年,第178至179頁。
[15] 華中師院等五院校合編:《教育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頁。
[16] 孫震、吳杰著《教育學》,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頁。
[17] 張義兵:《文化傳遞模式與教育價值取向:一種社會學分析》,《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年9月第5期。
[18] 唐·庫什曼等著:《人際溝通論》,北京,知識出版社1989年,第181頁。
[19] 蔡春,扈中平:《從對話到獨白──論教育交往中的對話》,《教育研究》2002年第2期。
[20] 國際21世紀教育委員會報告:《教育──財富蘊藏其中》,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頁。
[21] 陳桂生:《師道實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4頁。
[22] 葉瀾:《讓課堂煥發生命活力:論中小學教學改革的深化》,《教育研究》1997第9期。
參考文獻
[1] 胡小林,袁伯誠. 中國學習思想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2] 陳桂生.教育原理[M] .華東師大出版社1993年.
[3] 阿爾溫·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年.
[4] 戈登?德萊頓,珍妮特?沃斯 著:《學習的革命》,上海三聯書店,1997年版
[5] 陳時見.課堂管理論[M]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6] 霍力巖.論教育特征的變化──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教育科學研究,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