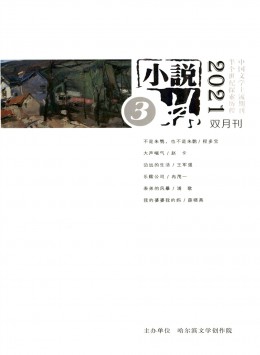雁翼小說時代性根源探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雁翼小說時代性根源探究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雁翼在小說中塑造的多是普通勞動者形象,有鐵路修建戰線上的工程師、勘測員,還有駕駛著大卡車奔馳在巴山深谷里的女司機,有礦井煤山中的女護士、老礦工、操作員等。雁翼正是從這些身份普通、事跡普通、外在形象并不高大甚至有的還有殘疾的人物身上,挖掘出其所代表的時代精神。
一方面,雁翼并未以新時代英雄主義敘事來書寫工人生產勞動中的英雄事跡,他關注的是普通勞動者的日常工作場景、人生經歷等。《腦云錐上》描寫了老工程師周建和勘測員劉洪在被稱為腦云錐的深山中,艱難地進行勘測的場面;《帶路的老人》講述了曾兩次勇走“斷頭巖”給紅軍送信和保護紅軍撤退的老游擊隊長,如今50多歲了,為不耽誤修路工程進度,再次抄近路冒險帶領發電機手攀越懸崖陡壁;《唱歌的人》中刻畫了一個礦山女護士白真,當她遠赴南海前線的未婚夫生死未卜之時,她依然堅持以歌聲和微笑給礦工們帶去熱情和力量。這些身份普通的勞動者從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出發,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職盡責,無私奉獻,雁翼以這些普通人來折射時代精神的投影。
另一方面,與17年時期的工業題材小說潮流不同,雁翼在小說中沒有以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的二元對立來突顯英雄的豐功偉績。雁翼筆下的建設者幾乎沒有反面形象,他們身上所凝聚的時代精神都是作者所肯定的。雁翼從人物的人生經歷出發,去探尋其時代精神的源頭,他筆下人物解放前后身份的變化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由解放前的軍人到解放后的建設者,一類是由解放前的受壓迫者到解放后當家作主的新時代工人。對于前者來講,對以自己和無數戰友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新社會,定會倍加珍惜,做一名新時代的奉獻者。《我的戰友》中的田耕耘、《成熟的季節》中的劉建東均是如此,他們承擔起新時代的戰斗任務,把在戰場上不畏強敵、拼搏到底的戰斗精神繼續發揚和延伸。而對于后者來說,新社會使他們的命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老夢大叔》中的老礦工王樹槐、《燈》中的礦工鄒洪等是此類人物的代表。舊時代給他們的身體帶來了殘疾,新時代下他們身殘志堅,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生與死的斗爭,血與淚的磨練使他們認識到命運變化的原因,而政治、經濟地位的提高是他們在翻身解放后具備無私忘我勞動精神和積極進取精神的內在動力。雁翼巧妙地將這些平凡建設者的日常工作刻畫出來,緊緊抓住時代給每個人心靈打下的烙印,使讀者在平凡中感受人物神圣的靈魂。正是這些默默堅守在祖國建設最前沿的普通人構成了新中國建設的主力軍,他們為祖國的建設貢獻著一己之力。他們是平凡的時代英雄。“他的作品講述的是普通人的故事,卻又是實實在在的英雄和模范等先進人物的故事”[3],正所謂平凡中的偉大。誠如魯迅所言“:戰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4]
80年代初期,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提出和寬松政治文化環境的出現,對新時代下新思想新人物的書寫成為當代文學創作者的普遍追求,改革文學成為此時的主流。從80年代初期開始的以《喬廠長上任記》為代表的對大刀闊斧的改革者的描繪,到80年代中期以《魯班的子孫》為代表的對農村變革的艱難和伴隨的道德失落的表達,再到90年代以《分享艱難》為代表的對城鄉變革、社會轉型的書寫,構成了改革文學的主脈。有著8年深圳生活經歷的雁翼,帶著自己“豐富的感受”,在90年代中期創作了短篇小說集《深圳奇情錄》,成為改革文學大潮中一股獨特的細流。
首先,不同于多數的改革文學作品,雁翼沒有采用“改革———反改革”的主要模式,沒有把改革的重重阻礙作為主要矛盾點,沒有塑造大刀闊斧的改革者形象。他著眼于這場大變革引起的人的心靈變遷及其帶來的多重影響。“而文學家要思索的是心靈的事,那沉藏在社會變革深處的心靈活動是異常豐富的,它可能比社會變革的表層要豐富十萬倍!”[5]在雁翼筆下,改革開放為眾人實現追求和夢想提供了機遇,同時其博大包容的時代內涵成為喚發人性美的源泉。雁翼筆下的經濟特區成為尋夢者的理想之地,《太行山的兒子》中的農民邵仲山、《汪梅嫂子》中的汪嫂、《學不會的愛》中的黃玉都在這里成就了自己的人生追求……然而雁翼更關注的是這些人在改革開放時代氣息熏陶下表現出的靈魂深處的人性美。被村里趕出來的邵仲山不計前嫌帶著自己的養殖技術和全部資本,回到家鄉帶領父老鄉親走致富之路,女知青吳曉蘭沒有記恨當年人們的陷害和冷眼,隱藏下自己對邵仲山多年的情感,還拿出了自己的8萬元積蓄支援他回村辦廠;汪嫂在認子遭到拒絕后將自己辛苦拾荒掙來的20多萬元和全部的母愛給予了她收養的殘疾孩子……雁翼以這些人物的善和美證明著時代的力量,詮釋著中華文明傳統的博大、包容的精神在改革開放時代的新內涵。同時,在雁翼看來“1979年以后的改革開放的基本成果則是:把敵變成友、把仇變成親、把恨變成愛”[6],他在小說中以“變”來彰顯時代力量。親歷過多次政治運動的雁翼對運動中的“敵人”在改革大潮中的命運格外關注,這是一種創作視角的突破。他的筆下出現了一個復雜的改革者群體,有解放前的國民黨軍官,有時期的階級敵人,有被改造的勞改犯。他把這些“敏感人物”放在改革開放的大背景下,關注他們的思想、情感在時代變革中的轉變。《親與仇》中孫紹生從原國民黨軍官到新時期的美籍實業家,再到與曾經是戰場上的敵人周明山結為親家,他們有過仇視、疑慮、退卻,然而兒女深厚的愛和建設祖國的共同心愿終使兩位仇敵化解前嫌。《悔心和尚》中的曾是侵華日軍的小野,戰后出家為悔心和尚,后又把自己曾經是戰場上的敵人、此刻的救命恩人王景槐雕成神象,供春香火。治病救人的博愛精神和追求和平的時代氣息化解了戰爭的怨仇,使敵化為友。《鬼魂之光》《戰友之間》《尋找味覺》等多篇小說都是對這一主題的詮釋。雁翼在小說中突出了時代給人物心靈帶來的這種“變”的力量,從而化解了歷史帶來的戰爭仇恨、階級仇恨,包容了政治立場的對立,消除了歷史遺留在內心深處的傷痛。
其次,與多數的改革文學作家一樣,時代風浪的沖刷和歷次政治運動的磨練使雁翼對時代的書寫不再僅限于前期小說中單純地頌揚,而是多了一層思索和憂慮。在深圳他看到了經濟的快速發展,體驗到了開放包容的時代環境對人心靈的改善,但也感受到了改革的艱難和阻力,認識到了金錢對人心和道德的腐化。在這個思想大解放時代,人的思想觀念受到所謂西方文明的沖擊。在金錢至上、經濟利益至上等畸形觀念的影響下,許多人的愛情、理想、事業都成了金錢的附庸,對這些改革“問題”的展示和思索也成為雁翼小說的一個主題。《酒店秘史》《孔雀回飛》《楊柳傳奇》等作品中愛情、婚姻成為獲取經濟利益的手段,男女間的情感關系完全建立在金錢利益之上,最終“在金錢中倒下”[7];《越攪越苦的咖啡》中女主人公在生活重壓之下把給富商做情人作為無奈之選,這種生活方式的選擇使她在真愛面前無地自容,只有以死逃避;《飛來的百萬富翁》則以戲劇化方式寫了一位公司黨委書記在以合法方式獲得股票投資巨額收益后一家人的苦惱和命運起伏。“我心里一陣暗痛”[8],是作者為人物的悲劇收場而痛,也是為改革開放這一社會轉型期出現的不和諧之音而痛。作者以這些人物的悲劇命運展示了人們在金錢誘惑下價值觀、愛情觀的迷失,并在其中寄寓了作者對時代變遷自覺而深沉的思索。綜上可見,雁翼小說中并未對中國當代社會歷史進程予以完整呈現,也沒有描繪重大歷史、政治事件,而是以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為關注對象,以人的心靈變遷為切入點,通過歷史與現實的對照,發掘人物的時代精神,思索時展方向。雁翼正是以這種獨特的方式來表達他對社會、對時代的關注。
雁翼認為“一個作家,寫什么與不寫什么,他的個人經歷起著決定性的支配作用”[9]。雁翼是時代變遷的親歷者,他不到11歲參加抗日活動,15歲參加八路軍,16歲加入共產黨,一路從戰火硝煙中走來,曾三次負傷,戰士們的英勇無畏、老百姓的積極擁護“成了激勵的動力、生活的源泉和作品的底色”[10];解放后,轉業到西南鐵路工程局,成為寶成鐵路修建大軍中的一員;60年代初因詩歌問題遭受批判,被下放到工礦勞動改造,他奔波于深山峽谷、煤山礦井中,深入到工人群眾勞動的第一線,被建設者們的英雄風貌所感染;時,下牛棚,關監獄,挨批斗,經歷著十年浩劫帶來的身心摧殘,他沉思,他憤懣;后成為一名文藝工作者,辦報紙,辦雜志,從事專業寫作;改革開放后,來到深圳,并常作為文化使者走出國門,感受著新時期的發展變化。豐富的人生閱歷給予了他豐厚的生活積累和生命體驗,為他反映現實、把握時代脈搏提供了可能。他本人也有意識地積累生活,為創作出緊貼時代的作品,他常到各地去考察采訪,多次回到故鄉,并到經濟特區生活8年。他說“我常常思索,我所以能夠從事文學創作,完全是社會的現實生活對我‘塑造’的結果。”[7]
作家生活的社會與時代,只為其創作提供了可能的素材,要成為小說的內容,還必須與創作者主體相融合。而創作者本身文化結構的差異性,必然導致其觀察生活視角的不同,那么作品反映出來的生活也是不同的。而對于文學來說,其價值更多的體現在創作者在自身文化積淀影響下的思維過程和表達方式。只讀過13個月書的雁翼并未受過系統教育,他的出生地河北館陶,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文化的聚集地,古樸的文化氣息浸潤了雁翼的思想;伴他長大的衛河流域,流傳著許多反映現實、關注民生的民謠,本家老奶奶更是以民間說唱的方式向他講述著自己悲慘的身世和人間真善美,這開啟了他感知社會、關注現實、敏銳捕捉愛與美的心靈之眼;他小學時的許老師以蠶啃嚙桑葉的形象方式對其進行的愛國主義教育,在兒時雁翼心里播下了抗日思想,引領他一生關心祖國命運。雁翼一直堅持著讀書的習慣,每天總要讀三四個小時的書,讀的書多而雜,有古典小說、詩歌,也喜歡通俗文學、民間故事、野史、地方志,這些作品引發了他對歷史發展中人民命運變化的思索,由此積淀下了濃厚的民族意識和底層關懷精神,也為形成他的現實主義創作觀奠定了基礎。雁翼是一直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的。“從我學習文學起就接受現實主義并且一直堅持”,正是在這種創作觀念引導下,他始終關注著社會現實的變化,有頌歌、有批判、有憂思、有呼喚:對戰斗英雄的頌揚、對普通建設者的贊歌、對改革者的思索、對世界和平的呼喚、對生態環境問題的憂慮……社會發展與時代的變遷在其作品中得到現實主義地體現。“他60年的文學創作生涯貫穿了中國當代文學整個發展歷程。中國當代文化歷次變革都在雁翼創作中留下了痕跡。”[12]
雁翼是一位有大愛情懷的作家。他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受到研究者的關注和文學界的普遍認可。“雁翼最值得我們踐行的是他的責任和擔當意識。”[13]他關心青年的成長,對于文學青年的求教,他都會給予熱情的鼓勵和積極的幫助,跟無數的文學愛好者書信來往,給他們修改作品,免費發表和出版作品;他關注中國文學的發展,結束后,克服多重困難,主持創辦多家文學刊物、報紙,為文學的復蘇和發展提供陣地,并積極參與組建世界華文詩人協會;他致力于世界文學交流,多次參加世界詩人大會,與世界各國詩人交流創作方法,推動世界文學的發展;他珍愛和平,在世紀之交,主編了《世界和平史詩》,包含了世界104個國家的107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對世界和平的美好祝愿。崇高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使雁翼代時代立言,對現實生活密切關注,發掘其間的時代精神,為當代生活留下真實的寫照。
由此可知,責任感和擔當意識使雁翼自覺地以小說記錄當代社會的發展變遷,傳統文化、地方文化的熏陶和書籍中獲取的文化氣息形成了他獨特的文化素質和感受時代的敏銳思想,人生經歷豐富了他的創作題材,賦予了他獨特的審美視角。通過書寫時代賦予普通人的時代精神把握時代特征,以人物心靈變遷表現時展,在人物的命運變化中思索時代前進之路,這種獨特的時代性使雁翼小說在當代文學體系中別具一格。(本文作者:王偉 單位:邯鄲學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