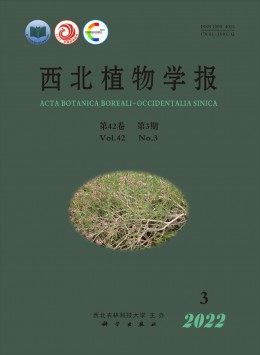植物學教學中數據庫的應用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植物學教學中數據庫的應用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傳統的植物學教學已不能適應植物學科的發展要求,也不適應當代學生的學習特點.依據植物學不同部分的特點及不同網絡數據庫的結構和資源類型,采用多種數據庫輔助教學的方法開展植物學教學.實踐表明,這種結合了數據庫的教學方式資源豐富,方法靈活,能適應學科發展和學生特點,教學效果好.同時,這種教學過程也為學生的后續學習和科研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關鍵詞:植物形態解剖;植物分類;大數據;教學改革
植物學是各綜合大學和農林類院校生命科學、林學、農學和環境科學等專業的專業基礎課,在學科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1-2].植物學教學質量直接影響植物生理學、生態學和遺傳學等各學科的學習和教學.傳統的植物學教學以課堂講授為主,配合一定量的實驗和實習課程.課堂講授一般以教材為主,應用ppt講授并結合一些掛圖、模型等[3].實驗課一般在室內觀察模型、實物和切片,以增強學生的感性認識[4].然而,隨著新時代植物學科的高速發展和學生思維、學習特點的改變,傳統的教學方法越來越難以滿足教學和學習的要求[5].我國的植物學教材一般知識比較系統,注重知識結論的穩定性.這固然具有系統完整、便于學習的優點,然而近幾十年來,植物學科的發展極為迅速,植物學知識的積累也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大量新理論、新知識和新技術不斷涌現.而教材更新和修訂的速度遠遠比不上學科發展的速度,這導致課本知識和學科發展脫節,嚴重影響學生后續學習和繼續深造時的研究能力[6-7].此外,現在的大學生是在網絡信息時代成長起來的,很難適應傳統的課堂講授,更習慣也更善于通過網絡、手機等方式獲取大量的知識和信息[8].基于植物學教學面臨的挑戰,將數據庫與大數據引入教學過程,以期獲得更好的教學效果.
1數據庫在植物形態教學中的應用
植物學形態解剖部分的知識體系龐雜,知識點瑣碎[9].由于生活經歷和學習歷程的限制,多數學生對植物形態解剖知識缺乏直觀認識,而課本提供的信息又明顯不足.如陸時萬的《植物學》[10]中對植物分枝類型的講授,主要包括了二叉分枝、假二叉分枝、單軸分枝、合軸分枝和分蘗5種類型.課本通過手繪模式圖的方式展示了這幾種分枝的基本形態,然而模式圖和實物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在教學中發現,學生在學習時似乎明白了這幾種分枝類型,然而在實驗和實習中發現學生很難在實踐中區分這幾種分枝類型.馬煒梁的《植物學》[11]中有一些彩色照片,相較于模式圖更為形象.然而,除了完全由彩色照片組成的教材比較貴以外,課本中能容納的照片數量比較少,而且為了達到說清理論的目的,教材中選用的照片都是比較典型的,這導致學生依然難以在實踐中明白分枝類型的差異.基于此,建立了植物形態數據庫,并將此數據庫鏈接共享給學生.在此數據庫中,包含了50個科,200余個屬,500余個種的植物形態圖譜.每種分枝類型都有大量不同種類植物不同形態的分枝,這些植物即使分枝類型大體相同,也會有眾多差異,能使學生更好地理解分枝類型的準確內容.如很多槭樹屬(AcerLinn.)的植物是假二叉分枝,但是在同一植株上,也能發現一些單軸分枝的莖;又如紅丁香(SyringavillosaVahl)、金剛鼠李(RhamnusdiamantiacaNakai)和東北山梅花(PhiladelphusschrenkiiRupr.)都是假二叉分枝,然而它們形成假二叉分枝的原因有的是頂芽變成花序(紅丁香),有的是頂芽變成枝刺(金剛鼠李),有的是頂芽停止發育(東北山梅花).學生通過觀察數據庫中大量不同植物的分枝,對分枝類型的理解明顯加深.
2數據庫在植物解剖教學中的應用
相比植物形態部分,植物解剖部分更難以被學生理解.首先,植物解剖知識距離學生的經驗更遠;其次,解剖知識龐雜而豐富,往往需要將理論和感性知識緊密結合.如植物器官往往需要根據其解剖特征進行定義.在教學中,當教師說芹菜(Apiumgraveolens)吃的主要是葉柄時,即使學生能夠“相信”教師的講授,卻也很難理解為什么這個部分是“葉柄”而不是“莖”.此外,為什么仙人掌(Opuntiadillenii)的刺是葉,為什么文竹(Asparagussetaceus)綠色的部分是莖而不是葉,為什么假葉樹外觀看起來和葉子非常相似的部分是莖,這些知識雖然像“常識”一樣很容易被學生“記住”,但學生要想理解卻有一定難度.吳國芳和陸時萬的《植物學》[12]中,對葉和莖的初生結構進行了詳細而準確的講述,并繪制了模式圖.由于葉柄是葉的一部分,所以葉柄的解剖結構是背腹式的,或者說是兩側對稱式的,而莖在解剖結構上是輻射對稱式的,但這種知識需要大量觀察實際的解剖結構才能掌握.應用建立的植物解剖結構數據庫,學生可以觀察大量植物不同器官的解剖結構,理解表面差異巨大的器官、組織和細胞直徑的關系,理解植物個體發育中不同器官的本質差異,進而獲得對此類知識的深刻理解.
3數據庫在植物分類教學中的應用
近20年來,植物分類學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量傳統的知識、技能和體系都進行了徹底的更新,國內外相關的數據庫也紛紛建立起來[13].然而,絕大多數國內的教材仍然使用舊的知識體系,嚴重阻礙了學生對新知識的學習和掌握.從2001年被子植物APGI分類系統發表以來,以分子生物、分支分類信息和生物統計為基礎的現代植物分類系統建立后,這種新的分類系統已經成為國際學術界的主流,大量新的研究成果紛紛涌現,國際上的植物學教材也紛紛使用新的分類系統.目前,新系統已經出版到第4版,然而絕大多數國內教材依然使用較老的分類系統,使用新系統的很少.如馬煒梁的《植物學》[11]、吳國芳和陸時萬的《植物學》[12]使用的是克朗奎斯特系統,汪勁武的《植物分類學》[14]使用的是哈欽松系統等.此外,由于大量研究的深入,植物學名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植物學中的大量學名已經修訂,成為“過時”的學名.然而依靠傳統的教材和參考書籍難以使學生掌握最新的知識[15].在植物分類部分的教學中,充分利用已有的數據庫進行補充教學.這些數據庫主要包括:中國植物志網絡版和手機版,其內容不但包括植物的學名、文獻考證、形態描述和地理分布等,還包括部分植物的彩色照片[16].這些照片質量高,鑒定準確,是學生學習和教師教學的好材料.中國植物志的英文版也可以在線查詢,其中約1/3的學名已經修訂[17],對于學生了解較新的知識幫助很大.但是FOC網絡版中圖片和文字是分開排列的,學生使用時稍有不便.中國國家標本平臺(NSII)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網站,已經收錄了大約1400萬標本數據[18].教學中,學生幾乎都可以在手機上通過這個網站查到教師講到的植物種類、標本照片和海量標本記錄.中國自然標本館(CFH)中收錄了大約1億幅植物的彩色照片,資源極其豐富[19].除了這幾個數據庫外,部分利用這些數據庫開發的軟件也是學生學習的重要幫手.如花伴侶、形色和生物記等軟件.這些網絡資源特點不一,各有特色.在教學中,需要教師通過講解讓學生了解不同資源的不同特點,否則學生在學習中的使用會遇到各種問題.花伴侶等軟件在植物開花時識別較準確,但是沒有花、果等器官時,其識別的準確率明顯降低.中國植物志網絡版可以使用拉丁學名或者中文正名進行檢索,但是不支持俗名檢索,很多學生在使用時會遇到因為不知道正確名稱而無法檢索的情況.
4教學效果評估
新的時代是網絡的時代,是數據的時代.當代學生思維活躍,對新技術、新方法適應迅速.應用數據庫等網絡資源的教學既可以充分適應學生的特點,又可以使學生較好地掌握學科發展中出現的新知識、新理論,是傳統教學方法和體系的重要補充.在實踐中發現,使用新的教學方法作為補充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學生自主學習的動力和能力.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教學過程的訓練可以使學生在植物學課程結束后,開始其它課程學習或者后續的科研活動,能夠獨立完成相關知識的檢索和使用.無論學生還是后續課程的教師都能感受到這種變化,說明這種教學方法是有效的.
參考文獻:
[1]趙杏花,燕玲,藍登明,等.植物學實驗教學改革探討[J].內蒙古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3(1):170-171
[2]苗芳.高等農林院校植物學課程教學方法探索與實踐[J].安徽農業科學,2011(36):22907-22909
[3]陸嘉惠,王紹明,吳玲,等.CAI課件在植物學多媒體教學中的應用探討[J].黑龍江生態工程職業學院學報,2009(3):109-110
[4]李孫文,趙昶靈,劉勇,等.農業院校植物學實驗教學改革的思考與實踐[J].云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69-74
[5]陸嘉惠,周玲玲,馬淼,等.提高植物學實驗教學質量的探討[J].兵團教育學院學報,2006,16(4):63-64
[6]白志川,王海洋,李先源.《植物學》課程建設的實踐與探索[J].教師教育學報,2005,3(1):130-132
[7]胡國雄,耿彥飛.植物系統學教學體系改革探討[J].綠色科技,2019(3):248-249,252
[8]申康.新一代大學生的特點分析及教育方法探討[J].科技信息,2011(27):174
[9]朱雪云.植物學形態結構理論教學思路創新初探[J].武漢生物工程學院學報,2011(3):211-212
[10]陸時萬.植物學(上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11]馬煒梁.植物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12]吳國芳,陸時萬.植物學(下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13]雷鮮,章懷云.植物分類研究進展[J].湖南林業科技,2005(6):55-58
[14]汪勁武.植物分類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15]高潤梅,王衛鋒,葛麗萍,等.植物學類課程產學研互作模式實踐教學的探索——以山西農業大學林學專業為例[J].中國林業教育,2019,37(3):44-46
[16]中國科學院《中國植物志》編委會.中國植物志[M].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
作者:董雪云 王洪峰 單位:哈爾濱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