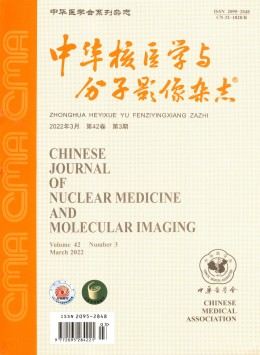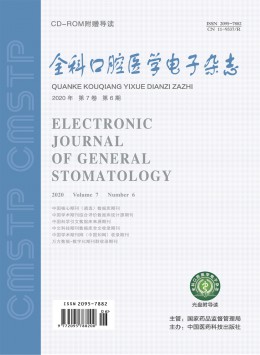口腔鱗狀細胞癌發病及轉移機制研究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口腔鱗狀細胞癌發病及轉移機制研究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摘要]口腔鱗狀細胞癌(oralsquamouscellcarcinoma,OSCC)的形成是多種因素作用導致基因突變的結果。淋巴結局部轉移是OSCC的最主要也是對治療預后影響最大的生物學行為之一。OSCC發生發展的原因及其淋巴轉移的生物學機制尚未明確。探求OSCC發生和轉移過程中的生物學機制對明確OSCC的發病機制和尋找潛在的治療靶點有重要意義。本文從不同角度對OSCC發病及轉移機制進行綜述。
[關鍵詞]口腔鱗狀細胞癌發病機制增殖轉移
1OSCC的危險因素
1.1人乳頭瘤病毒
(humanpapillomavirus,HPV)研究表明,HPV在宮頸癌的致病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超過90%的宮頸癌患者與HPV感染有關[3]。HPV屬乳頭多瘤空泡病毒科乳頭瘤病毒,為環狀、閉合、雙鏈DNA病毒,具有高度的組織特異性,主要侵襲黏膜上皮和皮膚組織。頭頸部腫瘤中,HPV主要為HPV-16/18[4]。在OSCC中,HPV的檢出率相對較高[5],因此HPV感染越來越受到重視。口腔癌中HPV總感染率為52%,HPV-16/18的總體感染率為52%,OSCC中HPV-16感染率為42%[6]。感染HPV-16后導致OSCC發生的危險性是未感染者的5.95倍,感染HPV-18后的致癌風險為未感染者的1.65倍[6]。因此,OSCC以感染HPV-16為主,HPV-16的感染明顯增加了OSCC發生的風險。通過各種渠道預防HPV-16的感染可能對降低OSCC的發病率有一定意義。
1.2不良生活習慣
臨床研究表明,OSCC的發病與患者不良生活習慣密切相關,如吸煙、飲酒和咀嚼檳榔等。煙草煙霧中70多種成分被確認為致癌物質[7]。吸煙可增加上皮角化程度,長期慢性刺激可使口腔黏膜發生防御性增生反應。吸食煙草可使發生口腔癌的風險增加3倍,而持續飲酒可協同增加10倍以上發生風險[8]。在歐美和日本,約75%口腔癌患者有煙酒嗜好,無煙煙草是東南亞、印度、中國臺灣等地區OSCC的主要原因[9]。有研究表明,飲酒發生OSCC的相對危險度為2.19,95%可信區間(confidenceinterval,CI)為[1.98,2.43](P<0.05)[10]。另有研究認為,在各種導致OSCC的致病因素中,檳榔比煙草的致癌力更高[11]。
2OSCC的分子生物學機制
2.1原癌基因
(proto-oncogene)與抑癌基因(anti-onco-gene)原癌基因在細胞增殖和分化中有重要的調控作用,其進化高度保守。在機體出現被病毒侵襲或染色體突變時原癌基因可被激活進而導致基因產物活性增強或數量增多,出現細胞增殖。在抑癌基因失活的條件下,可導致腫瘤的形成。在OSCC的發生發展中,大部分OSCC都具有明確的癌前損害階段,經歷了由正常到癌前病變、原位癌、浸潤癌的過程。OSCC的發生與原癌基因/抑癌基因的失調密切相關。2.1.1c-erbB-2c-erbB-2基因屬于表皮生長因子家族成員,是一種細胞來源的原癌基因。某些腫瘤細胞中存在著能夠序列特異性地與c-erbB-2的啟動子結合的DNA結合蛋白,促進其轉錄、細胞增殖、細胞惡性化,c-erbB-2蛋白在腫瘤組織中存在過表達[12]。c-erbB-2參與控制腫瘤生長的機制可能為c-erbB-2作為一種生長因子受體,其表達可能增加了腫瘤細胞對生長因子的敏感性或產生1個在結構上可被激活的受體級聯[13]。口腔黏膜發生癌變后,OSCC會產生c-erbB-2基因的擴增,伴頸淋巴結轉移組c-erbB-2表達水平高于無頸淋巴結轉移者[14],c-erbB-2也可能與細胞表面過表達的p185生長因子或其他激素類因子具有超敏感應,而促使細胞迅速增殖有關,快速生長的細胞逐漸發生惡性轉變表達出更多的p185,從而進一步促進了癌細胞的轉移。可見,c-erbB-2蛋白的表達與OSCC的分化程度及侵襲能力密切相關。2.1.2Bmi-1Bmi-1是1991年荷蘭癌癥中心在鼠B細胞淋巴瘤中發現的致癌基因。高表達Bmi-1的腫瘤細胞被認為是腫瘤中存在的“癌癥干細胞”。研究表明,多種腫瘤如肺癌[15]、食管癌[16]的發生發展過程均與Bmi-1的異常高表達有關。有研究發現,Bmi-1在OSCC組織和細胞株中的表達水平均高于正常組織和口腔角化細胞,且Bmi-1蛋白表達升高發生在口腔黏膜癌變過程的早期階段[17],提示其可能與OSCC的發生有關。Bmi-1表達強度隨上皮異常增生程度增加及腫瘤分化程度降低而增加,兩者呈正相關,表明在口腔黏膜癌變過程中存在Bmi-1蛋白的逐漸積累[18]。Bmi-1表達的上調不僅在OSCC發生的早期發揮作用,而且可能與OSCC發展進程有關。2.1.3p16p16又稱多腫瘤抑制基因,是一種細胞周期中的固有基因,直接參與細胞周期的調控,負性調節細胞增殖及分裂。多種惡性腫瘤及頭頸部腫瘤中可檢測到p16基因的改變[19]。p16表達缺失將導致細胞周期調節失控,細胞增殖加快,惡性進展。在OSCC中p16基因的甲基化失活是一個頻繁事件,p16甲基化失活早在口腔黏膜白斑階段就已存在,至OSCC中持續甲基化,p16甲基化所致表達缺失可能提示口腔癌的進展,擁有p16陽性表達的口腔癌也預示著好的臨床預后[20,21]。研究表明,正常口腔黏膜、口腔扁平苔蘚及OSCC組織中p16蛋白的表達依次降低,OSCC組織中其表達程度最低,這說明p16蛋白參與了口腔扁平苔蘚的癌變及OSCC的發生、發展[22]。故p16基因的缺失、突變、甲基化和p16蛋白的低表達與口腔癌的發生、發展有關,可作口腔癌診斷的分子生物學標志之一。2.1.4p53原癌基因激活、細胞的DNA損傷、缺氧、細胞因子信號通路的過度激活都可誘導p53表達[23]。p53基因與頭頸部鱗狀細胞癌密切相關[24],其在OSCC中的異常表達也已經得到眾多研究的支持,OSCC中p53mRNA表達率為80%,DNA擴增陽性率為40%,可能是OSCC發生的早期事件[25]。作為一種重要的轉錄后調控因子,微小RNA(microRNA,miRNA)廣泛參與了腫瘤相關基因調控的生物進程。在許多腫瘤均發現miRNA結構出現改變或者表達失調,而部分miRNA家族顯示有類似癌基因或抑癌基因的功能。p53既可能是miRNA直接調控的靶基因,同時也可能對p53上下游的基因起著抑制作用,OSCC發生發展過程中,至少存在1種miRNA參與抑癌基因p53的調控[26]。
2.2腫瘤細胞增殖與轉移
腫瘤的侵襲轉移是多基因參與、多步驟完成的復雜過程。主要是腫瘤細胞脫離原發病灶,侵襲基底膜并向周圍間質浸潤性生長,穿越局部毛細血管或淋巴管壁進入管腔并形成小瘤栓,隨著血液或淋巴液運輸至靶器官,與該部位血管或淋巴管內皮細胞發生粘附,進入周圍間質,在繼發部位不斷增殖形成轉移灶。2.2.1成纖維細胞活化蛋白(fibroblastactivationprotein,FAP)腫瘤細胞間粘附減弱和腫瘤細胞遷移能力增強是腫瘤侵襲轉移的基礎。FAP是參與腫瘤上皮-間充質轉化(epithelial-mesenchymaltransition,EMT)的一個重要調控因子。FAP在OSCC中晚期癌的表達顯著高于早期癌,FAP的表達與OSCC患者的總生存時間相關。FAP沉默后細胞的侵襲、遷移運動和轉移能力顯著減弱。FAP通過第10號染色體上缺失與張力蛋白同源的磷酸酯酶基因(phos-phataseandtensinhomologdeletedonchromosometen,PTEN)/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oinositide3-ki-nase,PI3K)/蛋白激酶B(proteinkinaseB,Akt)和Ras/絲裂原細胞外激酶(mitogenextracellularkinase,MEK)/細胞外信號調節激酶(Extracellularsignalregulatedkinase,ERK)兩條信號通路促進OSCC細胞發生EMT[27]。腫瘤細胞分泌大量的轉化生長因子-β1(transforminggrowthfac-tor-β1,TGF-β1),激活成纖維細胞,使其成為具有活化表型乳腺間質成纖維細胞α-平滑肌肌動蛋白(α-smoothmuscleactin,α-SMA)和FAP的肌成纖維細胞,并促進α-SMA和FAP表達增加[28],FAP又作用于腫瘤細胞,影響其增殖、侵襲和遷移。2.2.2胸腺基質淋巴細胞生成素(thymicstromallympho-poietin,TSLP)腫瘤的發生發展與機體全身或局部存在異常的免疫調節密切相關。TSLP信號的破壞可以導致免疫系統的紊亂。TSLP在OSCC組織細胞、癌旁浸潤的淋巴細胞以及外周血中都存在高表達,浸潤淋巴細胞和轉移淋巴結中可出現叉頭狀/翅膀狀螺旋轉錄因子3(forkheadboxP3,FOXP3)+調節性T細胞和TSLP的共表達[29]。OSCC細胞中分泌的TSLP,不僅直接作用于自身的腫瘤細胞,促進腫瘤的增殖,還作用于周圍或轉移淋巴結中的浸潤淋巴細胞,促進FOXP3+Treg的分化或募集,從而抑制機體對于腫瘤細胞的免疫反應,促進OSCC的發生和轉移。2.2.3Wnt/β-catenin通路β-連環蛋白(β-catenin)是一種由原癌基因編碼的多功能蛋白,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與E-鈣黏蛋白(E-cadherin,E-cad)形成復合體,維持上皮極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作為Wnt通路的關鍵蛋白參與調節細胞的增殖、分化和凋亡。它在腫瘤的發生、發展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經典的Wnt/β-catenin通路在成熟細胞中常處于關閉狀態,當β-catenin在細胞核或細胞質中出現高表達時,Wnt/β-catenin通路被激活。OSCC中β-catenin出現異常高表達,激活Wnt/β-catenin通路,參與OSCC的形成,同時與其發生EMT密切相關[30]。上皮標志物E-cad是一種重要黏附分子,是經典的上皮細胞標志物。E-cad的減少或丟失是上皮來源的腫瘤細胞侵襲的前提條件,是發生EMT的重要標志[30]。研究表明E-cad在正常口腔上皮細胞中存在較高的mRNA和蛋白表達,而在OSCC細胞HN4中表達下調,在OSCC轉移淋巴結細胞HN12中表達極低[31]。這在一定程度上提示E-cad與OSCC上皮細胞惡性度、轉移潛能有關。2.2.4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ascularendothelialgrowthfac-tor,VEGF)VEGF可提高血管通透性、促進內皮細胞增殖并加速血管的生成。其中VEGF-C和VEGF-D通過誘導腫瘤淋巴管的生成,促進腫瘤細胞的淋巴轉移。研究表明,OSCC癌巢及瘤內上皮均可見VEGF表達,且表達水平與腫瘤病理分期呈正相關,同時癌組織中微血管密度較正常組織及癌前病變顯著升高[32],VEGF-A與OSCC轉移相關[33]。因此,VEGF可能在口腔黏膜癌變的過程中參與調節病變局部組織血管的生成,這可能與腫瘤的生長和侵襲有密切關系。
3總結與展望
口腔癌是威脅人類健康的一種常見惡性腫瘤,近些年口腔癌的發病率有明顯的增加趨勢。OSCC是最常見一種口腔癌,其惡性程度高,預后差,5年存活率低。本文從不同角度對OSCC發病及轉移機制進行了綜述,以期對判斷OSCC的惡性程度以及尋找潛在治療靶點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為臨床提高OSCC患者的治愈率和生存率做出一定貢獻。
作者:王倩 侯大為 單位:甘肅省人民醫院口腔頜面外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