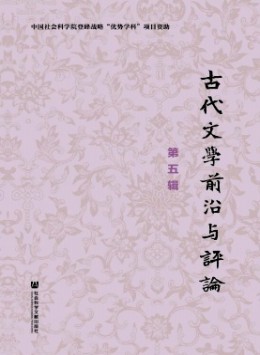古代文學教學中的功力與性情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古代文學教學中的功力與性情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一、緣起
2018年9月20日,筆者參加了貴州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接收外專業轉入本科生面試。當一位本科生被問到是什么樣的機緣促使她決定轉入漢語言文學專業時,她說有一天經過一間教室時,聽到教室里傳出吟誦古典詩詞的聲音,這個聲音感動了她,讓她陶醉,從那一刻起,她堅定了轉專業的決心。作為一名長期從事文學教育的教師,這位學生的講述在給予筆者觸動的同時,也引發了筆者的沉思。筆者在思考文學教育的課堂應該是什么樣的,或者說我們的文學教育與文學的距離是變遠了還是變近了。文學教育有其特殊性,是知識的傳授,又不能是單調的知識灌輸;是方法的訓練,又不能流于奇技淫巧;是文化的傳承,又不是照搬照抄;是情感的綺靡,又不是煽情濫情。中國古代文學教學的難度較之一般文學教育而言更大,畢竟古代文學與我們隔著久遠的時間,古人的語言形態、思維方式、情感模式等都與我們有著巨大的差異,將古代文學這條奔流了幾千年的河流導入當下的文學課堂,既需要深厚的文學功力,也需要充沛的文學性情。正如章學誠《文史通義•博約中》所言: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夫學有天性焉,讀書服古之中,有入識最初而終身不可變易者是也。學又有至情焉,讀書服古之中,有欣慨會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從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1]對于一位學者型教師而言,功力和性情缺一不可。沒有性情的功力,就好像封閉的書柜,散發出的是霉變的酸腐之氣;缺少功力的性情,宛如醉酒的兒童,流露出的是非理性的癲狂。鑒于中國文學史教學中功力和性情的比例失調和輕重失衡,筆者撰寫此文,縷述前賢中國文學史教學的成功案例,以之為當下之借鏡。
二、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
1988年,北京大學中文系著名學者袁行霈教授應邀出席北大青年教師培訓班開班典禮,發表了題為“北大學者應有的風度和氣象”的講話。在講話中,袁行霈回憶了老輩學者教學的深厚功力和敬業精神,他說:我上過王力先生的漢語史這門課,我注意到他的講稿是每個字都寫得端端正正的。我還上過李賦寧先生的西方文學史這門課。我注意到他是怎樣在圖書館埋頭備課。……我們當了多年老師的人都怕誤人子弟,心常懷警惕。即使小心謹慎,還是難免出錯,一旦知道了自己的錯誤就趕快改正,這不要緊。[2]王力和李賦寧是袁行霈心目中的典范教師,當然也是典范學者。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為一位優秀的教師首先必須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以孔子為例,學不厭始終被擺在教不倦之前,學不厭是教不倦的基礎,沒有學不厭的學術積淀,教不倦又從何談起?優秀學者的養成,深厚學術功力的培植,雖然離不開先天的資質,但后天孜孜不倦的為學工夫則更為重要。誠如朱熹在《總論為學之方》中所言:大抵為學,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既是遲鈍之資,卻做聰明底樣工夫,如何得![3]當代學術史上,不乏資質平常但成就巨大的學者,比如史學大家嚴耕望。嚴耕望本人自認為天資不高,其師錢穆也承認這一點,但錢穆勉勵嚴耕望說后天的氣魄和精神意志可以彌補先天資質之不足。嚴耕望在《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一文中回憶說:我覺得大本大源的通貫之學,實非常人所可做到;我總覺得天資有限,求一隅的成就,已感不易;若再奢望走第一流路線,恐怕畫虎不成反類狗!先生曰:這只關自己的氣魄及精神意志,與天資無大關系。大抵在學術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資,因為聰明人總無毅力與傻氣。你的天資雖不高,但也不低,正可求長進![4]學術研究有賴于后天學術功力的恒常聚集,教學則是把研究的獨到之見傳授與學生,同樣需要深厚的學術功力。有此功力方能傳授正確的知識,反之,則極有可能出現錯謬,甚至誤人子弟。南京大學莫礪鋒教授就曾經講述過一位美國教師誤人子弟的例子:1986年,在哈佛大學訪學的莫礪鋒旁聽了一位美國副教授開設的研究生討論課,主講的內容就是唐詩,而莫礪鋒是研究唐宋文學的專家,對內容深感興趣,就參加了討論。這位教授當時講的是韋莊《金陵圖》,全詩是:“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無情最是臺城柳,依舊煙籠十里堤。”莫礪鋒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他反復講烏鴉怎么樣。我當時就很納悶:這首詩跟烏鴉有什么關系?后來我搞清楚了,原來是“江雨霏霏江草齊,六朝如夢鳥空啼”中的鳥字被他解釋為“烏鴉”。……我說你講得很好,但是據我所知,這首詩里面沒有“烏”字,是“鳥”字。他不相信,馬上回頭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唐詩三百首》,翻給我看。果然是“六朝如夢烏空啼”,是一個臺灣出版社出版的,臺灣是繁體字,“鳥”字少了一筆就變成了“烏”字。……我當時就跟他說,這不可能是“烏”字。這是首七言絕句,又是晚唐韋莊寫的。韋莊是詞人,他更是講究平仄的。如果是“烏空啼”,則是114三個平聲字連用,變成了三平調,這是律詩的大忌,晚唐人是不可能寫出三平調的。所以平聲字“烏”一定是仄聲字“鳥”。[5]這位在課堂上講授唐詩的美國副教授連最起碼的絕句格律都不清楚,都是糊里糊涂的,又怎么能以己之昏昏使人昭昭呢?海外中國文學的研究與教學不乏此類事例,即使是聲名卓著的漢學家有時也難免在基礎性問題上犯錯,比如日本漢學泰斗級人物吉川幸次郎,在解讀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圣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時說:所謂的“至理”,是指把皇帝賞賜的東西丟掉這件事,這樣的解釋似乎是合理的。“至理”的“理”,應寫作“治”,為避高宗李治的諱而寫作“理”。[6]這段解讀就有兩個明顯的錯誤:第一,“至理”指的不是“皇帝把賞賜的東西丟掉這件事”,也就是說不是“君豈棄此物”,而是“實欲邦國活”。中國學者對此沒有疑問,如蕭滌非《杜甫詩選注》:“‘至理’,即上句‘實欲邦國活。’”[7]傅庚生《杜詩散繹》對這四句詩的白話今譯為:“天子把這些金帛之屬一筐一籠地賞賜給群臣,本意是指望他們能夠出力把國家治理得鼎盛起來,使得一般老百姓能過些好光景;倘或文武群臣忽視這些愛民活國的大道理,天子憑什么把這些金帛白白地浪費掉呢?”[8]第二,“至理”的“理”字不存在避諱,不是“為避高宗李治的諱而寫作理”。據陳垣《史諱舉例》第七十六《唐諱例》所考:“高宗,治改為持,為理,或為化。稚改為幼。”[9]120唐代確實存在吉川幸次郎所言的那種避諱處理方式,但卻忽視了陳垣關鍵性的一句考證成果,陳垣說:“唐時諱法,制令甚寬。”[9]119所謂“制令甚寬”就意味著可以避諱,也可以不避諱。有些情況下必須避諱,有些情況則不需要避諱:一般來說,在涉及公文、科舉等政府行文時要避諱,在詩歌等個人性寫作時,沒有嚴格的避諱要求。因此,杜甫在此沒有必要把“至治”改寫為“至理”。另外,如果杜甫果真要避高宗李治的名諱,那么杜詩中就不可能出現“治”字,凡是“治”字都必須避諱。但事實卻并非如此,杜詩中“治”字經常出現,如《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吾聞聰明主,治國用輕刑。”《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典郡終微眇,治中實棄捐。”《戲作俳諧體遣悶》“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如果吉川幸次郎熟讀杜詩就不難發現這些“治”的存在,之所以沒有發現,就是因為對杜詩的熟悉程度還不夠,這一點,他本人也不否認。吉川幸次郎在《中國文學與杜甫》中說:杜甫的詩總共約有一千四百首,依照中國方式,注釋這些詩,先要全部背下來,達到任何一首都能答出來的地步,方可落筆。實際上,在過去的中國,恐怕就有這樣的人,但我能背出來的大概是一百首。[10]作為一位以杜詩研究為主要學術致力點的學者,僅能背誦一百首杜詩,只占杜詩總數的十四分之一,從功力方面來說,還是欠缺得太多。在中國,確實有能把一千四百余首杜詩全部背誦下來的學者,比如康有為。在當代學者中,馬茂元先生的記誦工夫更是令人驚嘆,他能背誦一萬多首唐詩。不僅是便于記誦的詩詞,甚至枯燥泛味的古典辭書字典,也有學者背誦如流,如國學大師黃侃。吉川幸次郎在《我的留學記》中記載了黃侃帶給他的感動,他說:首先讓我佩服的是:對《經典釋文》中《谷梁傳》的部分,我一直有幾處疑問,在北京問過好幾位先生,或沒有清楚、滿意的回答,或干脆不理我。但我與黃侃先生見面時,一提出這問題,他立即回答說:“這是夾帶進了宋人的校語。”而且,并沒有看原書就作出了這樣的判斷。這讓我覺得很了不起。隨著話題漸漸展開和深入,我更感覺這人才是真正認真讀書的人。他可以把《廣韻》全部背下來。[11]正是因為深厚的學術功力,再加上至情至性的學者情懷,讓黃侃成為北京大學“當年國文系最受尊敬的名教授”[12]之一。王國維深厚的學術功力也令梁啟超欽佩,梁啟超在《與清華研究院同學談話記》中說:教授方面,以王靜安先生最為難得,其專精之學,在今日幾稱絕學。而其所謙稱為未嘗研究者,亦高我十倍。我于學問未嘗有一精深研究,蓋門類過多,時間又少故也。王先生則不然。先生方面亦不少,但時間則我為多。加以腦筋靈敏,精神忠實,方法精明,而一方面自己又極謙虛,此誠國內有數之學者。[13]梁啟超自言“于學問未嘗有一精深研究”,乃是虛懷若谷的謙虛之言,不必引以為據。但他稱揚王國維為“國內有數之學者”,確實是不刊之論。王國維之博雅精深,可以敦煌寫本《秦婦吟》為例,王國維《唐寫本韋莊<秦婦吟>跋》曰:此詩前后殘闕,無篇題及撰人姓名,亦英倫博物館所藏,狩野博士所錄。案《北夢瑣言》:“蜀相韋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闕,著《秦婦吟》一篇,云‘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此詩中有此二語,則為韋莊《秦婦吟》審矣。[14]這個文本首尾殘缺不全,又沒有著錄篇名和作者姓氏,當時學者包括日本學者都不知為何物,王國維看到其中“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兩句詩,就斷定其為韋莊亡佚已久的詩歌名篇《秦婦吟》。其根據是,宋代孫光憲的筆記《北夢瑣言》著錄了《秦婦吟》這兩句詩。當時還沒有電子檢索的文獻查找技術,王國維全靠對《北夢瑣言》的熟稔,而且記誦下了這兩句詩,才能作出如上論斷,學術功力確實令人敬佩。之后陳寅恪撰寫了《<秦婦吟>校箋》,周一良撰寫了《秦婦吟本事》等,學術界對這篇詩作的研究也逐步深入,但開山導源之功自然要歸之于王國維。
三、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
深厚的學術功力是學者型教師的立身之本,但僅有功力而無性情,同樣還是有缺憾的,尤其是面對中國古代文學這種特殊的學科門類,性情乏味的學者無法領略中國古代文學的抒情之美。畢竟,中國古代文學有源遠流長的抒情傳統,抒情性是中國古代文學最大的特色。陳世驤《中國的抒情傳統》一文對此有深刻的剖析歸納,他說:中國文學和西方文學傳統(我以史詩和戲劇表示它)并列,中國的抒情傳統馬上顯露出來。這一點,不管就文學創作或批評理論,我們都可以找到證明。人們驚異偉大的荷馬史詩和希臘悲喜劇,驚異它們造成希臘文學的首度全面怒放。……中國文學的榮耀不在史詩;它的榮耀在別處,在抒情的傳統里。抒情傳統始于《詩經》。[15]抒情性的特質不僅體現在文學領域,在中國文學批評領域也是如此,正如張伯偉教授在《中國文學批評的抒情性傳統》一文中所揭示的那樣。周汝昌甚至認為,中華文化就是“情文化”。周汝昌《<紅樓夢>與“情文化”》曰:一位僑居日本的女學士寫信告知我說,在一個日語班的課堂上,老師提到日本文化是X文化,韓國文化是X文化,都用一個詞語來代表那個文化的特色;然后問中國的學者,中國是什么文化?沒有人能答上來。她信札中很以為憾事。我“聽”了這段話,很感興趣,于是自己也試尋起答案來。想了很多,最后的“決定”是,如要我答,我將回信道:中華文化是“情文化”。[16]周汝昌所言中華文化之“情”,不是局限在男女愛情上,還包括親情、友情、忠君愛國之情、朋友篤厚之情,以及對植物、動物一體之仁的惻隱悲憫之情。最遲從孟子開始,儒家就已經意識到人既是道德主體,也是情感主體。受儒家文化影響深遠的中國古代文學,既要擔負懲惡揚善的道德感化,也要宣導創作者的喜怒悲歡之情。道德感化一定程度上還容易滋生說教之呆板,但文學作品中充溢的情感脈沖,更容易引發后世讀者的心靈共振。遺憾的是,受西方模式的影響,五四以來建構的古代文學研究模式,在追求所謂客觀性、公正性、規范化的同時,也出現了重視理性分析而忽視感性認知,重視邏輯思維而忽視情感體驗的弊端。張伯偉教授《中國文學批評的抒情性傳統》對此有過警示性的分析:二十世紀初,隨著西方學術的大量涌進,導致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的轉型,文學研究也走上另外的途徑。研究小說,則注重情節、結構、人物形象、典型環境等;研究戲劇,則注重沖突、人物、布景、對白;甚至研究抒情詩,也會更加注重主題、題材、韻律、句式。從總體上看,越來越趨向于崇尚思辨,強調分析,輕視感性,忽略整體。……可以說,文學研究若拋棄了感情的因素,則必然是隔膜的,因而也必然是不圓滿的。[17]如果說作為學術研究的文學探討尚且可以適度容忍情感體驗的缺席的話,那么文學教育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把情感拋擲在課堂之外。因為文學作品不是塵封已久的僵死文本,而是承載著古人歌哭悲喜的船舶,順著歷史的河流緩緩駛來。如果把文學課堂比作宏大的舞臺,那么學生是觀眾,教師是演員,文學作品是舞臺的劇本。比如,把《牡丹亭》搬上舞臺,無論你費多少唇舌分析愛情的偉大,都抵不上杜麗娘“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一句唱腔。因為后者的感情可以感動觀眾,而前者因過于理性而消解了作品的魅力,這或許就是章學誠所言“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的原因吧。獨坐書齋的學問尚且不能如此,更何況面對學生的文學教育?縱觀民國以來的文學教育,稱得上是大師級的學者,他帶給學生的震撼絕對不僅僅是功力深厚的學術著作,必然還有性情洋溢的課堂風姿。比如,程千帆心目中的胡小石,他在《兩點論———古代文學研究方法漫談》中回憶說:胡小石先生晚年在南大教《唐人七絕詩論》,他為什么講得那么好,就是用自己的心靈去感觸唐人的心,心與心相通,是一種精神上的交流,而不是《通典》多少卷,《資治通鑒》多少卷這樣冷冰冰的材料所可能記錄的感受。我到現在還記得當時胡先生的那份心情、態度,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學到了以前學不到的東西。我希望頭一點告訴你們的,就是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并重,對古代文學的作品理解要用心靈的火花去撞擊古人,而不是純粹地運用邏輯思維。[18]在南京大學,胡小石留給程千帆最為深刻的唐詩教學記憶就是對柳宗元詩歌的吟誦,時隔多年之后,程千帆可能早已遺忘了當年胡小石講授的具體內容,但那一連串聲音卻一直縈繞心間。曾經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張中行,也有類似的記憶,他在《負暄瑣話》中回憶了黃節授課的情景:黃先生的課,我聽過兩年,先是講顧亭林詩,后是講《詩經》。他雖然比較年高,卻總是站得筆直地講。講顧亭林詩是剛剛“九一八”之后,他常常是講完字面意思之后,用一些話闡明顧亭林的感憤和用心,也就是亡國之痛和憂民之心。清楚記得的是講《海上》四首七律的第二首,其中第二聯“名王白馬江東去,故國降幡海上來”,他一面念一面慨嘆,仿佛要陪著顧亭林也痛哭流涕。我們自然都領會,他口中是說明朝,心中是想現在,所以都為他的悲憤而深深感動。[19]黃節沒有過多地闡述顧炎武詩歌的藝術技巧,單單是那“一面念一面慨嘆”的真情流露,就足以感染學生,激發起學生的愛國激情。這需要的不僅是學術功力,更是學者性情。相反,那些被公認為博學的學者,如果在文學教育中不注重性情的浸潤,就會嚴重影響課堂教學效果,乃至引起學生的反感。周作人就是其中一例,他在《知堂回想錄》中所說:平心而論,我在北大的確可以算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在各方面看來都是如此,所開的功課都是勉強算數的,在某系中只可算得是幫閑罷了。[20]對于周作人的文學課堂情景,親炙者也有回憶,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說:周作人先生教的是歐洲文學史,他所編的講義既枯燥無味,聽講課來又不善言辭。正如拜倫所描寫的泊桑(Porson)教授:“他講起來希臘文,活像個斯巴達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說且噎。”因為我們并不重視此學科,所以不打算趕他。[21]周作人課堂的乏味雖然與其不善言辭的語言表達障礙有關,但筆者認為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周作人性情的寡淡或許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性情等同于口才,口才好未必性情佳,口若懸河也有可能導致濫情和浮夸,而吉人辭寡的前輩學者往往也是文學課堂難得的別致風景,比如南京大學的管雄教授。其弟子張伯偉教授在《繞溪師的“藏”與“默”》中回憶當年問業情景曰:先師不僅惜墨如金,而且也惜“言”如金,他的話總是不多的。讀碩士階段,每周一次師徒對坐兩小時。每次去時,繞溪師就已經坐在那里。我進去后,師母總是再端一杯茶給我,然后把門掩上。我雖然比較喜歡講話,但在老師面前總應該少講,因而常常是默默地相對無言。先師如老僧入定,沉默無語乃本色當行。[22]沉默不語或者寡言少語也未必不是好的教學方法,反而是孔子“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教學之道的傳承,這種啟發式教學方法可以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讓學生從被動接受知識轉變為主動尋求答案,張伯偉教授就是管雄教授緘默教學之道的獲益者,他說:一次,我問何以從明代開始鐘嶸《詩品》大受歡迎?先師答曰:“與評點有關。”我想了解得更詳細一些,乃以目詢之,但繞溪師已眼簾微垂,作“予欲無言”狀了。后來,自己讀書漸廣,對于《詩品》與評點的關系有所了悟,更加欽佩先師的提示堪稱要言不煩。也就是在這樣的鍛煉下,逐步養成了我凡事多自己鉆研的習慣。[22]管雄教授對《詩品》在明代的接受與傳播極端熟稔,故能一語中的,這是學術功力的呈現,“與評點有關”五字則是緘默寡言的性情使然,功力與性情交映生輝,成就了現代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
四、結語
中國古代文學的教育面臨很多困境,從目前學術界的情況來看,存在著重視科研而輕視教學的問題,很多學者片面地認為只有藏之名山的論文和專著才能傳之后世,教學只是一場華麗而易散的演出,文字的壽命比金石還長久,聲音則會隨著下課的鈴聲而中止。殊不知,課堂上教師的一個聲音,一個手勢,一個轉身都有可能留給學生美好的記憶。學生對文學的興趣,對文學知識的掌握,對文學研究方法的研習,需要研讀教師的科研論著,也需要課堂教育的體知。中國文學史的教學又有其特殊性,深厚的學術功力是基礎,但基礎不是唯一,性情同樣是這門課程的必備修為,前輩大師級學者的成功案例已經證明了這個規律的合理性。
作者:趙永剛 單位:貴州大學 文學與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