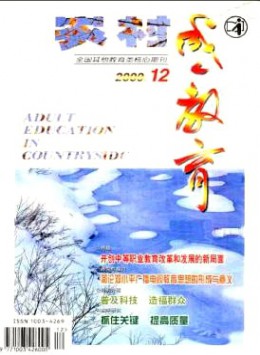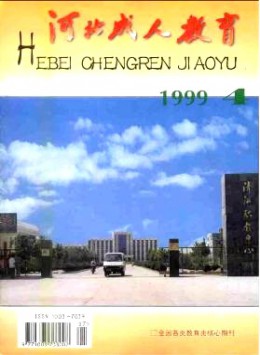成人教育人文精神培養探析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文章?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成人教育人文精神培養探析范文,希望能給你帶來靈感和參考,敬請閱讀。

一、后現代狀態下知識的轉化
從現代到后現代,轉化的標志就是對元敘事話語的普遍質疑。“現代”以啟蒙敘事一理性精神是人類最高級精神,其價值訴求可以通過知識的傳播達到共識——為中心,建構起一整套確認知識合法性的敘事體制,即一般所說的“元敘事”或“宏大敘事”。利奧塔給“后現代”的定義言簡意賅:后現代是對元敘事的懷疑。⑧利奧塔的定義源于對后現代狀態下知識的考察。在現代時期,特別是在啟蒙話語中,知識作為啟蒙英雄追尋的目標或是作為其手中的利器,具有其不言自明的合理性與確定性。這種合理性與確定性在后現代狀態下則被普遍質疑。在利奧塔看來,這源于科技的變化:在后現代時期,知識的研究和傳播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任何無法轉譯為現代科技話語所能接納的信息量,都必然失去其存在的根基。“我們可以預料,一切構成知識的東西,如果不能這樣轉譯都會遭到遺棄,新的研究方向將服從潛在成果變為機器語言所需的可譯性條件。”另外,在后現代狀態中,知識被外在化了,“從前那種知識的獲取與精神,甚至與個人本身的形成(‘教育’)密不可分的原則已經過時,而且將更加過時”。知識所聯系的供應者與使用者之間的交換關系,決定了知識的商品屬性,知識不再以自身為目的,而是以交換為目的被生產。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在后現代時期,知識作為精神的載體或作為精神傳播途徑的性質已經改變,傳統人文主義觀念認為知識承載著理性意識,擁有知識就意味著人將具有獨立性和自主性,而科學與理性的增長必然帶來總體的社會進步,現代價值也必然在社會進步中得到彰顯與普及。
但20世紀的現實卻將現想擊得粉碎。同一個上帝的子民間相互仇視,以致不惜訴諸戰爭。兩次世界大戰,原子彈的爆炸,機械化有組織的屠殺,這一切使得現代特別是啟蒙運動所認同與宣揚的理性“烏托邦”與知識“神話”在頃刻間土崩瓦解。在這樣的背景下,后現論家將知識與權利并置,從而將傳統理性(即人文主義)知識錨定于權利結構,進而加以批判與解構。米歇爾•福柯無疑是這方面的代表,“從其著述生涯伊始,福柯就與人文學科和人文主義的意識形態構形形成了公開競爭。即是說,福柯的規劃始終與各種個體的人文學科進行著斗爭,包括哲學、歷史、語言理論和文學批評,并受到人文精神的陰謀壓制。”④福柯運用其創造性的譜系學理論考察現代人文主義,在他看來,知識作為一種權利的現實被人文主義者通過宜揚“理性”的無功利性和客觀性所遮掩。而這一點在“文化”和“教育”領域體現得尤為明顯。福柯以“五月風暴”為例指出,課堂發揮一種雙重壓抑的功能:一方面,它將一些人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它又對課堂內的人強加規范和標準。這并非學習環境中存在著等級結構那樣簡單,福柯的含義更加深遠:“擁有”知識的人傳授知識,獲得知識的人與獲得知識的人造模式達成一致,二者都是政治行為,即通過對一個“學科”的掌握來繁殖一個新資本主義啟蒙社會權威的知識和研究形式,因此福柯說:“知識在其表現上最初意味著一種政治統一”。如此,知識與個體的完善之間的因果關系被打破了,傳統人文主義或新人文主義頂禮膜拜的那個主體——人——就成為了可懷疑的存在。
后現代另一位理論家是德里達。長久以來,對德里達的誤解使人們常常將他歸人各種宣揚“歷史終結”論的陣營。事實上,一個宣揚“延異”的哲學家是與“終結”無緣的。德里達的解構思想,從解構語音中心主義出發,運用“延異”思想,對一切本源意義進行了質疑。“中心”作為一種統攝意義的存在的合理性,在他那里被消解了:“處于中心的所指,無論它是始源或先驗的,絕對不會在一個差異系統之外呈現。先驗所指的缺席無限地伸向意謂的場域和游戲。”在這種無限延異的游戲中,傳統上作為文本意義賦予者的作者隨著這一“延異”的過程而瓦解,就勢在必然了。但這種瓦解與死亡或終結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作者權威遭遇“延異”的結果是其失去中心位置,與永恒性絕緣,但卻作為不斷變化的瞬間存在著。所有書寫都變成了“延異”的“痕跡”,所有意義都只能在瞬間存在。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一切確定性、永恒性與單一性的存在,啟蒙運動、人文主義所推崇的知識的統一陛、普遍性與確定性也自然被“延異”掉了。如是觀之,我們可以作如下總結:在后現代評價體系中,知識的精神屬性被解構或懸置了,實用性、短暫性、多元性、片斷性、非理性成為知識的特征,知識的后現代轉向必然影響整個教育體制,而成人教育因其教育對象與教育目的的特殊性,其經受的沖擊尤為明顯。
二、忽視內在精神導向的“終身學習”
現代意義的成人教育發軔于西方的工業革命。源于對生產效率的追求,資本社會逐漸達成一種共識:勞動者以技能為中心的勞動素質需不斷提升,這有賴于對成人(勞動者)的繼續教育,以適應迅速提高的生產水平。從這一角度來看,成人教育從一開始就與資本追求利潤的功利性訴求相關。成人教育一定程度也可命名為“勞動技能培訓”。至后現代時期,雖然人們對知識的認知已發生轉變,但成人教育的最終目標并不能脫離社會功利或集團利益的樊籬,反倒是后現代知識的轉向使原本可能通過知識的傳授實現人文精神的培養也失去了可能性。一般認為,成人教育理論一次質的飛躍是從“終身教育”向“終身學習”的轉變。這一轉變自有其內部與外部的動因。①當然我們無法否認這一轉變所具有的變革性意義——畢竟從“終身教育”強調的體制性教育轉向了“終身學習”強調個體性自主學習。但是,“終身學習”同“終身教育”一樣,并沒有從根本上質疑整個成人教育(也包括非成人教育)的潛在目的性,即其實用主義的功利性。相反,“終身學習”的個體強化被一種具有欺騙性的個體目標向度單一化,進而遮蔽了其個體對內在精神完滿的本能要求。
之所以說其是“欺騙性”的,是因為這種個體的目標向度仍沒有脫離體制性的桎梏,在沒有質疑知識的屬性的情況下,經后現代強化了的“實用知識”占據了個體所獲取知識的主要部分,以至全部。成人教育的對象在接受知識(無論是出于主動還是出于被動)時,不可避免的實用性訴求決定了哪怕是“終身學習”的觀念已深入人心時,仍會只是一種單一向度的學習。對個體的人而言,終身學習的維度應該是多元的,生命的長度、廣度、深度與力度的獲得不應被排除在學習之外。這種學習效果的取得必須以強調個人的主體性為前提,通過多元化的途徑,達到個體生命完滿的目的。這與后現代的旨趣相去甚遠,從根本上說,后現代是質疑人之主體性的,內在性也在這種質疑中最終被貫穿,其對成人教育的影響是深刻的,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個體自我發展的精英傾向與后現代成人教育的反精英傾向之間的不可調和性。現代教育傳授或接收知識以培養精英為目的,而個人的自我發展或以穿越原有生活瓶頸為潛在動力,或以內在性的豐盈、在精神上完滿為最終目的。個人自我發展的這種精英化傾向在后現代并沒有本質改變。但在后現代轉向發生后,對文化多元性的訴求,對知識世俗化的渴望,使得精英本身已成為一個飽受質疑的概念,甚至被等同于“強權”或“中心”而拋棄。如果說個體的發展最終就是要以自我價值的實現或內在完滿的實現為目的,那么,我們應該為這樣的以此為目標的“精英”培養高舉贊成之手。發展的一致性讓位于個體自我導向發展的差異性并不是后現代的勝利,而是向往自由之力量發展的必然結果。
從這一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后現代思想帶給成人教育的問題,遠比它解決的問題更多。其二,傳統人文主義精神受到普遍質疑,人的屬靈性在面對后現代多元主義時,不可避免地被壓抑,世俗的多向度性被強化,并被貫以“自由”之名。因強調精神訴求的一致性而忽視個體的差異性是一種強權,誰又能否認,因強調多元化而否定人類在精神上的共通性需要也同樣是一種暴力呢?法國學者保羅•朗格讓認為,教育的現實責任可作如下定義:第一,確定能夠幫助一個人在其一生中不斷學習和得到訓練的結構和方法;第二,通過多種自我教育的形式,向每一個個人提供在最高、最真實程度上完成自我發展的目標和工具。如果我們承認這樣的現實——在現代,特別是被稱作“后現代”的當下,教育的目標已由過去以獲取知識的寶庫為目的,轉向為了個人的發展,作為多種成功經驗的結果而達到日益充分的自我實現,①那么,朗格讓的定義就不失其合理性。如此,問題就再明顯不過:后現代成人教育單一的實用傾向、對精神的解構與懸置策略,這一切必然最終引導成人教育走向歧途。沒有一種教育在失去精神引導時,可以實現個體自我完滿(即所謂“日益充分的自我實現”),可以使整個社會或某一地區受益。誰也無法否認,精神向度從來就是個體、群體以至整個社會發展的內在性需要。
三、質變學習的精神向度與兼容性
用保羅•朗格讓給教育的現實責任的定義去關照成人教育的發展歷史,我們就會發現,雖然成人教育與生俱來的實踐性決定其理論、模型、原則與解釋的多樣性,但其最基本的結構仍然是學習的成人與教育機構及整個社會環境的關系。這一關系從受教育者的角度來看,是一個學習過程;從另一角度來看,是一個教育過程,因此,雪倫•B•梅里安認為,“成人教育學”與“自我導向學習”仍然是成人學習理論的支柱。②如何才能將二者結合到一起,就是成人教育當下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成人學習是在原有知識的基礎上的發展過程,而質變學習則強調如何在這一過程中促進學習者的本質性變化。從這一意義上可以說,質變學習是學習者認知方式與認知策略發展根本變革的結果。無論是強調質變的解放性觀點,指出社會的不公平性并支持解放的弗萊雷,還是強調成人學習中的社會背景,將其研究集中在學習過程的認知方面的麥基羅,他們的質變學習理論都持一種發展的觀點,“把意義的形成作為成為人的基礎”,強調“指導者在質變學習過程中的重要性”;而其精神整合觀則強調“質變學習的超理性因素”,③即質變學習已經超越了以自我為基礎的、依賴語詞交流的理性方法,而轉向了超理性的、以心靈為基礎的學習。綜合考察質變學習的理論訴求和現實狀態,我們可以發現質變學習具有兩方面特質:
首先,質變學習強調學習過程中的學習者內在精神的本質變化,這種變化最突出的表現是學習者對待自己和世界的態度和方式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這種改變可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也可能是突發性的。前一種狀態要求施教者要在教育過程中綜合運用多種方法引導啟發學習者,以促進這種改變的發生。而后一狀態則需要施教者在狀態發生改變時,引導其良性發展。其次,質變學習在強調學習者內在精神需求的同時,兼顧了外在功用的需要。質變學習既不強調個人學習,也避免談論集體學習,而是把目光集中于個體與學習環境的關系上。在這樣一個場域中,個體的良性本質變化,其力量必然作用于社會風潮的發展,最終促成社區甚至是地區精神與物質發展的和諧共進。由是觀之,如何將質變學習的理論在成人教育實踐中具體化、策略化就成為我們必然考慮的核心問題。考慮到質變學習的精神向度以及后現代狀態中人文精神的失語的現實,人文學科的傳統優勢理應得到強調,并使其在質變學習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質變學習理論家泰勒非常強調承載著價值判斷的課程內容對培養質變學習的重要作用。這些課程的論題在教師的引導之下,會引發批判性的反思。這其中的矛盾也是顯而易見的:教師的引導作用如果發揮不當,其個人的觀點可能會威脅學生的世界觀,“啟蒙”與“壓抑”有時只相差一步。
另外,應建立以受教育者為中心的成人教育體制。成人教育的對象往往是帶著問題或任務來的,這樣的特殊性與傳統成人教育的課程設置的通約性之間矛盾重重。如何在教學過程中輔之以通約性課程之外的教學手段,就成為成人教育改革的當務之急。以課題或項目為中心的成人教育也許是未來成人教育發展與改變的方向或主流。這種體制的建立因為困難重重,往往難以實施,但這決不是我們逃避這一問題的理由。質變學習不是一種獨立的行動,它需要一種信任關系作為基礎,只有在滿足成人教育對象現實需求的前提下,成人教育的精神向度才能有一個穩健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