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隨想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清明隨想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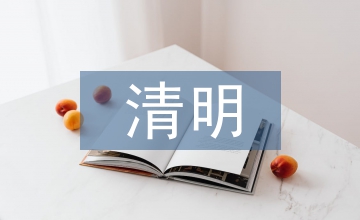
第1篇:清明隨想范文
清明節,讓人緬懷先輩,令人留戀,令人悲嘆,令人振奮,這里面蘊含了許多的先輩們的事跡,當他們入土為安之時,自己的故事就告終了,剩下的,就只有讓人懷念了!
敬愛的革命烈士們,您用青春和生命為民族解放而英勇抗爭的光輝業績令我們敬仰;您留給后人崇高的民族精神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它將永遠鼓舞我們進取、向上;您播下的思想種子,已經在我們心中生根、發芽,成為帶領我們走向美好明天的旗幟。
敬愛的革命烈士們,經過你們不懈努力和艱苦卓越的奮斗,當年被帝國主義列強辱罵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已經站起來了,今天,我們接過從您手中傳過來的接力棒,決心要更新觀念,擴大視野,掌握一技之長,全面完善自我,為中華民族的興旺出一份小小的力量。
敬愛的革命烈士們,此時此刻,我們只想用一朵小花寄托我們的哀思,我們只想用一個花環表明我們的心意,我們只想用一座石碑表達我們的敬仰……但是,我們更明白,最好的方式只有一個,那就是:繼承您的意志,弘揚您的精神,讓我們的明天更加輝煌,讓我們的祖國更加富強。
第2篇:清明隨想范文
1、 關于文學園地:是冬天爐中的一團炭火,可以讓人取暖;是世俗世界的一縷清風,可以給人撫慰。
2、 關于文學獎項:是一種人文激賞,是一種人生喝彩;為在文學之途寂寞趕路的一群人點亮了一盞燈。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隨想之二:激賞一個散文家――朱小軍――有魏晉筆記小說簡約之風,得明清散文小品輕淡之范。
1、 他是一個文學學養深厚的人。他讀書可以讀到淚眼婆娑,他作文可以讓人咀嚼再三。他以五十多年人生閱讀之積累,爾后始于表達,所謂厚積薄發是也,所謂居高聲自遠是也。其看似散漫、輕淡、簡約而為的文字,甫一問世便成為了一個事件,成為了一個現象。現在,在東風文學圈內,大家見面常常問一句:“你讀朱小軍了嗎?”
2、 朱小軍所寫之人之事,是一個時代一個群體的人文記憶,是一個時代一個企業的精神涵養。它是東風人的口述歷史,是東風公司的人文《史記》,全是紀實,因此,它是歷史的;同時,它又是文學的,所有文字,寫人記事,你盡可以當作志人之類的筆記小說讀,平和而不平靜,簡約而不簡單,在文字之外自有大波浪,大天地――他直抵人心,觸動人,溫暖人,撫慰人。
3、 我以為,朱小軍文字的路數是純粹中國的,有魏晉筆記小說簡約之風,得明清散文小品輕淡之范。是根植于中國文化沃土的,是在中國文人學士圈里一直流傳的文風,文脈。
4、 納博科夫為世人留下了回憶錄《說吧,記憶》,希望朱小軍的系列文章只是熱身,是開始 ,希望他接下來繼續說吧,寫吧。
隨想之三:推薦一個詩人――蔡崢嶸――詩味與詩感共生,優美與優雅同在。
1、 蔡崢嶸的詩合符我個人閱讀詩歌的興趣取向,即所謂詩歌“三昧”:有味道,可誦讀,深究一番讀得懂。故推薦之。
2、 蔡崢嶸的詩是干凈的詩,是明麗的詩,像山泉水,像純凈水,像礦泉水,幾乎就沒有什么雜質在。
3、 蔡崢嶸的詩是有詩味的詩,是輕靈的詩,是輕盈的詩,也是起伏飄逸的詩。好比酒出自糧食谷物,它是水鄉清酒,是房縣黃酒,是紹興花雕,綿香而又純粹,清冽而不濃烈――我們撫摸打在日子上的補丁/抹去生活的鹽分/繼續說愛/說童年的故鄉/說著說著春風就擠進門縫。這樣的詩,品嘗一口,滿嘴生津。
4、 蔡崢嶸的詩是有詩感的詩,是生動的詩,是有情趣的詩――當一只蝴蝶俯沖藍/當藍分泌藍/我想走向比藍更藍的地方。――我以為,詩的感覺,或者說生動,是詩歌、詩人高下之別的主要指標,是衡量詩歌、詩人是否優秀的KPI,其他都可以是從屬和其次。
5、 有詩感的詩,有詩味的詩,是可以透著一份優美與優雅的,就仿佛京劇里的梅蘭芳,小說里的沈從文,歌曲里的王洛賓。
6、 李白是熱鬧的,浪漫的,豐富的,王維是平和的,安靜的,明亮的,他們并不見得十分深刻,但他們絕對優秀與偉大。蔡崢嶸,愿照此在詩歌之路走下去,且一路走好,寫出更多優美與優雅的詩!
隨想之四:致敬一個小說家――傅祥友――在文學園地,他是一個堅持者和堅守者,他是一個可以把生命托付給文學的人,他是東風人文領域里一道最美麗風景線。
1、 在文學之途,雖踽踽前行,但總是在行,而且沉浸其中,從不回頭。這就是傅祥友。其人也義氣,其行也正氣,其文也生氣,其悟也真氣。
2、 普天之下,皆可冷嘲;率土之濱,無不熱諷。時而還間雜一點調侃,這是祥友能耐所在,更是他風格使然。是的,祥友積十年之訓練與修煉,還真有了那么一點契科夫的味道。其語言也是這樣的,不僅增添了一點韻味,而且生出了一些張力,最終具有了內容性與文化性。是明顯的成績與進步,是需要保持與發揚的。
3、 感受于文學之美妙,體味于創作之神圣,祥友敢與青燈相伴,可以生命相許。當今之世,如斯之人,能有幾何?如此精神,這般狀態,當贏得全體起立鼓掌致敬。
4、如果在明處省一點力,比如說能夠從語言中出得來;如果在暗處多用點勁,比如講對故事多一分經營,那么,在現有格局之上還將增長幾分境界,祥友便會化蛹為蝶,一飛沖天了。
隨想之五:賞析一個作者群――漸顯個性,漸成風格,漸成風氣。
1、 周中:他是今天東風詩歌繞不過去的一個人。盡管其見諸于報刊雜志的作品并不十分多,但據說其寫作量是驚人的。縱觀周中詩歌,其文也華麗,其采也艷麗,其氣也壯麗,其勢也雄麗。先說其文、其采,周中的詩是美文中的三島由紀夫,華美而不鋪陳;是美食中的東坡肘子,肥美而不膩歪;是美人中的楊貴妃,豐腴而不肥胖。再說其氣、其勢,周中的詩是眉飛色舞的,是高聲闊論的,是恣睢的,是排山倒海的,聞其聲,是高音中的多明戈;品其味,是美酒中的二鍋頭;辨其色,是百花中的紅牡丹;觀其勢,是河流中的瀾滄江。此等文采,這般氣勢,其底蘊與涵養只能是中國文化,是中國詩詞。
2、王征珂:有一種記憶是童年,有一種意象是童趣,有一種表達是童謠。王征珂是幸福的,在紛繁熙攘的塵世,其精神總是生活在童話里,并且始終做著一個清醇歌者的夢,二十多年了都不醒過來。他又是敏感、可愛的,像鄰家那個缺了門牙捂嘴賣萌的小妹崽,其喜怒哀樂全是童謠的,也全是詩歌的。但是,其聲音又不全是稚嫩,發出的又不全是嗲聲,其人其文也絕不一覽無余,絕不清澈見底。因此,王征珂的詩往往是初春遠處的湖面,是初夏早晨的原野,總有一種薄霧在繚繞,也總有一種水汽在升騰,所呈現出的是一種萌態美,氤氳美,朦朧美,迷離美。
3、趙明的《江上人家》――靈性初現,像早春枝頭,讓人眼前一亮;李俊玲的《活著》――人性燭照,像爐膛炭火,讓人心頭一熱;姚天賜的《夢長安》――心性勃發,像天馬行空,讓人超然物外;尹琦的《走在城市心中》――天性點化,像酷暑冰啤,讓人全身通泰;陳宏的《大年夜》――率性而為,像冰糖葫蘆,讓人酸酸甜甜。
第3篇:清明隨想范文
鐘一聲,鳴一聲,漸次催人急更行,兩三馳道封。
樓一層,人一層,病眼迷蒙遠望空,幾人歡樂容。
采桑子 遐思
香蒲小扇虛空轉,望月憑欄。望月憑欄,不見微星卻籠煙。
更深人靜花池處,一片蛙歡。一片蛙歡,漏斷風輕卷月殘。
采桑子 雨過天晴
微光斜入杯中影,雨過天晴。雨過天晴,漫卷簾升思量停。
風光無限雖常好,易冷人情。易冷人情,不若時時氣正平。
采桑子 閑心
憑窗遐想云端碧,薄暮天陰。薄暮天陰,高樓望盡總浮沉。
移收視線從前對,數落閑心。數落閑心,春闈臨近應更勤。
憶王孫 佳人
云煙聚散總飄縈。起自窗臺卷綠旌。萬里長空日正晴。鳥輕鳴。催憶佳人歡笑聲。
憶王孫 遠思
漸行漸遠漸無書。終日憑窗望遠途。對鏡新妝鳳鳥服。起鷓鴣,記得當時梅子熟。
憶王孫 離別
天南地北各紛飛。落水浮萍魚緊隨。渡口船只號角催。鳥徘徊。代我送君迎客回。
南柯一夢
水澈魚歡戲,林青鳥暢鳴。
碎步竹里處,閑作玉簫聲。
歲歲花相伴,安心度此生。
南柯空好夢,醒臥醉翁亭。
小巷
風吹小巷碎花香,
殘葉微光影映墻。
搖曳身姿天氣爽,
迎風正步路憑長。
秋日
秋冬更替漸天寒,
乍暖昏昏夢日邊。
醒坐窗前欹望遠,
遐思一路向云端。
隨想記
傷心舊事莫重提,
會有一朝盡忘時。
惟恐暮春逢杜宇,
催人腸斷惹相思。
夏
春盡終辭杜宇去,
農家細雨晚來及。
橋邊紅藥枝枝盛,
池小芙蓉朵朵開。
無題
花落終究夢一場,
覺來不過是尋常。
沉思何必時時淚,
傷痛從來百日長。
夜來思 念郎
因思昨日斂峨眉,
夜來起身撫琴墜。
賺得紅燭空垂淚,
愁未解,幾時睡?
夜來思 別君
輕舟已過極目送,
孤身佇立江樓中。
隔岸猶聽《梅花弄》,
心中愁,幾時空?
漁歌子
又是一日夕陽殘,
無語對天盡呢喃。
仍記得,君未還,
一別不知幾經年。
未眠
長夜蛙鳴吵,
煙云掩月昏。
心懷人事去,
倚柱候清晨。
輕夢
合翠樹,
白鷺自徘徊。
策馬驚飛去,
塵埃與后來。
遠望
狹路相逢去,
千帆入海流。
匆匆一過客,
知己往難求。
天地謠
天地恒長遠,
遙相對立邊。
無需牽一線,
海角自關聯。
思遠人
恍若寒冬逝,
深梅落幾枝。
殘花如有意,
最是恨別離。
且徐行
何須難自犯?
世事本多艱。
徑取千樽酒,
無妨縱醉歡。
十月
雁去初十月,
江南正暖陽。
思君方寸亂,
非曉桂花香。
偶書
遙望青石路,
風吹幾許黃。
回腸思入定,
輕捻桂花香。
重逢
林青沾雨露,
天色漸清明。
路盡歡歌止,
相思了卻情。
安世
莫若孤單去,
無非度暮遲。
世間生百態,
冷暖自須知。
清晨
風輕云亦淡,
倚樹鳥還眠。
觸手新陽暖,
得來一早安。
月夜
開軒窗對月,
執筆畫雙眉。
一夜紅裝待,
郎君自遠來
伴
寒冬臨又盡,
春逝夏秋來。
一日同攜手,
明朝共發白。
絕情
十載功名就,
攜來一女還。
三千黑發斷,
從此盡塵緣
華胥
不戀功名利,
田園共赴歸。
開軒同賞桂,
與爾畫雙眉。
路燈
凄清風雨夜,
寂寞似長燈。
幾處紅光影,
空街一夜明。
雨后
東邊虹又現,
雨后放初晴。
花鳥重歡樂,
松竹洗更青。
中元
夜深人不寐,
獨自望蕭墻。
清漏滴滴響,
橫笛更斷腸。
杜康辛且辣,
微風暖還涼。
多少圓鉤日,
偏覺此夜長
拾憶
暮春花盡殆,
秋來雁皆南。
爾與相似暖,
非覺臘月寒。
紅豆
多少蓬萊事,
重提自淚流。
世傳醫扁鵲,
能否治相思。
李后主
千古金陵破,
從今違命侯。
天生才子手,
詩詞書畫周。
遍灑他鄉淚,
因思故土流。
七夕吟怨曲,
太祖賜千秋。
憶難忘
亭臺上,
獨倚小軒窗。
思過往,
回憶摧斷腸。
欲把思念折成船,
遙寄遠方,
清風擋,
難前向。
立斜陽,
望天穹蒼茫。
盡惆悵,
心情難舒暢。
稍候天黑待天狼,
指引方向,
未料想,
雨水滂。
無歸人
一腔紅豆,
身與心皆瘦。
以為萬事休,
問能否,
久作停留?
相思已久,
百花皆看透,
至化為烏有,
空等候,
又添一段新愁。
枝頭景
花滿枝椏,
蝶戀花。
未料想,
忽有傾盆雨下,
傷兩家。
花成殘,
雨打蝶散天涯。
遙憶初夏,
蝶倚花斜,
今又有此畫,
第4篇:清明隨想范文
一、打造品牌文化,水墨漫畫唱響全國。今年圍繞湖北省文聯和孝感市文聯提出的“一縣一品”文藝品牌創建,我們主打水墨漫畫牌,讓安陸水墨漫畫唱響全國。圍繞品牌創建,我們做了如下工作。
1、成功策劃全國水墨漫畫理論研討會在我市召開。這次會議有四大收獲,出版了《安陸市水墨漫畫集》;舉辦了安陸市及全國知名漫畫家水墨漫畫展;搜集整理出版了《水墨漫畫理論文集》;被人民日報《諷刺與幽默》授予漫畫創作基地。
2、由水墨漫畫院和文化館聯合舉辦了國畫研習班,提升老畫者的功力,擴大新畫者的隊伍,營造更濃厚的創作氛圍,先后有80余人參加研習班,并推出了一大批精品力作。
3、積極投身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和文化館、水墨漫畫院一道完成了《科學發展觀漫畫知識讀本》一書的編輯出版,反響較好。
4、積極組織作者參展參賽,王同志參加了武漢城市圈名畫家邀請展,展出水墨小品12幅;12人作品入圍湖北省第11屆美展;三人作品入圍中國美術家協會舉辦的第十一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8月,安陸23件水墨漫畫作品參加年第三屆亞太青年動漫大賽,引起國內外漫畫界關注;10月,安陸19件水墨漫畫作品入選武漢漫畫佳作展,并有6件作品獲佳作獎;11月,王同志在廣州市成功舉辦了個人畫展。
二、發揮領軍優勢,文學藝術創作豐收。今年,市文聯干部、市作協主席曹同志加入中國作協,實現了我市文學藝術國家級會員零的突破,是一大亮點。同志等文學、詩歌、漫畫、書法、攝影等各方面的領軍人物,不斷推出精品佳作,文學藝術創作喜獲豐收。曹同志在《清明》雜志發表中篇小說《逝去的足跡》,在《福建文學》發表短篇小說《去南方》等多篇,年末,其中短篇小說集《雨水》獲湖北省屈原文學獎優秀獎提名;黃同志的創作也進入高峰期,發表報告文學多篇;曹同志繼去年在《長江文藝》發表長詩《我的祖國》后,今年又在《人民日報》大地副刊發表詩作;朱同志的小城系列第三部長篇脫稿;易同志的《歲月如水》繼獲湖北文壇網絡文學征文特等獎后,8月又獲中華之魂優秀文學作品征文一等獎;聶武等19人作品在《書法報》刊登;池同志的攝影作品《隨想》入選《中國攝影在線》第一屆國際攝影展覽;王同志的攝影在《人民攝影報》發表,池同志、段同志、劉同志、易同志四人作品入展“三江杯”全國攝影大賽;9月,王同志的長詩《我是長江的女兒》獲“富思特杯”慶祝建國60周年征文詩歌類一等獎;12月,李同志的散文獲“延安精神贊,頌歌獻給黨”詩歌散文征文三等獎;網絡也有許多高品味的作品問世;市廣電局辦公室主任高同志的博客《永恒苦旅》點擊突破60萬大關,成為草根名博;退休老干部王同志的博客點擊也突破10萬,倍受博友歡迎;安陸博客圈已有博友120余人。
三、爭取領導支持,大小活動接連不斷。年,在各級領導的關心和支持下我們開展了以下活動:3月,全國水墨漫畫理論研討會在安陸成功召開;同月,《書法報》走進安陸作品研討會在安陸成功舉行;市作家協會和水墨漫畫院聯合在安陸文化館組織水墨漫畫家與作家圓桌對話;4月,市作協成功舉辦·孛畈之春文學采風筆會;5月,組織部分作家赴安陸一中進行文學講座;5月,成功接待湖北省詩家安同志風行;5月,舉辦攝影培訓班,先后有50余人參加培訓;5月,舉辦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成果攝影展,同月,編輯出版《太白風》特刊;9月,會同市攝影家協會、市煙草局舉辦慶祝建國60周年“煙草杯”攝影大賽;9月,市中老年合唱隊參加孝感市紅歌比賽,以總分第二獲“牡丹金獎”;9月,市作協舉辦“一葉秋黃”網絡詩歌座談會;同月聯合攝影家協會和煙草專賣局舉辦安陸市紀念建國六十周年“煙草杯”攝影大賽11月,市文聯主席易同志參加孝感市“一縣一品”經驗交流會并作大會發言;11月,在錢沖舉辦首屆中國銀杏節銀杏風光攝影展,展出作品15余0件,展出10余天,好評如潮,市文聯被評為銀杏節先進單位,文聯主席易同志被評為先進個人;同時,加班加點,編輯出版了《太白風》銀杏節特刊;11月,組團參加了孝感市第四屆文代會,我市13名代表參加了會議;此外,還有其他多項小型活動。諸多活動的開展,使文聯的社會地位得以不斷提升,社會影響不斷擴大。
第5篇:清明隨想范文
摘要20世紀80年代后期,是詩歌這一文體在社會轉型期中逐漸被邊緣化的一個時期,這個時期的許多外在社會因素對西部詩人昌耀的影響是巨大的,昌耀的創作在這種精神的焦慮中發生著變化,與其在80年代初期剛剛復出時的創作有著很大的不同。本文試從80年代后期這個視角出發,通過對其作品的解讀,來分析外在影響及在這些影響因素之下詩人自身的創作。
關鍵詞:昌耀 詩性 思索
中圖分類號:I207.2 文獻標識碼:A
20世紀90年代后期,昌耀詩歌的價值開始得到詩界的重視。但通過對發生在那個時代的一些詩歌事件的分析,我們可以感覺到,80年代中后期的這段時間對于中國詩界來說是紛亂而復雜的。雖然詩歌在這一時期表現出在文學觀念、方法的更新、探索,以及在人的生活、精神處境的關注上,并常常走在文學其他樣式的前面,但是這并未能改變詩歌的“邊緣”地位。同時,詩歌界內部不同層面的分裂與沖突,以及詩歌活動方式上的“圈子化”、“江湖化”,雖說并不是只有負面的意義,但制造的泡沫也確實使真誠、專注的詩人蒙受損害。對于一個堅守詩歌理想的詩人來說,這一時期的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發展狀況對昌耀的影響是巨大的。
一 艱難之思
閱讀昌耀80年代中后期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他在當時外因影響下的一種惶惑中的焦慮心態。這種影響帶給他的焦慮與他罹難歲月中的苦難有著諸多的不同。與此同時,昌耀自身也面臨著諸多的困境,困境之一是來自創作上的。昌耀在復出的幾年時間里,在詩歌創作中構建了屬于自己的詩歌理想,他詩歌中生命意識的覺醒及對“時間”歷史性的把握,都使他的詩歌在西部詩歌中樹起一座詩歌的豐碑。如,1979年所作的長達500多行的長詩《大山的囚徒》;1980年創作的《慈航》、《山旅》;1982年創作的《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個孩子之歌》。1982年至1985年,他創作了西部的大高原造型,這是一個結構了他詩歌主體形態的、恢宏而輝煌的系列:《曠原之野》、《青藏高原的形體》(共六首,包括《河床》、《圣跡》、《她站在劇院臨街的前庭》、《陽光下的路》、《古本尖喬――魯沙爾鎮的民間節日》、《尋找黃河正源卡日曲:銅色河》)以及《巨靈》、《牛王》和《秦陵兵馬俑館古原野》等。青藏高原的形體系列在展示昌耀的睿智和語言功力的同時,也隱約透露出他創作中存在的動力不足等諸多問題。而這些問題的存在使昌耀在詩歌創作中,又表現出一種相當強烈的焦慮意識,如《艱難之思》、《聽候召喚:趕路》、《招魂之鼓》、《燔祭》等詩篇,都是詩人表達這一情緒的代表詩作;困境之二,作為一個詩人,昌耀出版的詩集并不多,文學“商品化”趨勢的日益強勁,使得昌耀在這一時期預計要出版的《情感歷程》和《淘的流年》均未出版,《命運之書》的出版也是幾經周折。
由此可見,“艱難之思”應該說是昌耀在80年代中后期心態的真實寫照。除了對現實處境的困惑之外,在昌耀的作品中還可以感受到一種深刻的矛盾和沖突,這些深刻的矛盾和沖突在他這一時期創作的詩歌,如《內心激情:光與影子的剪輯》、《意緒》、《云境?心境》、《內陸高迥》等詩中都有明顯的表露。雖然在詩的領域里昌耀是不甘落伍的,并且永遠保持著一顆永不言敗、絕不放棄的心態。但是現實的無情依然將昌耀及當時的西部詩拉入一個低谷。如果單以作品數量來評價這一時期昌耀的創作,他無疑還是成功的,從80年代中后期昌耀創作的詩文總集來看,1985年和1986年可說是詩人創作的高峰期,特別是1986年的詩歌數量已達到詩人創作數量的頂峰。筆者所說的低谷是就昌耀的創作心態而言。昌耀的創作心態之所以形成低谷是與當時的西部詩潮所面臨的困境,以及昌耀對困境引發的全方位的關照性的思索有關。如果說1986年的“詩人大展”中“第三代詩人”的蜂擁而出,幾乎擾亂了詩界正常的秩序是造成西部詩潮趨于沉默的一個重要的外因,那么,西部詩自身存在的問題引發的內因則是使西部詩潮趨于黯淡和沉默的主要原因。西部詩潮所面臨的困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詩歌本體所展開的層面已經不是西部詩既有的方式所能企及的了;其次是為了適應于各種文化本體觀,西部詩歌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藝術靜態模式,使它在原有的路子上舉步維艱。這種潛在的內因成為西部詩發展創作上難以逾越的障礙。作為一個智慧型的詩人,昌耀對于自己的創作和西部詩創作的這種體會是十分深刻的。在長詩《燔祭》中,他慨嘆:“世界無須掩飾,我們相互一眼看透彼此,/偶像成排倒下;而以空位的悲哀/投矛荷戟的壯士,/壯士壯士壯士/踩牢自己銹跡斑斑的影子”,“我偷覷沉默的獅面人如同孩子偷覷父親/我偷覷獅面人威猛的沉默……我感覺他如火照人的瞳孔透出疲憊/我深知如此潛在的悒郁是我難得洞悉的悒郁/……獅面人的痛楚是我有直接嫡承的痛楚。”“獅面人”這位歷史“老人”親歷了時代的滄桑而望眼現在,頓覺“瞳孔疲憊”,心情悒郁,這是詩人的憂患、痛楚、沉思,更是民族的痛楚。詩人心靈的抒寫也是整個民族心靈的律動。所以說:“一切無可回避,但是人類已不堪其巨額的血肉支付,一切唯賴攜手同舟共濟。”《燔祭》這首組詩,是昌耀對于中國當代歷史憂患中的深刻反省,“‘燔祭’就是‘心祭’,這里有對純真的獻身精神的悼惋,有對‘異我’的解剖,也有對物欲橫流、道德淪喪的悲困,但更多的則是透過‘獅面人’對民族生存的悒郁、痛楚和幽思。”同樣,為了擺脫這種困境,昌耀在他的創作中,依然在努力延續著自己建構的詩歌與生命的理想,并且以1986年為界,昌耀詩歌開始自覺地追求“藝術的抽象和抽象的藝術”,其詩歌的主題也從關注外在功利的善惡角力轉至對生存宿命的感悟,以及對于宿命抗爭的崇高的人格的塑造。
二 詩性探索
面對著當時的社會現狀和自身感應的困境,昌耀毅然敲響了《招魂之鼓》,“無有表情的表情是至真至誠至慟的表情。/無聲的號泣是刺心至深至毒至美的號泣。”“自從人之成為人以來――飲血、飲淚、飲光、飲土、飲鐵、飲風、飲露、飲男女、飲愛、飲善惡之果……”卻“總也解不開千古的困擾”,而“生的強音無可奈何。”雖然在《懸棺與隨想》中,昌耀認為“人生有不可溝通的煩憂。/人生有不可匡救的盲區。/人生有不可解析的困頓。/人生有不可平撫的創痛。”但在現實的處境中,昌耀卻依然執著于“趕路”,在《諧謔曲:雪景下的變形》這首詩中,我們可以看見“落伍的一只魚穿過雪城/追隨另一群披著掩耳長發的魚”,這可以說是詩人最為形象的自畫像。在面對自己創作中的困境和外界隨著時代的發展,價值體系引發的心態失衡給人們帶來的極大震蕩時,昌耀的“行為”就是“永無休止、永無退卻、永無妥協”地“趕路”。同時“永無妥協”的形象,也成為詩人精神內境的一個縮影。《聽候召喚:趕路》中的“太陽說:來,朝前走。”成為這一時代昌耀“趕路”行動的核心部分。而《回憶》、《金色發動機》和《兩個雪山人》則分別體現和刻畫了“趕路”的背景、心境和生存者。《金色發動機》中“金色發動機懷著焦躁不安的沖動”,“在天底的岑寂中抗拒:/既不能在岑寂中泯滅,/也不能自岑寂中超脫”的詩句描述了詩人內心的巨大搏斗,在《回憶》中,詩人把這種沖動和搏斗的心靈投放在更為寬闊的歷史情景上,表述了這種精神的一貫和永存:那些西域道上的使者,那些坎坎伐檀者,那些舍身求法的人、埋頭苦干的人,那些中國的脊梁、不化的顱骨,乃至大漠深處縱馳的一匹白馬,正如詩人駱一禾在他所撰寫的文章中稱:
“我們之所以稱昌耀為大詩人,在于他的詩歌寫出了個人內心和寬闊背景上的諸般生命所并存的主導精神,他所突出的是這種至今仍然驅策著中國人的緊迫感,這是一個時代的因素,在今天它越來越具有事實感,越益地強化了,要么便是聽候召喚,是趕路,要么便是迫降和永遠吞沒,并且詩人的心靈自身也首先是具有和抵達了這個程度的覺識。”
當然文學的實現,也就是詩人精神生活的實現。在《內陸高迥》中,“一個蓬頭的旅行者背負行囊穿行在高迥內陸”,他艱難地跋涉,“步行在上帝的沙盤”,與命運作著最無畏的挑戰,以殉道者般的虔誠追尋崇高的人格境界――“河源”。為了它,旅行者義無反顧地獨行在曠古荒原上,“誰與我同享暮色的金黃然后一起退入月亮寶石?”高潔、痛苦,然而執著,因為他堅信“社會與人性總要走向進步與完美,任一混沌或混濁都將復歸清明”。這種義無反顧的執著,心之“內陸漂起”,也正是昌耀人格理想的體現,是“一個徹悟了世事的人,能從更廣闊的歷史背景和遼遠的生活進程中反觀個人生死榮辱,從而尋找和表現人類的存在,從平凡中去尋找光輝,找到能夠使他的詩成為永恒的主題。”
昌耀認為“每一位詩人在其生活的年代,都應是一部獨一無二的對于特定歷史時空做能動式的‘音樂機器’,其藝術境界可成為同代人的精神需求與生命的驅動力。”因此,他把自己置身于歷史與時代生活的壓力下來從事創作。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以及在由此而引發的人們價值觀念的深刻變化和商品經濟的巨大沖擊中,這種建立在80年代想象基礎上的理想主義情結,在真正付諸實踐之后,人們卻發現了理想與現實的偏差,并由此而引發了種種負面效應,從而使80年代初形成的樂觀的情緒受到了很大的削弱,而這種理想與現實的偏差,同樣也給了昌耀以極大的刺激。在一個精神追求貧弱的年代,昌耀感到了“時代的陣痛”,再加上過去的種種經歷以更頑強、更自覺地被重新記起,因此,使昌耀的精神世界在不甘落伍的“趕路”的同時,也積淀了一種厚重的苦難意識和憂患意識。此外,昌耀對詩壇的現狀以及新詩自身發展也表現出了強烈的憂患意識,“是由于那些‘反傳統’或‘實驗詩歌’,表面上看似乎更具現代意識,實則是在逃避詩歌的道義責任和寫作難度,使詩歌遠離了讀者,還是由于經濟社會造成了‘痛苦的精神缺席’”。昌耀在他的詩歌《小滿夜夕》中這樣寫到:
“唯獨我的苦悶才是致命的/每當堅守自己都得經受一切歇斯底里的神經戰,……于今又多了一層嚴峻。/灰色的心態造就灰色的人生,/黃金播下嫉恨使龍種變性。”
昌耀在詩中所表達的不僅是苦悶、憂患,而且幾乎是絕望到“情緒死亡”的境地。但他又是積極的,做著不懈的自我救贖,“如此訣別的日子花朵也讓人心寒,/苦悶的心皈依田園慨因靈魂渴望自由”,正如魯迅所言:“因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斗者更勇猛、更悲壯。”這是生命力度的表現,承擔“嚴峻了的現實”帶予的絕望反而使“靈魂變得剛健”,享受了“鷹翔時的”:
“我感覺自己是一只蹲伏在花盆的鷹……須知既已永遠而去誰又曾回來復述其樂?/只有這一次我聽到晨報登載一條驚人消息,/說是昨夜人們看到詩人只身翱翔在南疆天宇。”
詩人以自己創造性的詩歌實踐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將詩在如此的歷史境遇中化為“高尚的情思,寄托的容器,是凈化靈魂的水,是維系心態平衡的安全閥,是人類本能的嚎哭,是美的召喚、品嘗與獻與。”這種與民族共憂患的使命意識,又促成了詩人在更高的層次上改造與完善了自己的文化心理結構,探求一種立足本土,面向世界的博襟與文化心理,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6期。
[2] 昌耀:《昌耀詩文總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 李震:《中國當代西部詩潮論》,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李萬慶:《內陸高迥:論昌耀詩歌的悲劇精神》,《當代作家評論》,1991年第1期。
[5] 駱一禾、張:《太陽說:來,朝前走――評〈一首長詩和三首短詩〉》,《西藏文學》,1988年第5期。
[6] 楊柳:《至真、至善、至美:西部詩人昌耀的審美追求》,《浙江學刊》,2000年第6期。
相關期刊推薦
精選范文推薦
- 1清明詩詞大全
- 2清明節的由來故事
- 3清明古詩一首
- 4清明古詩杜牧
- 5清明節紀念烈士手抄報
- 6清明節手抄報簡單小學生
- 7清明節緬懷先烈詩歌
- 8清明節的來歷故事
- 9清明記事
- 10清明古詩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