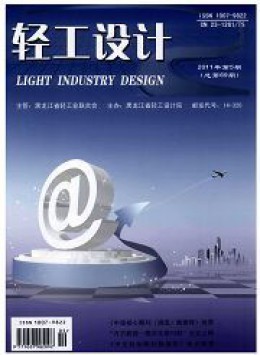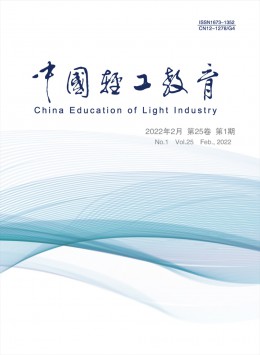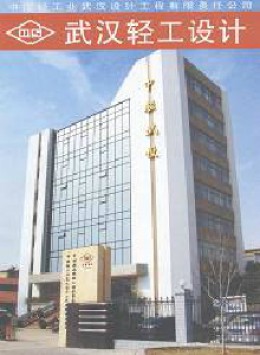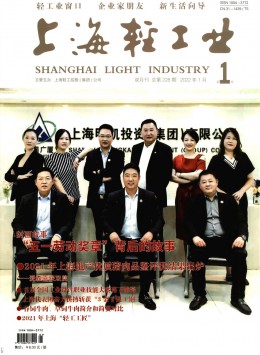輕工業的特點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輕工業的特點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輕工業的特點范文
輕工業的發展,對增加就業量、增強進出口貿易、服務“三農”、促進經濟的提升以及社會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債務危機爆發后,因為全球的需求萎縮,我國輕工業的發展受到了非常大的打擊。我國輕工業企業越多、發展越壯大,受到波及越大,受到的挑戰越嚴峻,例如,我國沿海制造產業有著“世界工廠”之稱,但是由于生產成本越來越高、勞動力不足、利潤率下降、貨款困難以及海外訂單大幅減少等等原因,使其發展受到嚴重影響。目前我國輕工業面臨的最主要挑戰有:比較優勢不明顯,融資難,技術、結構、質量的矛盾依然存在等等。
1 輕工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1 輕工業自主創新能力差,研發環節比較薄弱
就目前來講,我國輕工業中發展最多的是中小型企業,并且其中大多數為民營企業。此種中小型民營企業存在的特點就是門檻相對較低,布局分散、凌亂,這是導致創新能力差、研發環節比較薄弱的主要原因,其根本就沒有自主創新、自主研發的能力與土壤。由于缺乏創新能力、研發能力,使得企業重復建設的現象非常突出,經濟效益得不到提升,大多數生產主要以加工型或者原料型為主,生產出的產品結構水平底,技術附加值不高等。
1.2 輕工業增長方式存在結構性矛盾
目前,我國輕工業結構存在著不合理的現象。企業分布相對分散,而大型企業在核心技術方面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在國家化資源配置能力方面也嚴重缺乏。企業生產同質化嚴重,且技術含量相對較低,以初加工產品居多,各個品種之間的結構布局也嚴重不合理。從輕工業結構的視角來看,市場競爭力不強。
1.3 輕工業循環經濟、節能減排不到位
我國有相當一部分輕工業企業發展存在著污染嚴重、工業消耗巨大、生產產品質量差的問題,其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沒用采取循環經濟、綜合利用的方式來進行生產,節能減排不到位,依然采取粗放的增長方式。
2 解決輕工業發展中存在問題的對策
2.1 改變經營戰略,開放實施“特色輕功”
提高技術含量是目前我國輕工業發展最需要做的事情。開放實施“特色輕功”、實施“請進來、走出去”的經營戰略對提高我國輕工業市場競爭力至關重要。之前我國輕工業市場競爭力低,所獲取的經濟效益低,其原因在于生產技術含量不過關、生產處理過多是原料加工等等。增強產品層次的更新與多樣化是當今輕工業發展的迫切需求。首先,“請進來”。所謂“請進來”就是要接受發達國家經濟輻射,利用發達國家的相關資源來促進我國輕工業發展、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市場競爭力的提高。但是,資源的“請進來”不能原封不動地利用,應該根據本國實際情況來進行,結合資源特色,這樣才能發揮作用。其次,“走出去”。將我國特色輕工產業分工鏈條中的一部分放在區外更有優勢、更合適的地區,這對產業整體優化具有重大意義。
2.2 建立輕工業園區
建立輕工業園區,對解決我國輕工業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我國輕工業企業數量非常龐大,布局不合理、分布較為廣泛,而建立主題輕工業園區可以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將存在一定關聯的輕工業、生產同類產品的輕工業集中起來,建立主題輕工業園區,這對形成規模,真正做強、做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以此同時,要以點帶面地發展,通過產業的關聯帶動,延長產業鏈條,推動相關產業的進步與發展,促使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2.3 加強創新體系的建設
要想提高我國輕工業的發展,解決輕工業中存在的問題。加強創新體系的建設至關重要。那么首先要推動、扶持企業建立技術中心,尤其是重點骨干企業。企業中一定要建立技術開發機構,大力實施學研聯合開發工程,加快利用速度,并且轉化成科技成果。輕工業若想走向高科技發展以及推動“特色輕工業”的發展就必須建立技術創新體系。因為它是發展的保障與支撐,是發展的根本動力。政府要大力扶持企業技術創新,給予政策、資金幫助與投入,還要建立技術創新機制,以企業投入為主體,金融、財政以及外資互動的新體制。最后,要不斷完善風險投資體系和機制,政府大力支持風險投資公司,而風險投資公司本身也必須要不斷提高管理、經營的能力,使其在輕工業的發展中發揮應有作用。
3 總結
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輕工業得到了迅速發展,解決了我國就業難、進出口貿易不景氣的問題,也很好地為“三農”提供了服務與幫助,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隨著一些主客觀原因的出現,如債務危機等。我國輕工業發展還是存在著一些問題,如融資難技術,結構、質量的矛盾依然存在。因此必須要解決好我國輕工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本文從輕工業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出發,對解決輕工業發展中存在問題的對策進行探討分析。希望對輕工業的發展起到借鑒的作用。
第2篇:輕工業的特點范文
——基于京津冀協同發展的觀點
郭洪生1張辰利2
(1.河北農業大學機電工程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1;2.河北農業大學經濟貿易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1)
【摘要】河北省環京津環渤海區位優勢得不到充分發揮的關鍵在于產業的重化工化,而重化工產業布局需要遠離中心城市;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需要沿京津周圍布局輕工業產業帶作為過渡,以實現河北重化工業和京津城市產業的密切銜接;但是目前河北輕工業發展滯后,需要通過促進加工貿易以外部力量來提升輕工業的產業水平和發展速度。
關鍵詞 環京津環渤海優勢;重化工化;輕工業;加工貿易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Layout in Hebei Province
——Based 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 Beijing and Tianjin
GUO Hong-sheng1ZHANG Chen-li2
(1.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School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Baoding Hebei 071001,China;2.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School of ecnomics and Trade, Baoding Hebei 071001,China)
【Abstract】Hebei Province is around Beijing,Tianjin and Bohai Rim region, but the region advantage is not fulfilled for its heavy Chemical Industry. To achie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ith Beijing and Tianjin, Along the Beijing-Tianjin area, a light industrial zone as a transitional arrangement should be arranged to coordinate Beijing and Tianjin urban economy closely. But now light industry in Hebei is less developed, the development level and pace of light industry can be enhanced through prompting processing trade, and now there is coming a historic opportunity for Hebei Province to develop its processing trade.
【Key words】Around Beijing,Tianjin and Bohai sea advantage;Heavy Chemical Industry;Light Industry;Processing Trade
河北省內環京津,外環渤海,在國際范圍內,所有類似地區基本都是最為富庶發達,而河北省經濟發展水平卻相當滯后,甚至出現“環首都貧困帶”的極端反常現象。
1產業結構重化工化是京津冀區域經濟發展分化的主要原因
1.1重化工產業布局需要遠離大城市,使河北經濟重心布局要遠離京津
河北是一個以鋼鐵、煤炭、石化、裝備制造為主的資源型、重化工大省。“十一五”期間,鋼鐵、裝備制造和石油化工三大支柱產業完成增加值占全省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由2005年的57.4%提高到2010年64%,2012年繼續增加到65%,重化工特點呈逐年加強的趨勢。
重化工產業初級資源投入比重大、吞吐量大、耗費能量高、污染嚴重,類似企業選址要遠離居民密集的城市。比如鋼鐵行業,需要大量運入礦石原料,煤炭燃料,運出成品鋼材和工業廢料,生產過程中還要產生大量污染,都會給城市帶來很大的交通和環境壓力。
1.2重化工產業市場化程度低,使河北經濟發展缺乏活力
重化工行業隨著行業集中度的提高,壟斷程度提高,行業進入門檻提高,行業的社會化水平降低,民間的各種資源難以融入其生產循環過程,京津市場資源也難以得到有效整合,比鄰兩大市場,卻使得整個社會缺乏商業活力。
經濟活力是一個地區吸引投資和人才的軟環境,河北比鄰京津,擁有吸引京津投資和人才的天然區位優勢,但現實卻不但沒能吸引京津的資源,反而出現了“倒虹吸”現象,即河北省的資本和人才資源向京津外流,不但使河北經濟不能承接京津產業的轉移和輻射,卻導致河北和京津經濟發展的日漸分化。
1.3重化工產業適箱貨較少,使河北港口集裝箱業務發展緩慢
重化工產業的投入與產出基本都屬于大宗貨物,大宗貨物的裝運、轉運以及聯運比起集裝箱運輸繁瑣且缺乏效率,難以滿足國際經濟分工合作的要求。而集裝箱運輸,無論從裝運、轉運到聯運,都可以實現快速、高效率的門到門運輸,大大縮短了運輸時間提高了運輸效率。由于當前河北省產業重化工化的特點,港口吞吐貨物基本以煤炭,礦石和鋼鐵為主,這些大宗貨物已經成為河北港口的支撐,而集裝箱運輸發展緩慢,河北省重化工化的產業結構是導致缺乏集裝箱貨源是主要原因之一。
全球生產不斷提高環境標準和發展替代能源的意識逐漸加強,以及對“資源的詛咒”問題的關注,碳排放稅的征收的出現,對能源、礦石的需求在長期中將出現下降的趨勢。而經濟全球化和國內物流業的逐步開放,河北市場將與世界市場越來越緊密的合作,河北參與全球更緊密的分工,集裝箱運輸的發展將是實現高效分工合作的前提。港口集裝箱業務沒有足夠的貨源保證,直接影響港口的長足發展;港口集裝箱業務發展緩慢,反過來也會影響區域制造業和區域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集裝箱業務的滯后,也不能滿足京津城市經濟發展的要求,結果導致港城分離。
2發展輕工制造業是實現京津冀經濟對接合作的有效途徑
北京天津的幾千萬居民,擁有巨大的消費潛力,是河北輕工業潛在的最為廣闊的市場。河北省應該在京津周邊布局輕工制造產業帶,利用地緣優勢,以最高效率供應京津市場;同時,吸引京津市場的投資和人才,最終實現京津冀市場的高度融合。
2.1輕工業產業的特點及發展趨勢適合京津城市產業發展的要求
2.1.1產品直接服務于消費者
重化工工業位于整個工業產業鏈的上游,產出一般供應下游的產業。而輕工業的產出不同,更多的直接供應消費者。所以,消費市場對輕工業產業的布局更重要,而京津兩大市場恰恰是河北省發展輕工業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
2.1.2產品具有綠色、環保、安全性
綠色、低碳日益成為全球產業發展的趨勢,以節能減排為核心的新產業革命對輕工業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產品節能環保安全日益成為贏得消費者、增強企業競爭力的重要手段。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日漸國際化的京津地區,對產業進入的環境門檻越來越高,原有的重化工業要不斷遷出,新上項目也要遠離京津城區。比較而言,輕工業更為適合在城區或臨近地區布局。
2.1.3品牌化、集群化趨勢加強
重化工業產品多為大宗產品,主要供應的客戶有限,同質化特征明顯,市場上區分度較低。而輕工產品更加直接面向消費者,但由于當前產能過剩情況日漸凸顯,市場上多數產品供過于求。為發揮協同效應,降低生產成本,輕工業將加快向集群化方向發展,企業向產業集群集聚,專業化生產。市場向品牌集聚,為增強產品的辨識度,品牌化趨勢明顯,品牌競爭日趨激烈。而京津市場屬于相對高端的消費市場,品牌效應更大。河北利用自身豐富的勞動力和土地等(下轉第177頁)(上接第48頁)初級資源,結合京津的豐富資本、高端技術、人才和廣闊市場,具有創造品牌產品的更多優勢。
2.2河北省輕工業的發展現狀
2.2.1河北省輕工業發展滯后
“十一五”期間,河北省輕工業產值、主營業務收入、利潤三項指標在全國的位次分別由“十五”末的第8位、第8位、第7位下降為第9位、第9位、第8位,均比“十五”末后退一位。到2010年,河北省輕工業主要經濟指標占全省工業的比重多在15~18%之間,其中皮革毛皮及其制品、金屬制輕工業產品制造、日用玻璃制品等三個行業規模居全國前五位[1]。家電、日化、文教體育用品等行業發展滯后。從此可以看出,河北省輕工制造業規模較小,比重較輕,初級加工產品較多,技術含量和附加值較低,產業技術水平較低[2]。
2.2.2發展機遇
隨著發達國家經濟逐漸復蘇和國內經濟的企穩回暖,全球范圍對消費品需求穩步增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將大幅釋放國內城鄉居民消費潛力。城市化的快速推進,環渤海增長極的崛起,為擁有地緣優勢的河北省輕工業提供了歷史性發展機遇,輕工產品將成為新的增長亮點。東南沿海加工貿易企業由于區域內產業結構和環保政策調整,大批企業已有向北和內地轉移的趨勢。我省加工貿易規模整體偏小,發展空間巨大,利用這一機遇,吸收并承接加工貿易的轉移,必將促進我省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
3以加工貿易促進輕工業的發展是激活“兩環”優勢的著力點
加工貿易是河北外向型經濟和工業發展必須借助的工具,這是國際競爭的現實和中國國情所決定的。作為發展中國家,國內資源不足,技術落后,市場狹小,這決定了必須開展大規模出口,依靠更廣大的國外市場實現生產的規模效益和高速增長[3];而在進入國際市場初期、不掌握海外市場渠道的情況下,加工貿易是唯一可以利用的快速參與全球生產一體化的途徑。通過承接加工貿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是促進河北省輕工業產業升級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1]河北省輕工行業協會.河北省輕工行業發展報告[R].2011.
[2]河北省工業和信息化廳.河北省輕工產業發展“十二五”規劃[Z].2012,02.
第3篇:輕工業的特點范文
一、建設輕工業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建設輕工業園是我市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需要。目前,我市工業是以鋼鐵、焦化、發電、原煤、永泥等能源重工業為主導的產業體系,能源消耗十分驚人,每萬元GDP能耗高達5.176噸標煤,是的2倍,比全省的4倍還多。同時高能源消耗致使環境污染嚴重,節能減排形勢十分嚴峻。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的現狀,也反映出我市工業結構極不平衡,嚴重影響我市工業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建設輕工業園,加快發展低能耗低排放的輕工業是我市改變高載能、高排放工業結構,實現科學發展的重要途徑。
建設輕工業園是我市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我市城市化發展迅速,有大量的富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就業。輕工園的建設將促進一批勞動力密集型項目建設,必然會引導大量富余勞動力就地轉移,實現就業,從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
建設輕工業園是我市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提高招商引資水平、加快吸納民間投資的新要求。一是由于國家產業政策的調整,資源型重工業的門檻越來越高,部分民營企業只能通過關、停、并、轉尋找出路,有近30億元的閑散資金正在尋找投資渠道。輕工業園的設立必將為民營企業的轉型和吸納閑散資金提供發展平臺。二是盡快搭建高質量、大容量、特色化的招商平臺,對于承接東部產業轉移,吸引大型項目落戶,加速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創建布局科學、分工合理、優勢互補的新型經濟體系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
二、指導思想
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堅持“政府引導,市場主導,多元投入,快速發展”的原則,按照“產業集群、項目集聚、土地集約、管理集成”的要求,創新建設模式,大力實施項目帶動戰略,努力構筑輕工、機械加工等產業集群,加快工業產業結構調整步伐,形成我市經濟新的增長極。擴大農民工就業,推進城鄉統籌發展,促進經濟、社會、環境的和諧進步。
三、發展目標
到2015年,龍門生態工業示范區輕工業園工業產值達到20億元;到2020年,工業產值達到50億元,實現工業增加值22億元,地方財政貢獻超2億元,新增就業人數5000人以上。
四、區位確定和產業布局規劃
布局規劃的總體思路:按照“產業發展集群化,集群發展園區化”的原則,通過這一區域的快速發育,有效地接納重點產業和富余勞動力的轉移,成為新的資金流、物資流以及人流信息流的聚集區域。結合各行業的生產特點,規劃建設東區、北區兩個產業集群地。兩塊區域占地4778畝,實際可用地4046畝。
一是輕工業園東區。在城市環北路以北、小曲溝以南、高速路以西(退高速路120米)、鴨坡村以東,規劃一區總面積1235畝,實際用地1100畝。此區域規劃重點建設企業總部、研發中心、信息服務、工程咨詢、職工培訓中心等生產業以及紡織工業、農產品加工、醫療器械等產業。
二是輕工業園北區。位于小渠溝以北,寺莊溝以南,新108國道以西,溝北村以東,規劃區總面積3543畝,實際用地2946畝。主要布局倉儲、城市物流,農產品加工,裝備制造,節能、環保、節水設備制造,醫療器械等產業。并承接東部轉移的服裝、玩具、電子元件等產業。
五、入區項目要求
1、嚴格執行國家經濟發展產業政策要求;
2、符合園區發展規劃要求;
3、嚴格執行N家節能環保政策要求。要符合城市內工業廢水、廢氣、廢棄物排放標準的無污染工業。單位產品能耗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4、技術裝備要高。項目生產技術及主要設備達到同期國內先進水平:
5、適當控制投資規模。投資規模根據我市實際可分為兩檔:根據輕工業園東區主要擺布生產業,單個項目固定資產投資額不低于2000萬元,投資強度不低于每畝100萬元;北區主要擺布輕工加工區,單個項目固定資產投資額不低于500萬元,投資強度不低于每畝100萬元。
六、工作措施
(一)加強組織領導。為加強輕工業園建設的組織領導,成立“龍門生態工業示范區輕工業園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組成人員如下:
組長:市委副書記、市長
副組長:市委常委、副書記
市委常委、副市長
副市長
副市長
成員:市政府辦主任
市工信局局長
市經發局局長
市國土局局長
市住建局局長
市財政局局長
市環保局局長
市交通局局長
市招商局局長
市商務局局長
市煤炭局局長
市電力局局長
市中小企業局局長
市廣電局局長
市監察局局長
市國稅局局長
市地稅局局長
新城街道辦事處主任
西莊鎮鎮長
市工商聯書記
市工信局副局長
領導小組下設龍門生態工業示范區輕工業園管理辦公室,辦公室設在市工信局,具體負責園區建設的日常工作。同時為了加快園區建設,成立園區建設開發公司。
(二)做好發展規劃編制工作。由市工信局牽頭,按照輕工業園的發展目標和要求,組織有關專家,盡快高起點、高標準編制“龍門生態工業示范區輕工業園”發展規劃,使輕工業園的建設有序進行。
(三)創新工作,加快建設。實行土地統征統管。為改變以往項目等土地的現狀,做到讓土地等項目,通過土地統征統管來加快項目建設,由園區管理開發機構對園區土地進行統征。同時鼓勵民間資本參與園區內基礎設施建設。
(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實現快速發展。一是設立輕工業園建設專項資金。市級財政每年列支輕工業園發展專項資金,主要用于發展規劃編制、信息收集、項目儲備以及支持重點技術研發等工作。二是實行優惠的財稅政策。財稅部門按國家相關政策出臺區內新辦企業增值稅、所得稅優惠政策。(((市推進輕工業園建設優惠政策的意見》見附件1)
(五)嚴格入區項目管理。一是所有入區項目必須符合入區條件,堅決杜絕節能與排放指標不達標項目入駐:二是盡快制定入區項目的審核程序、用地以及投產后的管理辦法,簡化辦事程序,提高辦事效率,促進項目建設。《市輕工業園入區項目管理辦法》見附件2)
(六)實行大企業、大項目帶動戰略。一是重點實施“大公司,大集團”戰略,對于適合較大規模聯合生產的產品,建立以骨干企業為龍頭,實行專業化協作和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實現規模經濟效應。二是積極引導我市中省、民營骨干企業以大項目為切入點,以資金投入為紐帶,聯合中小企業組建跨行業的企業集團。
(七)做好項目儲備和招商引資工作。由招商局牽頭,經發局、工信局、環保局等部門配合,積極抓好項目的謀劃、儲備,并進一步加大招商引資力度,著力引進一批大企業,建設一批大項目。
第4篇:輕工業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長三角;制造業;分類;同構;趨同
[中圖分類號]F424.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6)12-0057-09
一、引 言
經過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高速發展,由上海市、江蘇省和浙江省組成的長三角地區已經發展成為我國的制造業中心和世界的制造業基地。2014年,該區域內制造業總產值達到23萬億元,占全國制造業總值的比重為23.5%,約占全球制造業總產出的5.8%。然而,作為區域經濟增長主要驅動力的制造業一直存在大而不強的問題,低端產能過剩,高端產能不足。尤其從全球價值鏈分工視角看,長三角制造業還處于中低端,國際地位低,附加值不高。盡管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很多,但由于制造業低端同構而引起的同質化競爭被認為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許多學者從測度方法、影響因素、形成機理、引致后果以及治理機制等不同角度對長三角產業同構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極大深化了人們對該現象的認識。事實上,對產業同構問題進行研究,除了需要關注上述幾個主要的方面外,如何對產業進行分類進而對其同構水平進行測度也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話題。因為,若選擇測度的產業范圍不同或對產業進行的分類不同,測度得到的同構水平是有差異甚至是大相徑庭的,這必然會對判斷該區域產業同構的真實狀況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
二、產業細分條件下長三角產業同構問題相關研究的梳理
唐立國(2002)測算了2000年長三角15城市三次產業的同構度,結果表明,各城市間產業同構水平都比較高,尤其是在地理上鄰近的城市之間,表征產業同構水平的產業結構相似系數均在0.93以上。同時該學者在產業細分條件下研究發現,15城市均將食品加工與食品制造業、紡織與服裝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制品制造業、電子通訊及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及設備制造業等作為主導產業[1]。陳建軍(2004)的研究表明,從1998年到2002年,上海與浙江工業部門的同構度均超過0.7,上海與江蘇工業部門的同構度均超過了0.8,而江蘇與浙江工業部門的同構度更高,甚至均超過了0.9,存在嚴重的同構現象。但當深入到細分產業層面考察,則會出現相反的情況。比如在紡織、化工、機械等領域,兩省一市間的產業同構水平是比較低的[2]。邱風等(2005)認為,長三角地區三次產業結構趨同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應當在產業細分條件下深入考查同構問題。為此,其將產業分為細分產業Ⅰ、Ⅱ和Ⅲ,并測算了同構水平。結果發現,長三角細分產業Ⅰ的結構相似系數平均為0.89,比三次產業結構的同構水平下降了8.24%。說明隨著產業細分同構水平呈下降趨勢[3]。靖學青(2006)測算了長三角15城市三次產業的同構水平,結果表明,除舟山外,城市間的相似系數均大于0.9。而當測算5個主要城市制造業、服務業的同構水平時發現,較三次產業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進一步,當細分到行業層面,其同構度的降低則更為顯著。也就是說,隨著產業細分,同構水平呈明顯的下降趨勢[4]。趙連閣等(2007)沿著陳建軍的思路,測算了1988~2005年長三角兩省一市工業部門的同構度,結果表明,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最高,均超過0.9,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浙江的同構最低,且呈逐年下降的發展態勢。在產業細分條件下對紡織業、化學工業、醫藥制造業、橡膠制品業同構水平的測算表明,江蘇與浙江紡織業的同構水平、三地之間化學工業的同構水平、上海與江蘇橡膠制品業的同構水平均很高,超過了0.9。這樣的結論表明即使細分到大類產業層面,有些產業的同構度依然很高,隨著產業細分同構水平并不一定出現下降[5]。李清娟(2006)的分析表明,上海制造業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以及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具有較強競爭優勢,是上海制造業層次較高的標志性特征。而浙江這兩類行業的產值比重相對較低,同時其紡織服裝業和食品加工業又很高,是制造業層次較低的標志性特征。說明即使在產業大類層面,長三角的產業同構度也不是很高。細分到產品層面也是如此,如上海的轎車產量是江蘇的6.8倍,是浙江的28.6倍,而江蘇紗產量則是浙江的3.3倍,是上海的16.1倍,差異性很明顯,不存在同構問題[6]。吳迎新(2013)的研究表明,從1999~2007年,上海與江蘇制造業的同構水平由0.92下降到了0.90,上海與浙江制造業的同構水平由0.86下降到了0.68,江蘇與浙江制造業同構水平由0.97下降到了0.84,均呈現下降趨勢,但仍處于高位。同時,即使在產品層面,也存在趨同。上海與江蘇有20余種工業產品產量分別超過10%的全國市場份額,江蘇與浙江有9個產品趨同[7]。蔣伏心等(2012)專門針對長三角制造業中高技術產業的同構問題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2001~2009年長三角兩省一市高技術產業同構度的平均值呈先下降后上升的發展變化態勢:2001~2005年,高技術產業同構度在波動中小幅下降,之后又在波動中上升,到2009年高技術產業結構相似系數的均值已經達到0.75。說明即使細分到高技術產業,同構度依然比較高[8]。
由以上文獻梳理可以發現,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不少學者在產業細分視角下對長三角的產業同構水平進行過考查,有的甚至細分到了產品層面。當然這些學者得到的結論不盡一致,有的認為隨著產業細分同構水平呈下降趨勢,而有的結論卻相反。同時,分析這些研究發現,多數學者在進行產業細分時缺乏系統性甚至帶有一定的隨意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對制造業所包含的大類產業進行同構水平測算時,產業的選擇存在缺乏系統性的傾向,僅列出相當少的一部分產業以舉例性方式加以呈現;二是在對產品進行細分時,緣于數據資料的限制等原因,也僅是選擇部分產品進行同構水平測算,舉例性呈現的特征更加明顯。正是這些不足的存在,使研究得出結論的可靠性和普遍性受到質疑。基于此,本文將在相對規范的分類基礎上,在大類層面上分門別類地系統梳理制造業的分類,并測度每種分類條件下各類產業的同構水平。這樣不僅可以構建起測度制造業中不同類型產業同構水平的體系,而且可以為正確認識不同類型產業同構水平的高低及其變化提供依據。
三、制造業的分類
《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GB/T 4754-2011)》將制造業這一門類劃分為31個大類行業,基于此,在不同的產業分類標準條件下,可以將制造業中的這些行業分為不同的類型,這也是進行制造業結構研究的前提。目前,對制造業大類層面各行業的分類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第一種:以生產的最終產品是生活資料還是生產資料為標準,可將制造業所包含的各大類行業劃分為輕工業和重工業。輕工業是指主要提供生活消費品和制作手工工具的工業,重工業是指為國民經濟各部門提供物質技術基礎的主要生產資料的工業。盡管從2013年下半年開始國家統計局在相關數據中不再使用輕工業、重工業這樣的分類,但其也是在我國沿用時間最長的一種工業分類方式[9]。分類結果見表1。
需要說明的是,在國家統計局關于輕工業、重工業的分類統計目錄中對某些大類產業細分到了其所包含的中類產業,本文考慮到數據的可獲性,僅從大類層面進行劃分。
第二種:以在產業鏈上所處位置是中游還是下游為標準或以生產過程是初級加工還是深度加工為標準,可將制造業所包含的各大類行業劃分為原材料產業和加工組裝產業[10]。原材料產業是指以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中采掘業所提供的產品為對象進行加工生產的產業,加工組裝產業是指以原材料產業所提供的產品為對象對其進行進一步加工、組裝進而形成最終產品的產業。分類結果如表2所示。需要說明的是,分類結果中并沒有包含所有制造業行業。
第三種,以勞動和資本兩種生產要素密集度相對高低為標準,可將制造業包含的各大類行業劃分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和資本密集型產業[11 ]。勞動密集型產業是指主要依靠使用大量勞動力,而對技術和設備依賴程度低的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則正相反。分類結果如表3所示。
第四種:以生產技術水平高低或最終產品技術含量的高低為標準,可將制造業包含的各大類行業劃分為低端技術產業、中端技術產業和高端技術產業[12]。分類結果如表4所示。
四、長三角各類型制造業結構趨同水平測度
測度制造業同構水平的方法有多種,本文選擇筆者曾經提出的結構重合度方法。選擇該方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該方法體系下有一個判斷同構與否的基準值0.667,這有利于更加清楚地認識同構問題[13]。關于該方法的詳細解釋可參見相關文獻[14]。同時,計算同構水平時,使用的是各行業的總產值指標,在沒有公布總產值指標的年份,以各行業的主營業務收入替代。所用數據均來源于相關年份《上海統計年鑒》、《江蘇統計年鑒》、《浙江統計年鑒》。為了方便后續的比較分析,本文在測度不同類型制造業同構水平之前,也以制造業包含的所有大類行業為基礎測度了整個制造業的同構水平。結果見表5。
由表5可以看出。
第一,不論是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還是江蘇與浙江,2000~2014年制造業的同構水平總體均呈波動下降的發展趨勢,即呈現出的是結構趨異而不是結構趨同。其中,上海與江蘇制造業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785下降到了2014年的0.716;上海與浙江制造業的同構度從2000年的0.727下降到了2014年的0.669;江蘇與浙江制造業的同構水平由2000年的0.847下降到了2014年的0.785。緣于此,長三角制造業的均值也呈波動下降的發展態勢,由2000年的0.786下降到了2014年的0.723。
第二,比較兩省一市制造業的同構水平可以發現,就多數年份而言,總是江蘇與浙江最高,上海與江蘇居中,上海與浙江最低。2000~2014年間,上海與江蘇制造業同構水平的均值為0.764,上海與浙江制造業同構水平的均值為0.677,江蘇與浙江制造業同構水平的均值為0.793。
第三,盡管長三角制造業呈結構趨異發展態勢,但直到2014年,同構水平仍然處于較高水平,均大于0.667這個基準值,說明長三角制造業仍然處于同構狀態。
(一)輕工業、重工業同構水平測度
依據表1中的分類,利用結構重合度指數計算得到的輕、重工業的同構度如表6所示。
分析表6中的數據可以發現。
第一,就輕工業而言,從2000~2014年,不論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還是江蘇與浙江,同構水平均呈波動下降的發展趨勢,呈現的是結構趨異,這與整個制造業同構度的發展變化趨勢是一致的。上海與江蘇輕工業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721下降到了2014年的0.579;上海與浙江輕工業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728下降到了2014年的0.565;江蘇與浙江輕工業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885下降到了2014年的0.757。與此相對應,整個長三角地區輕工業的平均同構度也呈現出波動下降的趨勢,而且比較發現,輕工業下降的速度要明顯快于整個制造業同構水平下降的速度。
第二,就輕工業而言,橫向比較發現,雖然上海與江蘇輕工業的同構度要稍高于上海與浙江輕工業的同構度,但這種差異并不明顯,上海與江蘇輕工業歷年同構度的均值為0.656,上海與浙江輕工業歷年同構度的均值為0.640。這組數據也說明,從歷年平均水平來看,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輕工業的同構度已小于0.667這個基準值,已不存在所謂同構問題。進一步,從2014年看,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輕工業的同構度已經降到0.600以下,已經遠小于0.667這個基準值,更不存在同構問題。而江蘇與浙江輕工業的同構度與之相比明顯要高,且即使經過多年趨異式發展,到2014年其同構水平仍然處于高位,甚至比兩省間整個制造業的同構度還要高。
第三,就重工業而言,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江蘇與浙江歷年同構水平發展變化趨勢不盡相同:上海與江蘇重工業的同構度呈現的是先在波動中上升而后在波動中下降的發展態勢,從2000年的0.814增加到了2005年的0.861,然后又下降到了2014年的0.758;江蘇與浙江重工業同構度的發展變化則正相反,呈現的是先在波動中下降而后在波動中上升的發展態勢,從2000年的0.840下降到了2005年的0.721,然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42;至于上海與浙江重工業同構度的變化則很微弱。
第四,就重工業而言,橫向比較發現,近幾年江蘇與浙江同構度最高,上海與江蘇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浙江同構度最低。當然,如果從所考查全部年份的平均水平看,同構度最高的是上海與江蘇,均值為0.807,其次是江蘇與浙江,均值為0.796,最低的是上海與浙江,均值為0.728。不過,不論怎么看,重工業同構度的數值不僅明顯高于判斷同構與否的基準值,而且還高于整個制造業的同構水平,說明重工業在長三角內部的確處于同構狀態。
第五,從長三角平均水平而言,到2014年,輕工業的同構度已經降至0.633,已經不存在同構問題。而重工業的同構度則要高很多,達0.774,仍然處于同構狀態。
(二)原材料產業、加工組裝產業同構水平測度
依據表2中的分類,利用結構重合度指數計算公式,可計算得到2000~2014年長三角原材料產業、加工組裝產業的同構度,結果如表7所示。
分析表7中的數據可以發現。
第一,就原材料產業而言,縱向的發展變化出現了分化,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總體上是結構趨同化的發展,而江蘇與浙江則是結構趨異化發展趨勢。從具體數據上看,上海與江蘇原材料產業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735上升到了2014年的0.805,由同構走向了更為嚴重的同構;上海與浙江原材料產業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666上升到了2014年的0.691,由不同構發展到了同構;江蘇與浙江原材料產業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844下降到了2014年的0.796,同構水平有盡管有所下降,但仍然處于同構狀態。與這種變化相聯系,整個長三角原材料產業平均同構度的變化呈現出的是微有上升的發展變化態勢,由2000年的0.748上升到了2014年的0.764。
第二,就原材料產業而言,橫向比較發現,多數年份而言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最高,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浙江的同構最低。同時,若以歷年同構度的平均值來看,則是江蘇與浙江最高,均值為0.790,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居中,均值為0.778,不過二者相差很小。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最低,均值為0.646,從這個角度看,上海與浙江原材料產業是不存在同構現象的,或者多數年份不存在同構,只不過到2014年已經發展到了同構狀態。
第三,就加工組裝產業而言,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江蘇與浙江之間同構水平的發展變化呈現出的趨勢并不一致。上海與江蘇加工組裝產業的同構度呈先上升而后下降的發展態勢,從2000年的0.857到上升到2005年的0.904,然后又下降到了2014年的0.769;上海與浙江加工組裝產業的同構度呈波動下降的發展態勢,從2000年的0.762下降到了2014年的0.684;江蘇與浙江加工組裝產業的同構度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發展態勢,從2000年的0.866到下降到了2005年的0.755,然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25。與這些變化相伴,整個長三角加工組裝產業同構度也呈波動下降趨勢,由2000年的0.828下降到了2014年的0.759。當然,盡管同構度是下降的,但其仍然要高于基準值,處于同構狀態。
第四,就加工組裝產業而言,從近年來的數據看,江蘇與浙江同構度最高,上海與江蘇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浙江同構度最低。如果從所考查全部年份的平均值看,上海與江蘇、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很接近,均值為0.823,最低的是上海與浙江,均值為0.721。
第五,就多數年份而言,長三角原材料產業的平均同構度要小于加工組裝產業的同構度,但發展到2014年則出現了翻轉,原材料產業的同構度反而要高于加工組裝產業的同構,前者為0.764,后者為0.759。
(三)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同構水平測度
依據表3中的分類,利用結構重合度指數計算公式,可計算得到2000~2014年長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同構度,結果如表8所示。
分析表8中的數據可以發現:
第一,就勞動密集型產業而言,同構度縱向的發展變化均呈現波動下降的趨勢,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740下降到了2014年的0.689;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766下降到了2014年的0.692;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897下降到了2014年的0.785;相應地,整個長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平均同構度的變化也呈現出的是逐步下降的發展態勢,由2000年的0.801降到了2014年的0.722。當然,盡管是結構趨異的發展態勢,但仍然處于同構狀態。
第二,就勞動密集型產業而言,橫向比較發現,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最高,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最低。同時,若以歷年同構度的平均值來看,也呈現出類似排序規律,歷年江蘇與浙江、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同構度的均值分別為0.839、0.724和0.719。
第三,就資本密集型產業而言,縱向看,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同構度均呈現的是波動中下降的變化趨勢。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816下降到了2014年的0.733;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740下降到了2014年的0.699;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呈現的是先波動下降而后又波動上升的發展趨勢,從2000年的0.826下降到了2005年的0.716,而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28。與此相對應,整個長三角資本密集型產業平均同構度的變化呈現出的也是波動下降的發展態勢,由2000年的0.794下降到了2014年的0.753。
第四,就資本密集型產業而言,橫向比較發現,近幾年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最高,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最低。而從全部年份的平均水平看,則是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最高,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最低。
第五,比較均值發現,長三角資本密集型產業的同構度要高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同構度,且兩類產業均處于同構狀態。
(四)低端技術產業、中端技術產業、高端技術產業同構水平測度
計算得到2000~2014年長三角低端技術產業、中端技術產業、高端技術產業的同構度,結果如表9所示。
分析表9中的數據可以發現。
第一,就低端技術產業而言,縱向的發展變均呈現波動下降的趨勢,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711下降到了2014年的0.538;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749下降到了2014年的0.584;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由2000年的0.884下降到了2014年的0.785;相應地,整個長三角低端技術產業平均同構度的變化也呈現出的是逐步下降的發展態勢,由2000年的0.782降到了2014年的0.636。表明就整個長三角而言,低端技術產業已經由同構發展為了非同構,尤其上海與江蘇、浙江之間更是如此。若從橫向看,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最高,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最低。這一點從歷年同構度的平均值也能得到印證。
第二,就中端技術產業而言,縱向的發展變化趨勢不盡相同,上海與江蘇同構度呈現的是波動中上升,而后又在波動中下降的變化趨勢,由2000年的0.826上升到了2005年的0.865,然后又下降到了2014年的0.767;上海與浙江同構度呈現的是波動中上升的變化趨勢,同構度由2000年的0.718上升到了2014年的0.808;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呈現的是先波動下降而后又波動上升的發展趨勢,從2000年的0.850下降到了2005年的0.722,而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02,呈微有趨異的變化趨勢。在這三種變化規律的作用下,整個長三角中端技術產業平均同構度的變化呈現出的是在很小的范圍內即0.770~0.800之間小幅波動的態勢。同時,橫向比較發現,到2014年,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最高,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最低。
第三,就高端技術產業而言,縱向的發展變化趨勢也不盡相同,上海與江蘇同構度呈現的是波動中上升,而后又在波動中下降的變化趨勢,由2000年的0.831上升到了2005年的0.852,然后又下降到了2014年的0.761,當然,總體呈現的是結構趨異;上海與浙江同構度呈現的是波動中下降的變化趨勢,由2000年的0.789下降到了2014年的0.686;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呈現的是先波動下降而后又波動上升的發展趨勢,從2000年的0.848下降到了2005年的0.737,而后又上升到了2014年的0.851,呈微有趨同的變化趨勢。在這三種變化規律的作用下,整個長三角高端技術產業平均同構度的變化呈現出的是在較小的范圍內小幅波動的態勢。同時,橫向比較發現,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最高,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居中、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最低。
第四,比較低端、中端和高端技術產業的同構度發現,低端技術產業的同構度最低,中端技術產業的同構度最高,高端技術產業的同構度居中。而且,低端技術產業已經不存在同構現象,而高端和中端技術產業仍然存在同構現象。
五、分析與討論
第一,分析表明,從整個制造業來看,到目前為止長三角仍然處于同構狀態。但有兩點應當明確:一是多年來該地區制造業呈現出的是結構趨異化的發展態勢,這是產業結構演進中最大的特點。二是上海與江蘇、上海與浙江的同構度已經顯著下降,同構明顯的是江蘇與浙江。尤其上海與浙江制造業已經基本不存在同構現象。因此,討論長三角的同構問題不能籠統言之,應當明確具體的狀況。
第二,分析表明,從平均水平而言,長三角兩省一市間輕工業、低端技術產業的同構度分別呈下降趨勢,也就是說出現的是結構趨異的發展態勢。而且發展到目前,其同構度已經低于判斷同構與否的基準值,即長三角的這些類型產業已經不存在同構現象。當然,緣于以上這些類型產業在長三角的地位,我們也不能因這些產業的非同構,就低估長三制造業的同構問題。雖然,到目前為止,從產值角度看長三角輕工業占制造業的比重已經下降到25%左右,低端技術產業占制造業的比重也僅有20%左右。但創新能力不強的問題十分突出,近期關于“圓珠筆之問”就是對此的真實寫照。長三角的上海是全國著名的制筆中心,浙江是世界聞名的制筆之鄉,但關鍵設備、核心材料仍然需要進口,甚至連筆尖上的鋼珠也需要進口[15]。
第三,分析表明,從平均水平而言,長三角兩省一市間重工業、加工組裝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高端技術產業分別呈現的是結構趨異的發展趨勢。不過,到目前為止雖然同構度有所下降,但仍然處于同構狀態,這仍然需要予以關注。在工業化發展進程中,重工業化、高加工度化、資本密集化、高端技術化曾是長三角乃至全國各地最普遍的選擇路徑。2014年,長三角重工業、資本密集型產業產值占制造業產值的比重已分別接近75%、70%,高端技術產業、加工組裝產業占制造業產值的比重也已分別接近制造業產值的60%、55%。一方面這些產業占制造業比重很高,另一面又處于同構狀態,理應引起重視。
第四,分析表明,從平均水平而言,長三角兩省一市間原材料產業呈現的是結構趨同的發展態勢,由同構走向了更為嚴重的同構,這是最值得注意的問題。盡管這類產業所占制造業的比重不是很高,其產值占制造業產值的比重約30%。但一方面這類產業不僅是高能耗的,而且是高排放的,在資源與環境約束日益加大的背景下,轉型發展已迫在眉睫。另一方面這類產業也是目前產能過剩集中的行業,行業業績近年來持續下滑,“去產能”的任務十分繁重。
第五,測算結果表明,2005年似乎是一個特殊的時點。因為,不論從整個制造業看,還是從重工業、加工組裝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中端技術產業、高端技術產業等類型產業看,在本文所考查的時段內,上海與江蘇的同構度在該年份總是最高點,而江蘇與浙江的同構度在該年份總是最低點。究其原因,在新世紀初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申辦奧運會、世博會的成功,極大刺激了長三角經濟的增長并使其快速融入了全球分工。在江蘇追趕上海的過程中,加工貿易在兩地迅速發展,由此形成了結構上的趨同。與此同時,浙江與江蘇相比而言,則走的是一般貿易的路線,因此出現的是結構上的趨異。當然,經過幾年的超常規發展,當“入世申會”效應逐步消退后,同構的狀況又出現了另外一種發展趨勢。
六、結論與建議
第5篇:輕工業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新疆;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三次產業;城市化
中圖分類號:F290文獻標識碼:A
經濟結構變革的核心是農業產值份額下降、非農產業產值份額提高(產值結構轉換)和農業勞動力份額下降、非農產業勞動力份額提高(就業結構轉換)這兩個過程。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勞動力份額從農業向非農產業的轉移滯后于產值份額的轉移,或者說就業結構的轉換滯后于產值結構的轉換。其原因主要由以下兩個方面:一是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過快、勞動力供給豐富;二是發展中國家的非農產業(特別是工業)技術進步速度比農業快,資本集約程度高于農業,從而勞動生產率較高,影響了勞動力的吸收。由于這兩點原因,發展中國家就業結構轉換不如發達國家類似發展過程來得成功。
在新疆經濟結構變革過程中,農業勞動力份額的下降嚴重滯后于農業產值份額的下降,即就業結構的轉換嚴重滯后于產值結構的轉換,這也就是新疆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非典型性特征,新疆農業勞動力份額下降滯后于農業產值份額下降的特征,并不是由于經濟發展水平造成的;相反,這一特征正是相對于既定的發展階段才存在的。進一步的考察會看到,這一特征是由于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所采取的經濟發展戰略造成的一系列經濟結構非典型性特征的后果。
一、非典型性特征之一:輕重工業比例失衡,吸納勞動力能力難度加大
霍夫曼比率是指消費品工業凈產值與生產資料工業凈產值之比。德國經濟學家霍夫曼將全部產業分為消費資料產業、資本資料產業與其他產業三種類型,他認為凡是某類產業的產品有75%以上是消費資料的歸消費資料產業,75%以上是資本資料的歸資本產業,不能歸入上述兩類的就歸入其他產業。霍夫曼比率適用于衡量一定時期的工業化水平和工業化階段的劃分。霍夫曼比率越小,重工業化程度越高,工業化水平也越高,它表明隨著工業化程度的提高,加工程度的產業份額比例將增長。
“霍夫曼比率”中運用的工業分類標準,使用的消費品工業和資本品工業的劃分與我國理論研究和實踐中所使用的輕重工業的劃分方法比較接近。因此,本文將此法修正為運用輕重工業產值之比,來近似判斷新疆工業化水平所處階段。新疆工業的這一指標從1949年的25.53下降到2001年的0.34,可以判定新疆的工業化發展水平越來越高,而且目前已經處于霍夫曼所認為的第四階段,即最高階段。顯然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新疆雖然重工業所占比重較大,但并未真正進入工業化發展階段。
由于歷史原因以及現實條件的影響,新疆工業發展呈現以下特點:
第一,重工業偏重,輕工業偏輕,輕工業、重工業發展不協調。世界多數傳統工業化模式在工業結構轉換中始終或是曾經以輕工業為中心向以重工業為中心發展,而新疆工業發展則與之不同,新疆從工業化初期開始重工業就占有較重要的地位,建國后重工業經歷了一個快速發展時期。1949年新疆的輕工業、重工業之比為95.9∶4.1;1978年輕工業、重工業之比達到41.6∶58.4,重工業的年均增長速度為24.2%,超出輕工業(10%)一倍以上;改革開放以來,輕工業、重工業發展不協調的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2002年輕工業、重工業之比為26.4∶73.6。根據霍夫曼理論,當一國的重工業與輕工業產值之比(霍夫曼系數)大于1時,說明該國進入了重化工業時代。我國目前的這一比例大概為1.5左右,世界發達國家的霍夫曼系數一般在2.5和3之間。新疆的霍夫曼系數達到2.8。新疆的霍夫曼系數高并不意味著新疆的工業化程度就高,而恰恰是輕重工業發展失衡的表現,由于沒有經歷輕工業充分發展的階段,現在新疆的輕工產品自給率很低,大多數日用品依賴從內地調入。這種輕重工業發展失衡導致工業與農業之間缺乏整體聯系,工業既不能為農業發展提供必要的市場和技術支持,又不能有效地吸收農業中的剩余勞動力。輕重工業比例不協調已成為制約新疆經濟發展的結構性因素。
第二,輕工業、重工業內部結構不合理。新疆的重工業中采掘、原料工業所占比重較大,占87.3%,加工工業所占比重較低,只占12.7%;而輕工業的91%以農產品為原料,以非農產品為原料的不到10%,因此新疆的輕工業仍處于以初級加工為主的初級發展階段。受計劃經濟體制下分工格局的影響,新疆的工業主體建立在資源初級開發基礎上,能源、原材料產品比重大,加工深度不夠,產品加工層次低、附加價值低,資源優勢尚未真正轉化為經濟優勢。目前,新疆產量比重較大的工業產品主要是采掘與工業原料,如原煤、原油、天然氣、紗、鋼材、水泥、化肥等。這表明在生產這些產品方面新疆具有一定的資源優勢和勞動力優勢,而加工品制造能力則不足,如新疆沒有家用電器的生產,汽車產量不到4,000輛,僅占全國汽車總產量的0.12%。面對加入WTO的新形勢,新疆的資源優勢正趨于弱化,新疆工業發展將面臨新的挑戰。
第三,工業中國有經濟所占比重較高。新疆的工業建設主要依靠國家投資,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轉變,2002年全國國有企業及國有控股企業數量比重僅為22.65%,其產值比重為40.78%,同期新疆國有經濟比重卻居高不下,國有企業及國有控股企業數量比重為63.93%,其產值比重為83.19%,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以上。國有經濟比重高、解困難度大制約著新疆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
總之,工業化發展滯后,加大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難度。2004年新疆三次產業的比重為20.2∶45.9∶33.9,工業產值構成中石油化工、能源、有色金屬等占較大份額,但并不能以此就斷定新疆工業化已進入重化工業階段;相反,這是新疆工業水平低、產業結構不合理的表現。事實上,由于新疆的重工業是在輕工業并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情況下發展的,屬于資源開發為主導的偏重工業產業結構,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相對不足,無法拉動和刺激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和流動。同時,重化工業的技術擴散空間狹窄,很難為鄉鎮企業發展提供生產空間和支持條件,而且新疆的石油石化多屬中央企業,精深加工部分大都建在區外,與當地經濟的關聯度低,對地方國民經濟的支撐和帶動作用也是有限的。屬于地方工業的大多數行業,特別是吸納勞動力較多的制造業在新疆工業產值構成中所占的比例偏小,一般規模小,產業鏈條短,市場需求彈性空間小,提供的就業崗位有限。
二、非典型性特征之二:第三次產業十分不發達,產業內部結構不協調
英國經濟學家科林?克拉克的研究表明,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當人均國民收入進一步提高后,勞動力繼而向第三產業轉移。勞動力的這一轉移順序,為發達國家早期的發展歷史所證明。因為在這些國家,工業中技術起初是勞動密集程度很高的,而隨著技術的進步,工業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逐漸降低,勞動力開始流向第三產業。而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在一開始就接受了資本密集程度較高的技術,吸收勞動力的潛力受到限制。因此,第三產業在吸收農業剩余勞動力中的作用大大加強。可以看到,繞過第二產業而直接把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轉移到第三產業中就業,是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轉移的一個特點,這一特征在中國尤其是在新疆表現得尤為突出。
新疆第三產業發展現狀與存在的問題是:
1、新疆第三產業比重與差距。從新疆近10年經濟發展中三次產業間產出結構(產值)和投入結構(勞動力)的變化情況看,1990年三次產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分別為24.1%、43.8%、32.1%,三次產業的勞動力比重分別是61.27%、17.39%、21.34%,到2001年,三次產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已調整為14.1%、51.8%、35.6%,勞動力比重分別是54.77%、13.75%、31.43%,符合產業發展的一般規律。但是,近年來經濟運行中遇到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難題,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第三產業發展相對緩慢,發達國家第三產業的增加值比重目前均在70%左右,一些發展中國家,其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也在40%以上,而2001年,新疆不到40%。相比之下,新疆第三產業發展存在兩個明顯不足:一是起點低;二是速度相對緩慢。
2、新疆第三產業內部結構與差距。與世界大部分國家相比,新疆與全國一樣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偏低,但從第三產業內部結構看,第三產業結構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應階段的水平相比,交通業、商業并不落后,真正落后的是教育、科技、信息、金融等新興行業,發達國家新興行業一直較大幅度上升。雖然,新疆新興行業如房地產、金融、社會服務業、衛生體育業、文教業在第三產業中的比重由1990年的17.2%提高到2001年的21.6%。但與發達國家走過的相應階段相比,與我們要達到的目標相比,還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第三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發展不平衡,發展水平低,體現出典型的“流通類”特征。傳統商貿流通一業獨大,占到三產全部增加值的50%左右,新興第三產業金融、保險、綜合技術、科研、信息咨詢服務業發展明顯滯后,比例普遍在10%左右。服務業的行業類別眾多,能廣泛提供簡單勞動、復雜勞動的就業機會,既可以為經濟發展做出積極貢獻,又可以為社會穩定發揮重要作用。但是,新疆服務業總體發展落后,處于第三產業欠發達狀態。新疆第三產業在總量上與全國其他發達地區差距很大,在結構上與全國相比,表現為更低的層次和更不合理的結構。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信息咨詢業等新興行業,在市場經濟中既是經濟運行的基礎,又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相對不足。從第三產業內部結構上看,發達國家主要以信息咨詢、科技服務、金融保險等新興行業為主,而新疆仍以傳統的批發零售貿易和餐飲業、運輸倉儲和郵電業為主,2002年這兩個行業增加值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42.93%,屬于新興行業的金融保險業、房地產業增加值合計僅占第三產業增加值的12.13%,比全國平均水平還低10.17個百分點。因此,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力促進新疆第三產業的發展面臨總量和結構的雙重挑戰。
第二,第三產業內部仍呈現國有經濟為主體的格局。第三產業中,國有經濟主要分布在交通運輸、郵電通訊、金融保險等行業,因而國有經濟在第三產業中所占比重最大、集體經濟相對較弱,個體經濟廣泛地活躍在商業、飲食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尚未形成規模經濟,仍處于低層次、低水平、低收入、低產出的科技含量低的初級資金積累階段。
第三,第三產業發展與一二產業發展的要求不相適應。為工業企業服務的科技開發、產品設計、營銷服技服務長期發展不足,使處于工業化加速發展階段的工業低水平徘徊,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農產品的增長和農業的增值。
第四,第三產業中的科技含量低。科學研究綜合技術服務業占的比重最低,有悖于依靠科技進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的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原則。2001年新疆科學研究綜合技術服務業占GDP的比重為0.37%,比全國平均水平0.71%低0.34個百分點。
第五,新興產業發展遲緩。與先進城市相比,新疆第三產業除規模小、比重低、整體水平不高外,更主要的差距體現在旅游、信息、房地產、金融、保險等新興產業所占份額太小。目前,旅游業占全球GDP的份額已超過10%,2001年新疆旅游業占GDP的比重為5.2%,全省房地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僅1.29%,低于全國水平0.6個百分點;北京金融保險業占GDP的比重1997年達到13.6%,而新疆2001年才達到3.29%。
第六,從就業方面看,第三產業傳統部門主要是商貨、社會服務業及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訊業吸納了絕大部分勞動力,而金融、房地產、科技等行業的從業人員增加有限。
城鎮化與工業化水平低是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的主要原因。2004年全國的城鎮化率平均為41.8%,而新疆的城鎮化率只有35.2%,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6.6個百分點。若按照美國經濟學家霍利斯?錢納里的城市化“標準結構”,人均GDP在1,000美元時的城市化水平應為63.4%。2004年新疆人均GDP接近1,360美元(2004年新疆人均GDP為11,199元,按匯率8.6計算得來),城鎮化水平相差甚遠。2004年全國工業化水平為45.9%,新疆工業化水平為33.9%,低于全國平均水平12個百分點。這樣的城鎮化水平和工業化水平致使第三產業難以快速發展,其產值及就業發展滯后。
今后,第三產業的產值和就業比重將明顯上升,成為吸納農村人力資源的主要領域。由于第三產業具有勞動密集、易于進入的特征,又符合時展的趨勢,所以大力發展新疆第三產業是促進新疆經濟發展,開發農村人力資源的有效途徑。今后第三產業的調整方向是:在繼續加強交通運輸、批發零售、餐飲等傳統產業發展的同時,大力發展旅游、社區服務、現代物流業和金融保險業等新興行業。
三、非典型性特征之三:城市化水平較低,吸納剩余勞動力能力有限
經濟發展的重要結果之一就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隨著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生和發展,必然會形成區位,并在空間上集聚。非農產業區位的發展和空間集聚就是城市產生的原因。但城市化滯后是中國非典型化的工業化發展的一個嚴重缺陷,它使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許多問題。
首先,城市化滯后使二元經濟矛盾不斷拉大。改革以前,中國重工業超前發展和城鄉隔絕制度下的城市化進程,造就了十分懸殊的二元經濟結構。1985年以來,由于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緩慢,使二元經濟矛盾又進一步拉大。特別是近幾年,由于大量勞動力滯留在比重不斷下降的農業上,導致農民收入不斷下降,農民與非農民的收入差距迅速擴大。這表明城鄉二元經濟矛盾不斷拉大。
其次,城市化滯后帶來的第二個問題是農業勞動力就地分散轉移,既不穩定也不經濟。我國農民一直存在從農業部門向比較利益較高的非農業部門轉移的強烈沖動,然而由于城鄉隔絕體制的限制,基本上是離土不離鄉,實行就地轉移,半徑不大。農民既不將非農產業看作自己的長期生存保障,脆弱的非農業也不給農民提供穩定的工作機會;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發展滯后,農村工業被迫就地發展,形成了十分分散的格局,致使“聚集效應”十分低下。致使鄉鎮工業長期徘徊在小型化、分散化的低層次上,難以進入現代化工業層次。到后來,這一問題是造成鄉鎮企業發展勢頭減緩,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第三,城市化滯后帶來的第三個問題是導致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第三產業要依托于人口、工業相對密集的區域,才能發揮其服務功能的規模效益。由于城市化滯后使人口和工業分布過度分散,嚴重抑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反過來又大大延緩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過程,從而使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變動,都大大偏離反映世界工業化發展一般規律的標準結構,由此把中國的大多數人口排斥在現代工業文明之外。
新疆的城市化進程也不例外,新疆的城市化水平低同樣也阻礙了新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1、城市化水平相對較低,吸納農村人口的能力有限。盡管新疆城鎮的形成和發展歷史悠久,但由于城市大多是政治行政中心,經濟功能較弱,而且規模小,布局分散。由于工業化發展滯后,新疆城市化水平一直較低。2004年新疆共有城市22個,鎮229個,城鎮人口690.11萬人,占全區總人口的35.15%。改革開放以來,新疆城市化水平年均1.3%的速度增長,大大低于工業化和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城市化進程緩慢,城市化水平相對較低。農業產值占GDP份額已下降到20.2%,但農業就業比例仍然高達54.2%,農業就業和產值存在著較大的偏差,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化水平低,城市結構體系不合理,缺少大中城市,特別是在廣闊的南疆,城市數量少,間距長,對小城鎮特別是廣大農村的集聚和帶動效應有限。
2、城市發展不平衡,城鎮人口分布不協調。新疆人口的分布南、北疆各約占47%,東疆約占6%。但從城鎮人口的分布看,南疆城鎮人口占24.97%,城鎮化18.13%,北疆占68.92%,城鎮化51.66%,東疆占6.11%,城鎮化35%。城鎮人口比重增加,農村人口比重減少,這是工業化過程的必然趨勢。目前,北疆城鎮分布較為密集,大小中心城市已經基本形成(如烏魯木齊、石河子、奎屯、克拉瑪依、伊寧等)。然而,在廣大南疆地區,除庫爾勒已形成一定的規模,具有工業交通中心的地位外,目前還缺乏實力較強的、可以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中心城市。
(作者單位:烏魯木齊職業大學經濟貿易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王斌等.新疆區域工業發展水平與結構初步研究[J].干旱區地理,2004.1.
第6篇:輕工業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全要素生產率;方向性距離函數;制造業;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
中圖分類號:F27;C939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6.012
目前,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一面,就是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資金和物質要素投入向依靠全要素生產率的帶動轉變。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還認為,經濟長期可持續增長的唯一動力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因此,全要素生產率成為了國內外眾多專家研究經濟發展的重要工具。縱觀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不難發現,制造業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但“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發展方式制約了制造業部門的可持續發展,也直接影響著我國區域經濟增長的速度與質量。針對目前我國制造業有關效率的研究中所忽視的環境污染的影響,本文運用考慮了環境因素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采用2001-2009年中國制造業31個兩位數行業的面板數據,基于能源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實證研究了中國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及其變動的根源。本研究將經濟增長方式與環境因素聯系起來,對于探討資源環境雙重約束下中國制造業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及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涌現出眾多的有關生產率問題的研究成果,其中對制造業部門生產率的測算更是受到了格外的關注。通過對現有文獻的梳理發現,我國制造業生產率的早期研究多數側重于傳統生產率的測度,也就是忽略了各種環境污染對行業生產率的影響。這類研究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第一,在制造業總體層面探討我國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及趨勢[1-3];第二,從區域、企業或行業的微觀層面測算生產率水平并分析趨勢[4-6];第三,深入分析中國制造業生產率變動的影響因素[7-9];第四,探析我國經濟增長與制造業生產率的提升之間的關系[10-12]。上述研究存在的不足之處在于,在測算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時,主要側重于測算生產過程中的“好”產出,而沒有考慮生產過程中產生的諸如廢氣、廢水和固體廢物等之類的“壞”產出的影響。現實中,工業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壞”產出會對社會環境產生負效應,從而給整個經濟帶來顯著的外部成本。因此,運用上述研究成果對現實經濟進行指導容易產生偏差和失誤。把環境污染因素看作具有負外部效應的“壞”產出,并同“好”產出一并引入到生產過程,還要追溯到Chung等人提出的方向性距離函數法(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簡稱DDF)[13]之后,運用該方法來分析環境污染在制造業生產過程中的制約作用可以顯得更為科學合理,并且能夠較好地解決“壞”產出的效率評價問題。基于此,一系列的評價方法又相繼被學者們構建出來。例如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簡稱ML生產率指數),它不僅具有Malmquist指數所具有的良好性質,而且其在考慮了“好”產出提高的同時,還要求“壞”產出的不斷減少。
近年來,隨著環境問題的日益突出,運用ML生產率指數實證分析全要素生產率的研究逐漸增多。Fare等人以美國制造業1974-1986年的數據為例,運用ML生產率指數法測算了其全要素生產率,研究結果表明,在考慮環境因素下所測算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速度要高于忽略環境因素時的測算值[14]。與此結論相類似,Yoruk和Zaim分別用考慮環境污染等“壞”產出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和不考慮環境污染等“壞”產出的Malmquist生產率指數分別測度并比較了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生產率,研究發現前者的測算值要高于后者[15]。國內方面,王兵等運用ML生產率指數法測度了1980-2004年APEC 17個國家和地區包含CO2排放的全要素生產率,認為在引入環境管制之后,APEC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水平得到了提升,且從分解指標來看,技術進步是生產率水平提升的主要動力[16]。在此基礎上,田銀華等采用序列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法估算了1998-2008年中國各省環境約束下的全要素生產率,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不足10%,反映了我國經濟粗放增長的現實,同時他們也得到技術進步是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重要源泉,而技術效率則呈現出下降的態勢[17]。吳軍在全要素生產率(TFP)分析框架中加入環境影響因素,通過ML指數測度分析了基于環境約束的我國1998-2007年地區工業TFP增長及其分解,并檢驗了其收斂性[18]。陳詩一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對改革以來中國工業TFP進行了重新估算,發現正確考慮環境約束的實際TFP比傳統不(正確)考慮環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19]。以上綜述表明,環境約束和環境規制被學者們更多地用來研究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而且這將使得所估算的全要素生產率更具有生產經濟學的含義[20]。
然而,由于選取樣本的差異,分析周期的差別,以及研究視角的不同等因素的影響,實證過程中即使運用相同的方法,最終得出的結論也難免會出現不一致的情況,這也使得后續的研究存在較大的探索空間。現有文獻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路徑,本文試圖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深入拓展:首先,運用中國制造業2001-2009年31個兩位數行業的面板數據重新估計考慮環境因素影響情況下的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同時與在不考慮環境因素的情況下用傳統的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測算結果進行比較;其次,注重考察資本深化、行業規模、科技投入和環境污染等現實因素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
二、數據和方法
(一)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研究選取的時間跨度是2001-2009年,各項指標數據均選自于相應年度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和《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為確保《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標準》(2002)實施前后統計數據口徑的一致,本研究剔除了“工藝品及其他制造業”和“廢氣資源和廢舊材料回收加工業”兩個行業,即我們的研究對象是中國制造業31個兩位數行業。涉及到的變量有:工業總產值、工業SO2排放量、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全部從業人員人數和能源消耗,所有價值量數據都平減為2001年為基年的可比價序列。本文中所使用的投入產出變量定義如下:
1.產出指標。其一,“好”產出。對于產出變量指標的選擇,部分學者選用工業增加值,還有學者選用工業總產值,我們根據陳詩一[19]的作法,由于一般經濟增長方程中含有中間投入品性質的能源要素,為此將含有中間投入成本的工業總產值作為產出指標。
其二,“壞”產出。“壞”產出表現為負的社會效應,是一種環境成本。對于如何全面科學地表達一國或者一個地區的環境污染水平,目前尚未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參照相關文獻的作法,本文選取工業SO2排放量來表征環境污染水平。
2.投入指標。
資本和勞動為大量文獻所使用的傳統投入要素,我們在此選取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和全部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分別作為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指標。參考以往文獻的一致作法,本文中能源因素作為投入指標處置。本文采用各行業煤炭消耗量代表能源變量。因為,一方面煤炭消耗直接關系到SO2排放量;另外一方面煤炭資源是不可再生資源,其使用效率關系到能否真正意義上保護環境,節約資源。
為了分析比較環境因素對不同制造業行業的影響效果,本文將中國制造業分為輕、重工業兩個類別分別加以考慮。一般認為,與輕工業相比較而言,重工業的生產方式和高排放與高耗能更為相關。因此,本文按照2001-2009年中國制造業各行業能源消費總量的平均值由高到低的序列,將我國31個制造業行業劃分為高、低能耗兩個類別(其中高能耗組15個行業,低能耗組16個),并以此作為重、輕工業的代表。各組別制造業的投入產出指標的描述性統計量,見表1。
從表1中不難發現,就工業總產值、全部從業人員年平均人數兩項指標來看,重工業分別是輕工業的3.3倍和2.2倍,但是其余三項指標的行業差異卻十分顯著,其中,重工業類的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是輕工業類的4.8倍,其能源消耗的平均水平是輕工業類的13.2倍,而二氧化硫排放量差異最大,倍數達到了34.9倍之多,重工業類遠遠高于輕工業類。這些數據表明,中國高投資、高能耗和高排放的發展方式并沒有帶來預期中工業總產值的高增長,這似乎表明重工業行業的生產率水平應該不是很高。此外,從標準差的數據來看,重工業類的各項指標的數值都遠遠高于輕工業類,尤以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硫排放量為甚,前者分別是后者的24.4倍和70倍。基于這些統計數據,可以看出中國重工業行業的資本投入、能源消耗水平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不但水平高,并且波幅變動也較大。
(二)研究方法
目前,估算全要素生產率的方法有指數法、索羅殘差法和前沿生產函數法三種。指數法以全要素生產率的基本定義為依據進行估算,例如Abramowitz提出了代數指數法(Arithmetic Index Number Approach,AIN),其基本思想是把全要素生產率表示為產出數量指數與所有投入要素加權指數的比率[21]。該類方法非常直觀地體現了全要素生產率的內涵,但對于不同的投入與產出指標,存在著指數公式的選擇問題。1957年索洛以生產函數形式給出了生產率測度的公式,第一次將技術進步因素納入到經濟增長模型中。他認為全要素生產率是指各要素如資本和勞動等投入之外的技術進步和能力實現等導致的產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貢獻后所得到的殘差,這一概念即為后來被稱為的“索洛殘差”,之后索羅殘差法在生產率估算中開始流行開來。
根據索羅殘差法測算出來的全要素生產率,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分析各種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識別經濟增長是效率型增長還是投入型增長,從而為制定和評價長期經濟政策提供基礎。但是
運用索羅殘差法估算TFP也存在缺陷,它需首先確認投入指標的產出彈性,然后通過CD生產函數或者超越對數函數進行回歸,這就隱含假定了生產在技術上是充分有效的,
從而忽略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技術效率提升的影響。
前沿生產函數法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該方法又分隨機性和確定性前沿生產函數兩種。隨機性前沿生產數法需先驗假定效率隨時間的變化而變化,而且它無法同時模擬“好”產出和“壞”產出兩種情況并存的生產過程,只能擬合出單產出的生產過程,因此該方法對于本研究不適用。確定性前沿生產函數又分為兩種估計方法,即參數估計和非參數估計。參數估計法的特點是需要設定總量生產函數的形式,然后通過回歸分析估計相關參數,求得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增長率。而非參數估計法的最大特點是無須對生產系統輸入輸出之間進行明確的生產函數表達式的假定,而采用線性規劃的方法求得生產率的相對變化。兩者中以非參數法更為常用,典型的就是數據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簡稱DEA)方法。DEA模型能夠避免參數化模型有可能產生的模型設定誤差和隨機干擾項正態分布假定不能滿足的缺陷;其次,該模型能同時模擬多產出、多投入的生產過程,對“好”產出和“壞”產出也能分別進行處理[24]。因此,綜上所述,本研究選用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法來測算環境約束下的中國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關于ML生產率指數法的更多技術細節,可以參見Chung等[13]。
三、實證分析
(一)基于環境約束的中國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變化分析
中國制造業31個行業各投入的產出變量的換算結果,見表2。
表2是中國制造業31個行業各投入產出變量的核算結果情況,其中MIPL、MLECH、MLTCH分別為運用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的ML生產率指數法的所測量的全要素生產率、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結果,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份額的計算方法參照吳延瑞[23]以及陳詩一[19]。
由表2可以看出,各行業的差異較為明顯,工業總產值的增長率由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9%到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29%不等;所估算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數處于煙草加工業的0.937到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1.130之間;生產效率指數也在印刷業記錄媒介的復制行業的0.921到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的1.053之間變動;而技術進步率則全部處于增長的狀態,從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的1.000 175(保留3位小數,表中值為1.000)到電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的1.115不等。那些產出增長慢以及全要素生產率和技術進步不快甚至為負的行業基本上都是高能耗的勞動密集型的制造行業,如造紙及紙制品業、紡織業、家具制造業、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印刷業記錄媒介的復制、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等,這說明對中國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行業進行節能減排和升級轉型改造已十分必要。而工業總產值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以及技術進步率較快的行業都是輕工業和高新技術行業,例如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等之類的,從這也可以看出信息技術等高新技術行業在工業發展和產業轉型升級中的重要性。除了造紙及紙制品業、紡織業、家具制造業、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印刷業記錄媒介的復制、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皮革毛皮羽絨及其制品業、煙草加工業這9個行業外,其余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均為正,且所有行業都處于技術進步的狀態,這又進一步說明了中國制造業生產率的提高主要是由技術進步而非生產效率引起。生產效率變化為正的行業主要集中于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儀器儀表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醫藥制造業、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等高新技術產業,同樣凸顯出高新技術行業在新型工業化進程中的重要性。此外,從各行業生產率的貢獻份額上也可以看出,沒有一個行業的生產率貢獻度超過50%,所有行業還是表現為要素驅動型的粗放型增長,貢獻度超過40%的行業有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和儀器儀表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負增長的行業對產出的貢獻也為負,其中,煙草加工業的生產率貢獻度最低,達到-48.46%。從各投入指標的角度看,資本存量和能源消耗的平均增長率要明顯高于勞動就業的平均增長率,這表明在當下要素驅動型的工業增長模式中,資本和能源要素發揮了主要的作用。
(二)環境因素對中國制造業生產效率測度的影響
本部分通過測算沒有考慮環境因素和將環境污染作為“壞”產出情況下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數及其分解,以檢驗環境因素對中國制造業生產效率的影響。見表3。
注:表中數值通過各行業加權平均(權重為工業增加值份額)和整個期間進行幾何平均計算得到;*、**、***分別代表10%、5%和1%的顯著性水平,使用學生氏t檢驗統計量進行檢驗,且基準模型是考慮了環境污染的ML生產率指數法,零假設為沒有考慮環境因素情況下所估算的全要素生產率、技術效率指數和技術進步指數的均值等同于ML生產率指數法所測得的對應值。
表3所示的即是兩種模型所估算得到的2001年以來我國制造業全行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技術效率指數和技術進步指數的平均發展速度,權重分別為各行業的工業增加值份額。
從表3估算結果可以看出,在正確考慮了SO2排放量和能源消耗的情況下,中國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4.49%,技術效率指數年均增長0.59%,技術進步指數年均提高3.83%。估算結果說明,“十五”以來,我國制造業環境全要素生產率所獲得的較大改善主要是歸功于技術進步而非技術效率的提高。事實上,在表3中由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法所估算的全要素生產率和技術進步率的變化方向都變正為負,分別為-7.96%和-9.88%,都一致地小于ML生產率指數法的對應結果;而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法所測得的技術效率增長情況為2.57%,高于環境約束下所測得的0.59%的增長速率。由此,可以初步得出一個結論,即考慮環境管制后,中國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水平會得到提高,而且其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也會提高。
進一步地,為了檢驗使用ML生產率指數法所測度的全要素生產率、技術效率和技術進步指數是否在統計上顯著大于由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法所測度的對應估算值,本文參照Kumar等人的方法進行了t統計量檢驗[24]。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由Malmquist生產率指數法所測得的全要素生產率估計值在統計量上要顯著小于ML指數法的估算結果,同時,傳統方法估算的技術進步指數也要顯著小于ML指數法對應的估算值,二者都通過了1%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但是這兩個模型所測量的技術效率值并沒有顯著的差異。因此,在考慮環境管制后,所測得的全要素生產率要高于不考慮環境因素的估算值,且技術進步是其增長的源泉,但是生產效率的估算差異不顯著。本文的這一發現支持了Jeon和Sickles[25]、王兵等[16]、葉祥松和彭良燕[26]以及王昆[27]的結果。
四、基于環境約束的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因素的計量分析
前文在環境約束的條件下,對中國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進行了分析,這里將分析環境約束下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影響因素。到目前為止,理論界并沒有正式的理論作為確定影響生產率增長因素的依據,因此,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加上自己的思考來確定這些因素的。考慮到通過ML指數法測得的生產率指數有一個最低界限值0,數據出現截斷,在此情況下用一般的線性回歸方法可能會得到負的擬合值,從而影響分析結果。因此,這里采用擅長處理限值因變量的Tobit模型,來檢驗生產率增長和影響其因素的關系,模型如下。
MLPIit=C+β1ZBSHit+β2HYGMit+β3YFTRit+β4HJWRit+εit
式中:MLPI表示經由ML生產率指數法所測算的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指數(被解釋變量)。為了考慮環境管制,解釋變量包括資本深化(ZBSH)、行業規模(HYGM)、研發投入(YFTR)和環境污染(HJWR)。綜合已有文獻,各解釋變量說明以及各因素對生產率所可能產生的影響見表4、表5。
從分析表5中的Tobit回歸結果,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結論。
第一,資本深化對生產率的影響。資本深化對輕工業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且其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與張軍[28]、楊俊等[29]認為的過早的資本深化不利于生產率增長的研究結果相左。本文認為對于制造業輕工業行業來說,在其資本深化階段,企業通過加大投入,引入先進的生產技術,從而促進自身的技術進步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而本文同時得出,資本深化對重工業的影響不顯著,且具有負效應,這與我們的預期不一致。我們認為中國制造業的重工業行業大都屬于資本密集型產業,而該類產業傾向于重污染產業[30],隨著資本-勞動比的上升,其對環境效率的負面影響抵消了技術進步所引致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因此,中國一方面要繼續堅定不移地走產業轉型升級的道路,另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以降低中國在工業化進程中對環境的負面影響。
第二,行業規模對生產率的影響。行業規模的擴大對提高輕、重工業生產率水平的影響方向不同。研究結果顯示,行業規模對輕工業的影響具有不顯著的負效應,說明中國輕工業行業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規模不經濟的問題。與之相反,行業規模對重工業行業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且在10%水平上顯著。這一點與我們的預期相同,說明中國重工業行業規模的擴大有利于形成規模效益,進而在行業科技創新能力的提高和集約化使用投入要素等方面得到保證。
第三,研發投入對生產率的影響。結果顯示,研發投入的增加對我國輕、重工業的生產率均存在正向影響,雖然結果與我們的預期相同,但是其系數檢驗都不顯著。說明中國制造業行業研發投入的增加并沒有真正有效地促進技術進步,中國雖然是制造業大國,但制造業行業的增長嚴重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因此中國制造業需要進一步加強產學研合作,提高技術成果轉化率。
第四,環境污染對生產率的影響。與眾多研究結果以及本文的預期相同的是,環境污染不利于輕工業行業的生產率的提高,研究結果表明環境污染與輕工業生產率負相關,但系數檢驗不顯著。而與之相反的是,中國重工業行業的生產率水平隨著工業SO2排放量的增多而提高,這在一方面驗證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存著“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問題,另一方面也促使我們深刻認識到,如果不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把過高的資源消耗降下來,中國經濟雖然一時可以增長很快,但走不好,也走不遠。加快轉變增長方式,走科學發展之路,已成為我們內在的迫切要求。
五、結 論
在生產過程中,若不考慮環境管制問題,傳統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測度方法會使得生產率增長的測算出現偏差。本文運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產率指數對2001-2009年間中國制造業31個兩位數行業在環境約束下的全要素生產率指標及其分解進行了估算,并比較了不考慮環境因素影響情形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情況;其次運用Tobit模型研究了環境約束下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因素。綜合上述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結論。
第一,總體來看,考慮環境因素的中國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各項指標都呈現出增長趨勢,其中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4.49%,生產效率年均增長0.59%,年均技術進步率為3.83%。實證分析表明,對于產出增長率、全要素生產率和技術進步指數都不高甚至為負的行業大都是諸如造紙及紙制品業、紡織業等高能耗的勞動密集型的制造行業;而工業總產值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以及技術進步率較快的行業都是諸如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之類的高新技術行業,這表明了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在今后中國產業轉型升級中的重要性。
第二,相比較不考慮環境因素而言,在正確考慮環境管制的情形下,中國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會得到提高,而且對生產率的增長作出主要貢獻的還是技術進步而非生產效率的提高。
第三,表象上資本深化,行業規模擴大,研發投入增多,環境污染減少,會對我國制造業行業生產效率的提升起到很大的作用,但是本文的實證分析否定了這一觀點。通過將制造業進行輕、重工業的劃分,其Tobit回歸結果表明,資本深化對輕工業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而對重工業的影響不顯著,且具有負效應;行業規模對輕工業的影響具有不顯著的負效應,對重工業行業具有顯著的正向的促進作用;研發投入的增加對我國輕、重工業的生產率均存在正向影響;值得警惕的是,中國重工業行業的生產率水平仍然隨著工業SO2排放量的增多而提高,說明中國依然未能擺脫“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發展方式。
綜合來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已是現階段提高我國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必然要求。未來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應擺脫以加工貿易為主導的制造業的發展道路,著眼于提高技術轉化成果,通過提升自主研發能力促進生產率的增長。與此同時,政府在制定發展戰略目標時,應充分考慮到不同行業的差異屬性,以降低萬元GDP能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為出發點,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節能減排目標,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顏鵬飛,王 兵.技術效率、技術進步與生產率增長:基于DEA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2004(12):55-65.
[2] 方 虹,王紅霞.中國制造業技術變化實證研究[J].統計研究,2008(4):40-44.
[3] 葉振宇,葉素云.要素價格與中國制造業技術效率[J].中國工業經濟,2010(11):47-57.
[4] 鄭京海,胡鞍鋼.中國改革時期省際生產率增長變化的實證分析(1979-2001年)[J].經濟學(季刊),2005(1):264-296.
[5] 涂正革,肖 耿.中國工業增長模式的轉變——大中型企業勞動生產率的非參數生產前沿動態分析[J].管理世界,2006(10):57-81.
[6] 袁堂軍.中國企業全要素生產率水平研究[J].經濟研究,2009(6):52-64.
[7] 魏 楚,沈滿洪.工業績效、技術效率及其影響因素——基于2004年浙江省經濟普查數據的實證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8(7):18-30.
[8] 戴平生.我國省域工業全要素生產率變動及其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J].中國經濟問題,2009(3):54-59.
[9] 王麗麗,趙 勇.基于DEA的中國制造業效率評估[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1):32-39.
[10] 易 綱,樊 綱,李 巖.關于中國經濟增長與全要素生產率的理論思考[J].經濟研究,2003(8):13-20.
[11] 沈坤榮,趙 博.TFP、技術選擇與長三角地區的經濟增長[J].江蘇社會科學,2006(4):59-66.
[12] 陳 娟.全要素生產率對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實證研究[J].數理統計與管理,2009(3):277-286.
[13] Chung Y H,Fare R,Grosskopf S.Productivity and Undesirable Outputs:A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7(51):229-240.
[14] Fare R,Grosskopf S,Shawna,Pasurka,Garl. Accounting for Air Pollution Emissions in Measureing State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Growth[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2001(41):381-409.
[15] Yoruk B,Zaim O.Productivity Growth in OECD Countries:A Comparison with Malmquist Indices[J].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5(33):401-420.
[16] 王 兵,吳延瑞,顏鵬飛.環境管制與全要素生產率增長:APEC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2008(5):19-32.
[17] 田銀華,賀勝兵,胡石其.環境約束下地區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再估算:1998-2008[J].中國工業經濟,2011(1):47-57.
[18] 吳 軍.環境約束下中國地區工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及收斂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9(11):17-27.
[19] 陳詩一.中國的綠色工業革命:基于環境全要素生產率視角的解釋(1980-2008)[J].經濟研究,2010(11):21-58.
[20] 胡鞍鋼,鄭京海,高宇寧等.考慮環境因素的省級技術效率排名——1999-2005[J].經濟學季刊,2008(3):933-960.
[21] Abramowitz,Moses.Resource and Output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70[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6(5):5-23.
[22] Zhou P,Ang B W,Poh K L.A Survey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J].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2008(1):1-18.
[23] 吳延瑞.生產率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新的估計[J].經濟學(季刊), 2008(3):827-843.
[24] Kumar Surender.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Productivity Growth:A Global Analysis Using Malm-quist-Luenberger Index[J].Ecological Economics,2006(2): 280-293.
[25] Jeon Byung M,Robin C.Sickles.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Growth Accounting[J].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2004(5):567-591.
[26] 葉祥松,彭良燕.我國環境規制下的規制效率與全要素生產率研究:1999-2008[J].財貿經濟,2011(2):102-110.
[27] 王 昆.環境管制下廣東省工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實證分析[D].廣州:暨南大學,2011.
[28] 張 軍.資本形成、工業化與經濟增長:中國的轉軌特征[J].經濟研究,2002(6):3-13.
[29] 楊 俊,邵漢華.環境約束下的中國工業增長狀況研究——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的實證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9(9):64-78.
[30] 涂正革.環境、資源與工業增長的協調性[J].經濟研究,2008(2):93-104.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Its Determinants under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ased on Empirical Study of Transition Period
YUAN Tian-tian1,SHI Qi2,LIU Yu-fei1
(1.School of Industry Development,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03,Jiangsu,China;
2.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46,Jiangsu,China)
第7篇:輕工業的特點范文
關鍵詞:世界工廠重化學工業化制造業日本
一、日本世界工廠的形成
戰后的發展使日本工業經濟實現了騰飛。重化學工業發展迅速,在戰后初期調整之后,再一次成為日本工業經濟的主要部分;從出口情況看,70年代中期以后重化學工業產品在出口結構中已占九成以上,得到了國際市場的認可。
戰后日本工業發展經歷了恢復生產、重化學工業化和技術立國三個時期。
1.恢復生產(1945-1955年)
二戰對日本工業破壞嚴重,1946年工礦業生產水平只有30年代中期的31%,重化學工業急劇萎縮,經濟發展面臨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困難。為了迅速走出困境,日本政府通過"傾斜生產方式",優先發展了煤炭、鋼鐵、電力等原材料和基礎工業部門的生產。1947-1948年,煤炭產量每年增長30%以上,粗鋼產量每年增長80%以上,發電量也大幅增加。
1949年,日本在美國占領軍的指揮下推行"道奇計劃",大規模緊縮財政,導致了翌年嚴重的經濟蕭條,工業生產下降,庫存大量增加。然而朝鮮戰爭期間美軍大量訂購各種物資和勞務,使日本工業在"特需景氣"下迅速發展。結果,1953年日本整個工業比戰前增長了55%,其中鋼、船舶、水泥分別增長了46%、47%和54%,電力增長了1倍。1955年日本經濟全面恢復到了戰前最高水平,但當時輕工業在制造業中比重仍高達50%以上。
2.重化學工業化(1955-1974年)
1955年,日本確立了"以后發展要靠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以“重化學工業化”和“加工貿易立國”為主要戰略指導經濟發展。其后到1972年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也是日本“世界工廠”發展的關鍵時期,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長是由重化學工業的飛速發展實現的。重化學工業在工業生產中的比重不斷提高,1974年達到了62.2%,再次超過輕工業。1975年出口結構中排在前兩位的是機械機器和鋼鐵、金屬制品,在出口總額中的比重分別達53.8%和22.4%,這標志著日本工業產品質量得到了提高,在國際分工中地位大大改善。
這一時期日本重化學工業的發展可分為兩個階段:
1955-1964年,重化學工業以擴大國內市場為主得到了充分發展。這一階段日本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完成了對國內設備的初步改進,進而以“投資牽動投資”使重化學工業實現了重裝備化,各個部門的設備投資飛速增長。傳統骨干產業,如鋼鐵、石化、電力工業都采用了現代化生產方式,電氣機器工業、汽車工業的生產也逐步現代化,造船業和產業機械部門已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1965-1974年,優勢產業朝著大型化、國際化的方向發展。這一階段除設備投資對經濟增長仍維持著40%以上的貢獻度外,外貿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已經增加到23.7%,1975年進出口總額增加到337153億日元,是1965年59834億日元的5.6倍。曾推動內需的鋼鐵、汽車等行業,進行了大規模的合并改組。由于產品質量提高,日本許多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也得到了增強,各產業積極轉向出口,其中重化學工業產品的出口對象更傾向于歐美發達國家。
總體來說,這個時期的增長是通過持續大規模投資和降低成本實現的。雖然日本迅速實現了重化學工業化,但經濟過分依賴海外的能源和資源,并造成了嚴重的環境問題。
3.技術立國(1975-1990年)
70年生的兩次石油危機,使日本國內普遍認識到經濟發展嚴重依賴海外資源的脆弱性。與此同時,以微電子、新材料、新能源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迅速興起,也促使日本在新技術領域加強自主開發研究。為此,1980年日本政府明確提出了"技術立國"戰略,以推動產業結構向高附加值的知識密集型轉化。
在技術立國戰略的指導下,日本產業界的研究開發轉向了節約能源和"輕薄短小"的方向。鋼鐵工業進行高爐技術改造、電力工業大力開發核電設備,提高能源效率;加工組裝型產業取代了基礎原材料工業成為生產重點,汽車、家用電器、機床等產量在1975-1980年間分別增長了1.19、1.72、2.03倍。
另外,日本大力發展新興的電子技術,對被稱為新的"產業糧食"的半導體、集成電路工業尤為重視。兩大產業在這個時期經歷了由無到有的發展過程,產量迅速增加。1990年日本半導體元器件的產值為7100億日元,相當于1975年1588億日元的約4.5倍,而集成電路產值達到了29134億日元,為1975年1176億日元的24.8倍。
新興技術蓬勃發展,不僅使日本在新興行業方面取得了優勢地位,而且推動了電器機器、機械等傳統產業的生產革命。如電子設備部門通過集成電路化提高性能、縮小體積,從而開拓了新的市場,實現了大幅度增長。因此,盡管面臨發達國家出口限制和發展中國家緊緊追趕的嚴峻形勢,日本重化學工業依然擁有所向披靡的國際競爭能力。
二、日本世界工廠的特點
日本在80年代中期成為公認的世界工廠,但與英國、美國世界工廠不同的是,日本世界工廠的規模并沒有達到絕對控制地位,其地位主要表現為在重點行業、重點技術領域取得了領先于美國的競爭優勢。
除上文提到的幾個世界領先行業外,1965-1971年日本主要制成品產量增長占全球產量增長的比重依次為:鋼鐵占54%、造船占54%、汽車占46%、電子機械中的民用產品占90%。到80年代中期,日本工業總產值占世界的份額達到10%左右,出口產品以機電設備、汽車、家用電器、半導體等附加值較高的技術密集型產品為主,這些產品所代表的行業正是日本世界工廠的重點行業。所以日本世界工廠是在一定的制造業生產規模的基礎上,以重點行業、重點技術領域的領先和先進的總體科技水平為標志的。
三、重化學工業的發展是日本成為世界工廠的原因
“重化學工業”是日本人創造的詞匯,它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以鋼鐵工業和化學工業為主要內容的基礎原材料工業,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機械設備工業,主要包括造船、機械、電器設備、汽車工業。
重化學工業對日本經濟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重化學工業(特別是其中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業)實現大規模國產化之后,將使工業發展過程中對產業用機械的消費轉回國內,形成“投資促進投資”的效果,實現國民經濟的良性循環;其次,重化學工業具有的規模經濟效益,需要依靠龐大的消費市場才能得以實現,所以工業產品產量的增加在滿足國內市場之后,必然走向世界市場,而且由于規模效應,其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也是難以抵擋的。再次,重化學工業發展成熟促使日本產業結構高級化,高附加值產品在工業產品中的比重增加,出口結構也出現高附加值化,進而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得到提升,國際收支大大改善。最后,鑒于重化學工業的發展對生產要素的要求,日本非常注重引進和吸收先進技術、促進資本積累、培養高素質勞動力,使日本在各種生產要素上有一個質的提高,增強了日本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潛力。
所以說,日本正是由于在一定的工業基礎上成功地實施了重化學工業化戰略,提高產業結構,在工業生產、科技水平方面占據世界領先地位,才得以成為日本世界工廠。
四、日本世界工廠的啟示
中國加入WTO以后,日益成為各大跨國公司的投資熱土,據統計,世界500強中有400多家公司在中國投資,中國產品銷售到世界各地,各國主要媒體也紛紛撰文稱“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那么中國世界工廠能夠從日本成為世界工廠的歷程中得到怎樣的啟示呢?
首先,嚴格按照輕工業——基礎原材料工業———加工組裝業的順序發展,才是日本工業化成功的道路,前一產業是后一產業發展的基礎,這是產業結構提升不能違背的規律。
其次,日本能如此迅速的成為世界工廠,其奧秘就在于制定了明確的重化學工業化戰略,通過各種措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縮短國民經濟在輕工業、基礎原材料工業等低附加值產業的停留時間,促進高附加值的重化學工業的發展。值得注意的是,戰后初期,日本只有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但是日本并沒有囿于國際分工理論,著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而是以“立國”為目標,確定了重化學工業化戰略,促進本國經濟的強大。這是對中國世界工廠最大的啟示。
參考文獻
1.劉昌黎:《現代日本經濟概論》,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
2.日本經濟新聞社編著,大連市信息中心編譯《昭和經濟里程2—日本的產業》,東方出版社1992
3.張健王金林主編《日本兩次跨世紀的變革》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第8篇:輕工業的特點范文
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歷史大概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79年到1991年,這一階段是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起步階段,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和金額都較少。盡管這一時期外商直接投資逐年增加,但其在我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中所占比重較小,只有29.32%,因此,在這一階段外商直接投資還不是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第二階段從1992年到1998年,這一時期外商直接投資大幅度增加,并且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外商投資在我國實際利用外資金額中所占比重超過對外借款,為74.02%,最高年份達78.14%(1994年),此時外商直接投資已經取代對外借款,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和國際資本流入我國的主渠道。第三階段從1999年至今,這一時期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有較大幅度減緩,但外商投資金額保持在400億美元以上的規模。
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測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間,中國GDP年均9.7%的增長速度中,大約有2.7個百分點來自利用外資的貢獻。隨著我國2001年成為WTO正式成員,可以預見外商對我國的投資將會有較快增長,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及其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都將繼續提高,外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也將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的影響,是一個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問題。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分布特點及其成因
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必須先了解外商投資在我國三次產業之間的分布特征,為此,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其加以分析:
1.外商投資在三次產業之間的分布。目前,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部門),而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比重則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額)在三次產業之間的構成(單位:%)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外資統計年鑒》
2.產業內部結構。總體來看,外商在我國第一產業的投資規模一直不大,在整個外商投資中所占的份額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資的協議金額累計僅120億美元,而外商投資額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億美元;同時,第一產業的外商投資項目平均規模也較小。從第一產業內部外商直接投資的分布來看,主要是集中在農業,尤其是種植業,而對林業、牧業和漁業等部門的投資極少。在2001年1-6月第一產業的3.35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中,農業項目為2.22億美元,占66.26%。
在第二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工業部門,尤其是制造業,而建筑業所占的比重較小。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部協議投資中,工業比重最高的年份達到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建筑業的比重最高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平均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產業的163.12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工業部門的投資為160.59億美元,比重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對第三產業的協議投資額中,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比重為60.27%,90年代后上升到70%左右,盡管最近幾年這個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第三產業外商投資的絕大部分。綜上所述,外商對我國第一、二、三產業的投資主要集中于農業、工業(尤其是制造業)、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
3.工業內部外商直接投資的分布。外商對我國工業部門的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制造業,其中加工工業的比重很高,原料工業的比重不大;輕工業的比重較高,重工業的比重較低;同時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比重高于一般加工工業。
從最近幾年外商直接投資在工業內部的分布來看,制造業的投資比重很高,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投資比重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協議投資額中,制造業的平均比重為88.53%,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平均比重分別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實際投資中,制造業的比重為89.78%,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平均比重分別為1.87%和8.35%。在制造業內部,外商投資比重較高的是機電工業、化學原料及制品業。
4.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從外商在我國投資的地理分布來看,外商投資主要集中于廣東、江蘇、浙江、上海、山東、福建等沿海地區。從表3可以看出,在過去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相當少,無論是從協議金額來看,還是從實際投資來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比重不足整個投資的15%,而85%以上的投資集中在我國的東部沿海地區。近年來,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及一系列優惠措施的,西部地區對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加強;據不完全統計,世界500強中已有80余家企業在西部地區投資或設立辦事機構。
表2我國東中西部各地區外商投資情況(截至2000年底)(單位:億美元)
附圖
資料來源:《2001年中國外資統計年鑒》第3頁
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幾個特點,主要與下面三個方面的因素有關:
一是與廠商經營的目標相關。廠商經營的目標是實現利潤最大化。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占領我國巨大的消費品市場,這既與我國人口眾多的市場優勢相一致,也與外商經營目標相一致。
第一產業是我國重點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首選領域,但實際外商直接投資比重較低,至2000年底僅為1.78%。其原因在于農業開發投資大,回收期長,利潤率低,風險大,這與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標不符。但同時也說明了我國農業開發條件較差,對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們在如何改善農業投資環境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外商投資方向的選擇同時也與我國的投資政策和貿易政策相關。由于我國對消費品的進口限制較嚴,外商想要進入這一潛力巨大的市場,只有通過直接投資方式,而我國對重化學工業產品的進口限制較松,因此,對于我國的重化學工業品市場,外商主要通過貿易來占領。
二是與我國目前的投資環境相關。我國目前的投資環境是輕工業投資較容易,而重化學工業投資較困難。與重工業相比,輕工業所需投資較少,能耗低,對于交通運輸要求相對不嚴,選擇余地大;加之輕工業品投資能夠利用消費變化快的特點,投資者可以開發出更新、更適用、更美觀、更便宜的產品來吸引消費者從而獲得較高的利潤。所以,外商比較青睞于對輕工業的投資。而重化學工業能耗大,對交通運輸和相關產業發展的要求較高,而且投資額大,回收期長,因此,外商對該行業投資興趣不大。
三是與區域經濟投資環境相關。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條件較差,基礎產業薄弱,西部地區的整體投資環境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3][4]因此,盡管外商投資有向我國中西部擴展的趨勢,但這種趨勢進展相對緩慢,可以預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外商投資仍將主要集中在我國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
二、我國產業結構的現狀與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改革和開放以來,隨著市場機制調節作用的增強,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和影響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當前,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是結構問題而不是總量問題。認識我國的產業結構現狀,找出調整結構偏差的對策是當務之急。當前我國產業結構有以下特點:第一,GDP中第二產業比重偏高,服務業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國第二產業在GDP中所占份額為49.2%,高于標準結構的比例,服務業在GDP的份額為32.8%;與“標準結構”相比,明顯偏低。第二,在產業結構中,農業所占比重過高,服務業比重偏低。2000年,我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高達49.9%,顯著高于標準就業人口28.6%,偏差程度超乎尋常;第三產業比重偏低,就業比率為26.4%,而標準就業比率為30.7%。第三,城市化程度不高。2000年,城鎮人口在我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為30.4%,遠遠低于標準化水平53.0%,表明中國標準化水平遠遠落后于工業化過程。第四,輕重工業比重偏差嚴重。最近幾年,關于今后我國重工業應該得到較快發展,重工業在工業產出中的比重應有較大幅度上升的觀點比較流行,主要理由是中國工業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發展過于“輕型化”,中國目前的重工業比重較低,輕工業比重較高。
我國三次產業出現以上結構偏差,與外商對我國三次產業投資的結構性偏差有一定關系。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性傾斜加大了我國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改革開放以來,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部門,對第一產業的投資比重很低,對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實際投資中,第二產業的比重高達70.38%,其中工業的投資比重高達66.57%,而第一產業的比重僅1.42%,第三產業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底注冊登記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就外方注冊資本而言,第二產業的比重為64.08%,其中工業的占61.32%,而第一產業的比重僅為1.54%,第三產業的比重為34.4%。顯然,外商投資結構向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傾斜的特征很突出。
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現狀看,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產業結構偏差變得更為突出,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我國產業結構偏差的加深,與外商投資過多地向工業部門傾斜有一定關系,其主要表現為:
1.外資工業的結構傾斜助長了我國消費品工業的過度擴張。近幾年我國工業消費品相對過剩,生產能力大量閑置,除了城鄉消費需求趨緩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工業比重過高的條件下工業結構向輕工業傾斜。80年代中期以來消費品工業一直擴張,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資過度集中于消費品工業。據統計,截止到2000年底我國三資工業企業的外商直接投資額中,輕工業的比重占58%,重工業的投資比重占42%。
2.外資工業的結構傾斜加快了我國工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進程。外資工業高度集中于制造業,而在制造業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業。由于結構傾斜的存在,外資工業占我國以工業品為原料的加工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目前已接近1/3,占加工工業產品銷售收入的比重已達1/3,而占原料工業的兩個比重只有10%左右。這個特點使外資工業的迅速發展更多地推動我國加工工業的擴張,加快了我國工業結構高加工化的進程。
3.外商投資在第三產業的結構性偏差對第三產業的結構變動產生了明顯影響。目前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其次是批發和零售貿易、交通運輸和郵電通信業,而對其他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的投資比重很低,投資的結構性傾斜十分突出。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結構的高度傾斜,與我國第三產業內部對外開放度的差別有很大關系,除了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以及商業、交通運輸業和郵電通信業之外,其他的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目前的對外開放度仍較低。
隨著加入WTO之后我國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對外開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政策的調整,外商將較大幅度增加對目前投資比重很低的第三產業部門的直接投資;一些重要的服務業部門的外商投資比重在“十五”期間將明顯上升;相應地,外商對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投資比重會逐步下降。也就是說,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時間內,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直接投資的結構過度傾斜的狀況會明顯改變。
三、產業結構調整目標與外商投資的產業導向政策
產業結構是一個開放的系統,隨著經濟的市場化、全球化,產業結構的轉換和升級既有來自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也有來自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調整產業結構的目的不是簡單地等同于盲目追求一、二、三次產業產值(或勞動就業)比重主要地位的轉化,而是要面向國際產業的發展,在提升一、二次產業競爭力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真正提高產業素質。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證明,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的分布結構呈現規律性的演變趨勢。具體表現是:第一次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的相對比重在整個國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產業中就業的勞動力在全部就業的勞動力總數中的相對比重處于不斷下降趨勢;第二次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相對比重和勞動力就業比重逐漸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趨于下降;第三次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就業的相對比重上升,其中勞動力的相對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產業變動呈現的這種總的趨勢,是由各次產業的內在特征決定的。在工業現代化過程中,第一產業農業相對比重下降幅度最大,這是因為農產品需求的收入彈性低,人們對農產品的消費屬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費,當生活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對農產品的需求并不隨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這樣就使農業實現的國民收入份額趨于減少。第二產業工業相對比重上升,不僅因為隨著人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結構的變化使工業品需求的收入彈性處于有利地位,而且經濟發展中用于投資的增長也在不斷擴大工業品市場,從而整個國民收入中工業實現的國民收入相對比重上升。但隨著技術進步,工業有機構成提高會排斥自身的勞動力,而工業部門內各行業擴張的增殖又吸收勞動力,兩相抵消勞動力相對比重逐漸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趨向下降。第三產業服務部門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務”這種商品比農產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彈性,也由于第三產業門類繁多,許多行業具有勞動力和資金容易進入的特點,農業勞動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務業,因而第三產業各行業呈現廣泛而顯著的增長,使其在國民收入中的相對比重大大增加。
目前,我國三次產業結構偏差的主要表現是工業比重過高而第三產業比重太低,產業結構內部的主要問題是工業結構的升級緩慢,因此今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是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工業結構的升級。從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要求和目前外商投資的產業構成及其影響來看,我國政府部門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大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力度。
1.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力度,相對降低對工業的投資比重。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變動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下降,使得產業結構偏差變得更加突出。我國三次產業的結構水平同世界上其它國家相比,存在著較大差距。我國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僅高于同屬發展中國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同時我國的第三產業的比重也遠遠低于這些國家的水平。目前,國際直接投資中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比重較之20世紀80年代迅速上升,對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則相對下降。因此,我國應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力度,相對降低對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這不僅符合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需要,同時也符合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變化趨勢。
2.引導外商增加對重加工業的投資,相應地減少對消費品工業的投資。目前外商對我國工業的實際投資中,大概有60%分布在消費品工業,對重工業的投資只有40%左右。外資工業占我國消費品工業增加值、產品銷售收入以及固定資產凈值和流動資產的比重約為30%,而重工業的同樣比重只有15%。外資工業占以工業品為原料的消費品工業的增加值比重和產品銷售收入比重2000年為38.25%和41.28%,固定資產凈值比重和流動資產比重為34.52%和35.67%,而外資工業占重工業的前兩個比重為27.67%和28.96%,后兩個比重為24.35%和22.84%。但是,我國消費工業的產品相對過剩和生產能力閑置比重工業更加突出,“十五”期間工業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是適度重型化,加強重工業尤其是裝備工業,相應控制消費品的投資規模和增長速度。因此,需要引導外商對工業的投資更多地轉向重加工業尤其是裝備工業部門,相應地減少對消費品工業的投資比重。
3.引導外商增加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利用外資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引進外資來彌補國內資金缺口,促進技術管理等方面的進步,從而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國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資過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業,而一般加工工業中,有些是我國生產能力過剩和競爭激烈的產業,也是我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重復建設、引進的產業。外資的大量涌入,加劇了這些產業的過度競爭,造成對國內市場和國內企業的強烈沖擊,致使部分國有一般加工企業的處境十分困難。目前,外資工業雖然在機電工業中占有相當高的比重,對我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資企業同時在不少加工工業中也占有較高比重,這部分企業主要是來自港澳臺地區的中小企業。而90年代以來,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具有由資源、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的趨勢,因此應利用這一趨勢,進一步重視吸引大型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引導外資更多地進入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薪技術產業,同時減少對一般加工工業的投資比重。
4.引導外商投資增加對薄弱的第三產業投資,減少對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投資。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和社會服務業,導致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波動比較大,并對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產生不良影響。在我國經濟擴張時期,外商對房地產和社會服務的直接投資高度擴張,往往導致整個第三產業的外商投資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經濟相對緊縮時期,外商對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直接投資迅速收縮,導致第三產業的外商投資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產業中投資結構傾斜現象的存在,房地產和社會服務業的外商投資大幅度波動會直接造成整個第三產業的大幅度波動。顯然,只有當第三產業外商投資結構過度傾斜趨勢得到逐步改變后,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的周期性波動現象才會明顯減少,由此對整個外商直接投資以及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才會相應下降。
在第三產業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資比重較低的部門,如金融、保險、衛生體育、社會福利、科研和綜合技術服務業以及教育和文化藝術等,多數屬于層次較高的服務部門,我國要提高其發展水平,必須通過相應的外資產業結構導向政策,引導外資合理地向這些行業投資。[5]
5.引導外商加強對我國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推動我國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的進程。目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但中西部地區還未建立起一個完善的以優勢產業為支柱的產業結構體系,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都相對薄弱,與東部沿海地區存在很大差異,這勢必會嚴重阻礙我國整體產業升級的進程。因此,我國政府應加大對外資地區流向的引導,以便有更多的外資投入西部地區的經濟建設中,從而加強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使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之間建立一種協調的產業關聯機制,促進我國的產業升級。
【參考文獻】
[1]胡新文.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資的新動向及我國的應對策略調整[J].世界經濟研究,2002,(1):19-22.
[2]張德修.入世后的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結構變化趨勢探析[J].經濟科學,2001,(6):81-87.
[3]顧建清.外商直接投資對江蘇產業結構的影響[J].中外科技信息,2002,(5):26-28.
第9篇:輕工業的特點范文
一、因開埠而新生的東北貿易中心
(一)連接太平洋和東北內陸的樞紐———營口
營口原為遼河口外的一處沙島,直到19世紀20至30年代才與陸地相連,并延伸至營口之處。[1]228根據中英《》第11款所規定,清政府開放“牛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等府城口”[2]作為對外通商口岸。1861年,英國人經實地考察后,發現牛莊一帶泥沙淤塞嚴重,于是將實際通商口岸改設在營口。這樣,營口就成為東北第一處對外通商口岸。營口地理位置優越,“臨冥北構而東折,南走辰韓,百川朝宗”[3],將太平洋和東北內陸連接在一起。營口位于遼河的出海口,船舶沿河而上可溯至鄭家屯,全部航程為1312.5km。再加上其支流渾河、太子河等,航程更有所增加。營口開埠,極大地推動了東北內陸經濟的發展。光緒后期,運載著大豆、糧食、煙草等經濟農作物的船只總量已經發展到2萬余艘。日本史地學家小越平隆在東北旅行時,看到遼河中船只之多,不禁感慨:“而往來河上者,尚艨艟如卿,大有掩江之勢。”[4]清末的30年間,遼河的航運業日益發達,儼然形成了以營口為出海口,以遼河航運為紐帶的東北市場流通結構。而在這種互動結構中,營口港也確立了在東北區域不可忽視的核心地位。
(二)以大豆三品出口為代表的進出口貿易
優越的地理位置僅僅為營口提供了發展的可能,而真正使其崛起的是開埠后涌現的貿易機會,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大豆三品(大豆、豆餅、豆油)的外銷。遼河流域歷來盛產大豆,且品質優良。1863年,清政府為改變日益嚴重的貿易逆差,決定“各海口豆石開禁,準令外國商船運售”[5]。于是,大豆三品成為商人販運牟利的首選貨物。據當時官方記載,駛達營口的外籍貨船,從1862年的86艘快速增至1864年的274艘,其中約90%的商船租給中國商人,進行以大豆為主的經濟作物的轉口貿易。[6]1872年至1894年,經營口輸出的大豆三品輸出額累計達到8338萬海關兩,占此間東北輸出總額的76.9%。[7]之前,尤其是開埠初期,大豆三品一直占營口港出口貿易的半數以上,而營口港又幾乎壟斷了東北地區大豆三品的外銷,并且數量巨大,這為營口港出口貿易的穩定增長奠定了基礎。隨著營口港的發展,對外出口產品也日益多樣化,柞蠶絲、雜糧、燒酒、中藥材、人參、鹿茸、皮革、鬃毛等商品的出口量逐年增長。同時,進口產品中最初占有絕對比例的鴉片,也逐漸被棉織品、毛織品、金屬制品、煤油、火柴等民用產品所替代。到1903年,營口港的進出口貿易額相比1893年增長2.7倍,與開埠初期1864年相比則增長19.7倍,[8]遙遙領先于東北其他對外貿易口岸。到1907年,營口港的輸出額已達到1800萬兩,是大連、安東兩港總和的3倍。[9]在營口開港的最初40年,其進出口貿易額不但穩居東北地區第一位,而且在全國范圍內也逐步躍升至第六位。進出口貿易的繁榮為營口城市的初期發展帶來了大量的資金,也為后期其他行業的開創積聚了資本。
二、因商貿業而催生的東北金融中心
(一)從事批發的“大屋子”興起
開埠之前,營口還是“地方狉榛,幾同草昧,百度未開,胥待治理”[1]109的海邊小村落。開埠后,隨著進出口貿易的繁榮,營口在東北貿易體系的關鍵地位日益突出,吸引了大批外來資本。先是附近原牛莊、田莊臺和蓋平商業資本的移入,后來又吸引了全國各沿海省份及山西資本投資,并且英、美、俄、德、法、荷蘭、挪威、瑞典和日本的商人也紛至沓來。營口的商業都與進出口貿易產品種類相關聯。例如,光緒元年(1875年)經營棉布和砂糖的商店只有東永茂1家,到宣統三年(1911年)增加到33家,經營大豆出口的糧棧共71家。[10]98這些寄生于進出口貿易的商店(號)又稱“大屋子”,其可分為三種類型:一是批發商,二是商,三是委托商。“大屋子”是營口港冬季封港,中外海上貿易暫時中斷,中間商通過資本運作買賣雙方批發買賣貨物并提供倉儲、服務的特殊行業。營口的“大屋子”種類繁多,有雜貨布行、南貨客棧、洋貨鋪、山貨鋪等,其經營大豆三品、柞蠶絲、棉毛織品、中藥材、糧食等數十種進出口產品。“大屋子”的興盛迅速帶動了營口當地商業的發展,經營各類商品的商戶成批涌現。據營口商務總會統計,1910年僅營口外城商戶就有601家,發展到1931年,商戶數量已增加到2588家。[11]179,370宣統元年(1909年),蓋州優貢沈羹唐赴京參加朝試時路過營口,對其繁華頗為感慨,于是寫詩云:“竹馬繁華地,狂游向夕曛;笙聲千戶月,帆影四圍云;世亂俗偏靡,言龐夷不分;可憐猶漢土,極目帳胡氛。”[11]146
(二)商貿業的興起促進爐銀業的興盛
爐銀的出現幾乎與營口開埠是同步的。當時,中國還沒有統一的貨幣,雖然都以元寶銀為貨幣,但是各地元寶銀成色、重量不同,換算復雜,嚴重地阻礙了全國商品經濟的大循環。隨著商貿業的發展,營口也像其他商貿城市一樣,出現了銀爐行當———即將不同規格的白銀貨幣鑄成統一規格的元寶銀(元寶銀俗稱“營寶”,后更名為“爐銀”)。“每屆秋冬,三省農產上市,資金內轉,凡南省或外國之來三省采運特產者,所攜他省通幣,勢必先匯做爐銀,再由爐銀買做當地之鈔票。”[12]這樣,爐銀很快就成了東北地區與外界貿易的實際貨幣。1875年以后,營口港同世界五大洲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貿易往來,其吞吐量以每年平均16%的速度在增長。[10]100隨著貿易范圍的擴大,商品種類的增多,“大屋子”的出現,交易的資金額變大,原有的現寶爐銀漸漸不能滿足商品經濟的需要。1880年,經當地裕盛祥銀爐執事李潤齋提議,創設“過爐銀”。“過爐銀”,即商人將現銀存放在銀爐暫不使用,使用時持票據去提取,買方也可以不使用現銀,僅僅更改票據持有人即可完成交易。這樣,銀爐就起到了銀行轉賬的作用,大宗交易也避免了過去車載船裝的現銀支付。此后,營口爐銀業又創定了“三、六、九、臘4個卯期”,銀爐到卯期無現銀實現交割,只需“加色”。①“加色”即為利息,顯然這時的銀爐起到了銀行的信貸作用。營口通過爐銀業建立了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地方金融制度,并得到確立和完善,逐步內生成一種獨立于行政權力之外的民間金融系統。營口爐銀體系建立后,不但一度壟斷東北的貨幣信貸業務,而且進一步吸引了國內外金融資本的入駐。從1898年起,華俄道勝銀行、正金銀行、大清中央銀行、正隆銀行、朝鮮銀行、交通銀行、邊業銀行等先后在營口開設支行,與當地的爐銀錢莊進行金融匯兌業務,并將營口的資本信貸規模推向頂峰,使這一時期的營口成為東北地區當之無愧的金融中心。隨著中東鐵路、中長鐵路的貫通,大連、哈爾濱等地進出口貿易迅速發展,致使營口逐步喪失了東北貿易的霸主地位,但這并未影響到營口貿易額的持續增長。例如,“1907年營口港的年貿易額3275.9萬海關兩”,“1931年的年貿易額12397萬海關兩”。[13]在大連開港24年間,營口港的貿易額不僅沒有減緩,相反增長了4倍多,歸其原因,還是因為“爐銀具有合資互助之精神,運用自由之便利”②。
三、因對抗殖民經濟而蓬生的遼南輕工業中心
(一)傳統輕工業的經久不衰
營口開埠后,隨著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營口的手工業開始脫離傳統的家庭作坊模式,并在原有家庭手工業的基礎上,萌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了近代工業萌芽。其中,以紡織、榨油兩個行業出現最早,而且經久不衰。開埠早期,東北的大豆出口額長期位列第一。中國商人為了開拓外國市場而造成的大豆的商品化,必然帶來榨油工業的盛大,而營口作為大豆出口的最主要港口,自然成為榨油工業的發源地。營口在1866年就已經有兩個油房,到1896年,營口油房達30余家。[14]85但這些油房采用的是人力畜力的楔式榨油,所以規模不大。1899年至1901年,營口的怡興源、怡東生、東永茂等3家油房先后采用機器的生產方式,[14]86榨油業從而步入了現代輕工業的范疇。到1929年,楔式榨油的方法在營口已經完全絕跡,新式油房業工廠有23家,共有水壓式榨油機292部,螺旋式榨油機354部,合計646部,日產豆餅32486片、豆油133150斤(66575kg),有工人876名。[11]3451931年,營口的油房業工廠年產豆油1654.62萬斤(8273100kg)、豆餅330.924萬片,生產總額為661.848萬元,占整個營口工業及小工業的比例高達63.02%,①是當之無愧的支柱產業。在近代東北進口產品中,紡織品長期占據第一的位置,而且英國、美國、日本紡織品先后壟斷過東北市場。營口民族資本家“為杜漏卮,而挽利權”,在一戰期間,將資本轉向棉絲業。1913年8月,營口首家恒祥永織布廠宣告成立。到1927年,有織布廠87家,織機1200架(內有使用電力者24家,織機500余架),年產60萬匹棉布。此外,還有織帶廠40家,織帶機230架,年產織帶9萬打;毛巾廠11家,機械約100架,年產毛巾1.35萬打;織襪廠75家,織機200余架。②此時,營口已經是僅次于奉天、哈爾濱的東北棉紡織業城市。
(二)新興輕工業的迅速發展
營口作為港口城市,最早開發的工業種類往往與貿易品種息息相關,但隨著近代工業思想的浸染,與本地資源相關的新興工業漸漸得到民族資本的青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打亂了原有的世界經濟秩序,也為營口民族資本開創民族產業帶來了機會,其中以火柴為代表的新興工業迅速發展。早在1909年,營口就成立了海來公司,專營生產牡蠣粉。此粉可以使火柴按擦時延緩燃燒,是制造火柴盒的必備原料。③此外,營口附近的海城、大石橋、蓋州是東北地區重要的磷礦、螢石礦產地,而這些都是火柴生產的必備原料。1913年,王灝、郭渭在營口青堆子創辦“營口關東火柴股份有限公司”,這是東三省民族資本最早創辦的火柴廠,其開創了東北民族火柴工業之先河。之后,在營口青堆子又先后開辦了三明、甡甡和志源火柴廠。營口火柴工業憑借緊靠原料產地的成本優勢,不久就在民族火柴工業中脫穎而出,而后又擊敗了東北地區的日本火柴工業,并阻止了瑞典火柴工業在東北的擴張。1927年,甡甡、三明、關東三家火柴廠年產火柴約16萬箱,并專門銷往南滿站沿線及錦州、洮南、熱河一帶。④營口火柴業在同外國資本競爭的過程中,“有了較大的發展,從生產能力說,滿洲是最早達到完全不需要進口的地區”⑤。營口及附近的蓋平、海城、熊岳、復州一帶蘊藏著豐富的硅石、螢石、硼礦、滑石、凌美礦等非金屬礦藏。其中,硅石、螢石、硼礦是重要的玻璃生產原料。隨著民族資本對現代化工技術的逐步掌握,玻璃工業在營口開始萌發。1929年,營口民族玻璃工業有東明、聚興、利順三家公司,生產玻璃瓶、燈罩、燈壺、化妝品瓶、藥瓶等制品,并銷往洮南、鄭家屯、通遼、哈爾濱等地。⑥除此之外,民族資本還涉及鹵鹽、窯造、染色、印刷、制藥、制鞋、食品加工、水產加工等輕工領域。與此同時,鍛冶、薄鐵、配件、造船等重工業也開始萌芽。“九一八”前,營口已經成為南滿地區重要的輕工業中心。營口開埠后,東北成為中國資本與殖民資本競爭的舞臺,而在競爭的過程中,沒有工業基礎的中國資本逐步喪失了對東北的經濟統治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東北人的衣食住行所涉及的工業產品幾乎都是外國商品,而自己生產的農產品除口糧外又幾乎都出口到外國作為工業原料。20世紀初,東北形成了“日本—滿洲、俄國—滿洲的殖民地統治關系”⑦。歸其原因,主要是中國沒有建立起自己的產業資本。而營口經濟在東北貿易金融中心地位喪失后,主動轉型,通過爐銀資本發展制造業,夯實了經濟基礎,又以制造業為依托,反過來帶動貿易、商業的繼續繁榮。營口輕工業的蓬勃發展,動搖了日本殖民經濟在南滿的統治基礎。1931年,日本甚至把自身的金本位體系“除已將南滿路營口支線運費改用銀本位外,并擬在南滿全線施行銀本位制”[15]537。
四、因日本殖民統治而衍生的特定物資供給中心
(一)扼殺民族工商業
“九一八”后,日本僅用4個月就占領了東北全境,但營口沒有遭受戰爭的破壞。1933年,營口主要工業及小工業生產總額達13877957.7元,比1931年增長32.14%。①一個強大且不斷發展的營口民族工商業的存在,是日本殖民者所不希望看到的。早在1932年7月,日本就將營口的東三省官銀號支號、邊業銀行支行、中國銀行支行、交通銀行支行強制整合為中央銀行支行,企圖掌控營口的金融業。但是,營口的爐銀業很發達,并在民間持有大量的民族資本,早已形成獨立于銀行體系外的民間借貸關系。1933年,美國為了使白銀與貨幣脫離,大量購買白銀,迫使其急速升值,導致白銀的商品價值遠遠大于其貨幣價值。同年11月3日,財政部命令:“從即日起,營口所有銀爐停止營業,嚴禁爐銀的鑄造流通。凡依靠‘過爐銀’而存在的債權債務關系,按爐銀5兩兌換滿幣一元的標準價格兌換。”[11]4991932年,日本銀行則以低于每盎司白銀25美分的價格收購,轉手即以每盎司白銀65美分倒賣到海外。在利益驅使下,曾經在營口工商業發揮過重大作用的爐銀業迅速消亡。至此,營口的民族工業在缺少民族資本的支持下,也走向敗落。強制收購爐銀事件的發生,使營口民族資本和日本殖民資本此消彼長。1934年6月,日偽頒布所謂的“產業統治聲明”,對重要經濟事業實行完全統治或半統治,主要工業則只允許政府或“特殊會社”辦廠。在資本和政策的雙重刺激下,日資開始大量強制收購營口民族工商業。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朝鮮紡織株式會社“得到關東軍特務部的允許,向營口紡紗廠投資一百萬元”②,將其吞并改為營口紡紗株式會社。1934年,營口日本工商業資本在5000元以上者7家,1萬元以上者32家,5萬元以上者7家,10萬元以上者7家,50萬元以上者1家,100萬元以上者2家,200萬元以上者9家,1億元者2家。[14]283而此時民族工商業者由于缺少資本和政策支持,經營規模普遍不大。1939年“滿鐵”調查部對吉林、營口、錦州3個城市的中國人經營的最有實力的225家工業、商業、運輸業、金融業進行調查,發現資本在“5萬元以下企業194家,5萬元以上企業10家,10萬元以上企業21家”[14]519。1935年以后,日偽又陸續推行對各種物資的配售統治。到1942年,幾乎所有產業的原料、生產、銷售環節都被日資把持,營口興盛一時的民族工商業幾乎絕跡于市。
(二)掠奪營口資源
日本在排擠民族工商業、實行經濟壟斷的同時,也加快了對營口資源的掠奪,并將其打造成特定物資供應的供給中心。隨著戰爭的不斷擴大,資源貧瘠的日本越來越倚重營口的非金屬礦產、輕金屬礦產、紡織品、紙漿、精鹽等軍用和民用物資。日本殖民者為了掠奪更多的資源,將相關領域技術和巨額資本引入到營口,強迫推動“一業一社主義”(一種業務由一個會社壟斷經營),造成相應工業的畸形發展。“九一八”之前,日本就想將營口及其附近的非金屬和輕金屬礦產據為己有,但因其一直由奉系官僚資本把持而無從下手。1937年后,南滿礦業開發會社陸續強制收購西大嶺采礦所、窨子峪采礦所、李家屯采礦所、沙崗臺螢石礦、臥龍螢石礦場等礦區,并由日資建立了滿洲鎂金屬工業株式會社、滿洲滑石株式會社和南滿制鐵柱式會社,壟斷了經營營口地區的非金屬及輕金屬采掘加工業。1940年,滿洲鎂金屬工業株式會社生產鎂礦700噸(t)。①1943年,滿洲滑石株式會社生產滑石礦產15057噸(t),占總產量的86.4%。1944年,南滿礦業會社燒煉菱苦土年產量達26376噸(t);滿洲制鐵會社生產螢石礦8472噸(t),占總產量的38.9%。②在其他領域,日資也不斷加強壟斷。營口紡織株式會社成立后,到1942年已繳納的全部資本金達1000萬元,其事業已經涵蓋紡織棉紗、棉布、染色、纖維生產等領域。1939年,營口紡織達到其產量峰值,生產棉紗42870件,棉布1139435匹。③后來,營口紡織將其紡紗廠轉向,專為日本軍隊紡織軍用布匹,走上了戰爭工業軌道。1936年,日商看中渤海沿岸地區的蘆葦資源,企圖用葦漿制造人造絲,后因成本過高改作造紙廠,并在營口成立了康德葦紙漿股份有限公司。1942年,該公司改名為鐘淵公大實業株式會社,資本總額達2057.5萬元。1943年,其峰值年產白紙漿7283噸(t),白板紙及手紙4427噸(t)。④營口鹽場歷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漢魏,并且一直是東北地區最主要的海鹽生產基地。“九一八”前,營口海鹽可達到年產量17.7萬噸(t)。1937年,日本殖民者為了更多地掠奪營口海鹽,將鹽改為專賣,由民制官銷。1940年,日商成立營蓋鹽業會社,將民灘強歸公有后并入滿洲鹽業株式會社。1943年,營口原鹽年產量達657728噸(t),占當年原鹽總產量的74.36%;精鹽產量19318噸(t),占精鹽總產量的100%。⑤“九一八”后,日本殖民統治下的營口經濟雖然繁榮并有所增長,但是,這種增長是建立在搜刮民族資本,打壓民族工商業,掠奪中國資源,為日本軍事侵略服務的基礎上。1944年后,隨著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節節敗退,營口的日本殖民經濟迅速敗亡,物價飛漲,民不聊生,營口港幾乎處于停滯狀態,除運輸少量軍用物資外,幾乎閉港。
五、小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