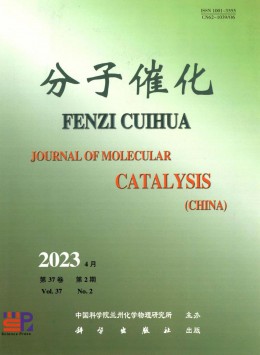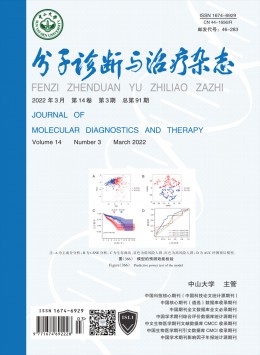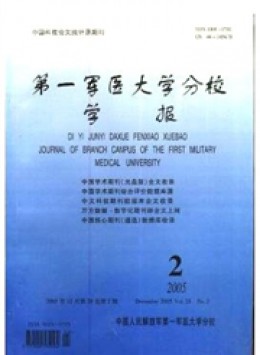分子遺傳學研究方法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分子遺傳學研究方法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分子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 行為遺傳學;數量遺傳學;分子遺傳學:基因:人格
分類號 B845
1 引言
人格是一個人獨特精神面貌的整體反映,是需要、動機、興趣、態度、價值觀、氣質、性格、能力等多個方面的整合。它的形成和發展與遺傳因素息息相關。然而,人格的遺傳性究竟如何?到底哪些基因在起作用?它們又是如何起作用的?針對諸如此類的問題,行為遺傳學家們試圖為我們提供有效的解答,并由此形成了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即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
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就是運用行為遺傳學理論和方法來考察和揭示人格特征(包括人格障礙)和人格差異的遺傳基礎問題。它強調遺傳基因是塑造人格核心特征和造成人格個別差異的主要因素,但并不忽視環境的作用,甚至主張人格特征與人格差異是多種基因、多種環境以及基因與環境動態交互作用的結果。早在19世紀中后期,英國心理學家高爾頓(Galton,F.)就首先利用家譜法和雙生子法研究了人格差異的遺傳基礎。盡管他的研究因未將遺傳和環境區分開來而具有諸多局限,但它“為人類行為的變異范圍提供了檔案證明并且說明了行為變異存在遺傳基礎”(Plomin,DeFries,McClearn,& McGuffin,2008),是運用行為遺傳學方法研究人格差異的先驅性嘗試。高爾頓之后的20世紀,人格的行為遺傳學研究因行為主義主流范式的盛行而長期遭到“冷遇”。前者強調人格的遺傳性,而后者堅持環境論并認為人格由社會化的習慣決定,兩者的矛盾在這種勢力不均的情勢下曾一度不可調和。
但近幾十年來,行為主義的逐漸衰落和現代生物學特別是分子生物學的飛速發展分別為人格的行為遺傳學研究提供了巨大發展空間和發展動力,并使它由傳統的數量遺傳學取向發展到分子遺傳學取向。分子遺傳學取向是發端于20世紀初而到20世紀末才應用于人格研究的一種新取向,它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上都較數量遺傳學取向具有革命性突破,目前正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著。可以說,人格遺傳學研究進入到分子遺傳學時代(Johnson,Penke,& Spinath,2011)。不過,兩種研究取向在基本思路方面各有特色,在具體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有價值的成果,積極推動了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的復興和發展。
2 數量遺傳學取向
人格的數量遺傳學(quantitative genetics)研究取向主張運用雙生子研究、收養研究等設計來估計群體中遺傳因素對人格表現型方差的貢獻率,旨在用數量化的手段從宏觀上估計某種人格變異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遺傳效應引起的,并考察遺傳通過與環境交互作用或相關影響人格的方式以及這些效應發生的具體情境。
2.1 人格遺傳率
數量遺傳學衡量人格遺傳性大小的核心指標是遺傳率(heritability),即在某群體內觀測到的人格總變異中能被遺傳變異解釋的百分比,它既可以揭示遺傳是否影響某種人格特征又可以指明這種影響達到何種程度。人格遺傳率可以用公式h2=Vg/Vp(其中h2代表人格遺傳率,Vg代表遺傳導致的人格變異,V。代表觀測到的人格總變異)來表示,數值在0~1之間,越接近于0,說明變異越少源于遺傳;越接近于1,說明變異越多源于遺傳。需要指出的是,遺傳率估計具有如下三個特點:第一,它具有群體特異性,僅僅適用于解釋樣本或群體的人格差異,而不適用于描述個體人格的遺傳性;第二,它假定遺傳因子和環境因子之間不存在相關或交互作用;第三,它會因測量方法和計算方法不同而有細微差別(郭永玉,2005;Larsen & Buss,2009)。
2.2 數量遺傳學設計
為了把基因和環境對人格差異的貢獻分離開來,數量遺傳學家采用了家族研究、雙生子研究和收養研究等多種研究設計。家族研究是最早用于人格研究的行為遺傳學方法,但它不能將遺傳與共同環境的作用區分開來,因而不能得出準確的遺傳率;雙生子研究是現代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最常用的一種有效方法,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家族研究的缺陷,但它的等環境假設和代表性也往往令人擔憂:收養研究作為一種強有力的自然實驗法,是“解開影響家族相似性的遺傳和環境源之結的最直接方法”,避免了雙生子研究中的等環境假設問題,提供了環境影響人格差異的最佳證據,但它也存在三個爭議,即代表性、生前環境影響和選擇性安置效應(Plomin et al.,2008)。
鑒于以上三種方法各有其長處和不足,在過去的20多年中,數量遺傳學家已經開始利用家族研究、雙生子研究和收養研究的組合設計來研究人格。例如,研究分開撫養的同卵雙生子就把雙生子研究和收養研究各自的優點進行了有效整合,并且分開撫養的同卵雙生子在某種人格特質上的相關系數可以直接解釋為遺傳率的一個指標(Larsen & Buss,2009)。另外,隨著離異和再婚現象增多而產生的繼親家庭研究,自然地綜合了家族研究與收養研究的優勢,也是一種有趣和有效的組合研究設計。對多組比較的組合設計,甚至簡單的收養和雙生子研究,現代行為遺傳學通常采用模型擬合(model fitting)的方法進行統計分析,即建立一個反映各種遺傳和環境因素對某種人格特質貢獻大小的結構方程模型,并將其與觀測到的相關進行比較,從而估計出遺傳和環境的影響程度(郭永玉,2005)。
2.3 具體研究與發現
數量遺傳學取向的人格研究者利用上述設計主要對人格特質、人格障礙以及態度與偏好的遺傳性問題進行了考察。
2.3.1 人格特質
數量遺傳學關于人格特質的研究主要涉及人格的五大特征,即外傾性、宜人性、責任心、神經質和經驗開放性,其中研究最充分的要數外傾性和神經質。多數數量遺傳學研究表明,“大五”人格模型中的所有因素都具有中等大小的遺傳率,并且此研究結果在不同年齡段、不同性別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樣本群體中具有普遍一致性(saudino,1997;Loehlin,McCrae,Costa,& John,1998)。例如,兩項以雙生子為被試的研究表明,神經質和外傾性的遺傳率估計值分別為43%和52-54%(Wray,Birley,Sullivan,Visscher,& Martin,2007;Rettew,Rebollo-Mesa,Hudziak,Willemsen,& Boomsma,2008)。以往數量遺傳學對“大五”人格的研究通常都以正常人群為被試,最近許多研究開始關注異常人群“大五”人格的遺傳性問題。例如,Kendler,Myers和Reichborn-Kjennerud(2011)的研究表明,邊緣型人格障礙與“大五”人格中的神經質維度存在顯著的遺傳正相關,而與宜人性和責任心維度存在顯著的遺傳負相關。Hare等人(2012)的研究表明,躁郁癥患者人群“大五”人格的遺傳率(23%~32%)某種程度上低于正常人群的研究結果(40%~60%)。我們固然可以推測是異常人格影響了“大五”人格遺傳率的變化,但要得出確切的因果結論還需依賴未來數量遺傳學和分子遺傳學更加細致的綜合研究。
除“大五”人格外,研究者還對活動水平(activity level)和“精神病”人格特質的個別差異進行了行為遺傳學分析。活動水平是氣質的一個組成元素,其個別差異出現于生命早期,并隨著時間推移在兒童身上表現出穩定性。Spinath,Wolf,Angleitner,Borkenau和Riemann(2002)對300對雙生子的研究表明,活動水平存在40%的遺傳率。“精神病”人格特質包括權術主義、鐵石心腸、沖動性不一致、無所畏懼、責備外化和壓力免疫等方面。Blonigen,Carlson,Krueger和Patrick(2003)對353名男性雙生子進行了研究,發現所有這些“精神病”人格特質都表現出中等或高等的遺傳率。
數量遺傳學研究發現,盡管不同研究設計所得出的具體數值會有所不同,但一般的人格特質都具有較高的遺傳率估計值(Krueger & Johnson,2008)。
2.3.2 人格障礙
數量遺傳學系統研究的人格障礙主要有精神分裂型人格障礙、強迫型人格障礙和邊緣型人格障礙。精神分裂型人格障礙具有輕微精神分裂樣癥狀,用個人訪談法和問卷法所做研究表明,它具有非常高的遺傳率(Kendler,Myers,Torgersen,Neale,& Reichbom-Kjennerud,2007)。強迫型人格障礙是一種神經精神病狀態,以思想、情感、觀念以及行為的反復為典型癥狀,它所包含的五個因素即禁忌、污馳/清潔、疑慮、迷信/儀式和對稱/囤積的遺傳率位于24%和44%之間(Katerberg etal.,2010)。上述兩種人格障礙可能是精神機能障礙遺傳連續體的一部分,因為它們分別與精神分裂癥和強迫焦慮癥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遺傳重疊(Plomin et al.,2008)。邊緣型人格障礙是一種以心境反復無常、自我認同感紊亂、情緒沖動以及行為不穩定等為主要表現的人格障礙,它很大程度上受遺傳基因影響。例如,對荷蘭、比利時和澳大利亞三個國家5000多名雙生子的數量遺傳學研究表明,加性遺傳效應(additive genetic effect)可以解釋42%的邊緣型人格障礙變異,而且這一結果具有跨性別和跨國別的一致性(Distel et al.,2008)。最近一項10年的雙生子縱向研究發現,邊緣型人格障礙特質在14~24歲的各個年齡段都具有中等的遺傳率,且遺傳率有隨年齡增長而輕微上升的趨勢,而這些特質的穩定性和變化受遺傳因素高度影響,一定程度上也受非共享環境的影響(Bornovalova,Hicks,Iacono,& McGue,2009)。
2.3.3 態度與偏好
穩定的態度和偏好通常被看作人格的一部分,并表現出廣泛的個體差異。數量遺傳學家對態度和偏好的遺傳性進行了饒有趣味的考察。綜觀多數研究可知,態度的核心特征傳統主義具有中等的遺傳率。例如,一項明尼蘇達的雙生子研究表明,傳統主義的遺傳率為63%;一項對654名收養和非收養兒童的縱向研究表明,遺傳對保守態度具有重要影響,并且顯著的遺傳影響早在12歲時就已產生(Larsen & Buss,2009)。然而,并不是所有態度和信仰都表現出中等水平的遺傳率,這要因所研究的態度類型而異。例如,一項對400對雙生子的研究表明,對上帝的信仰、對宗教事務的參與以及對種族一體化的態度的遺傳率為零(Larsen&Buss,2009)。基因似乎也影響職業興趣或偏好。一項用修訂版的杰克遜職業興趣量表(JVIS)做的研究表明,34種職業興趣中有30種的遺傳率在37%和61%之間(schermer & Vernon,2008)。這表明,我們絞盡腦汁作出的職業選擇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們從父母那里繼承的基因的影響。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為什么有些態度和興趣具有較高的遺傳性,而有些態度和信仰的遺傳性不明顯甚至為零?或許未來的行為遺傳學研究能夠給出答案。
3 分子遺傳學取向
人格的分子遺傳學(molecular genetics)研究取向主張在DNA水平上用基因測定方法研究特定基因對人格表現型的影響效應,旨在超越傳統人格數量遺傳學研究僅停留在統計學層面考察遺傳率的局限,而從微觀層面直接鑒別對人格產生重要遺傳影響的具體基因或基因組合,以精確揭示人格特征(包括人格障礙)或人格差異的根本遺傳機制。
3.1 人格候選基因
已知人類基因具有數萬種之多,要想從中找出對人格起作用的特定基因是件困難的事情。況且,復雜的人格或行為特質并不簡單地遵循孟德爾的單基因遺傳定律,而是同時受作用幅度不完全相同而又相互協同和相互作用的多個基因的影響,這就又大大增加了確定這些基因的難度。因此,研究者不可能對所有基因都進行考察,更多的是考察候選基因與人格的關系。人格候選基因(candidate gene)是被假定與某一人格特質有關的基因,通常人們已了解其生物學功能和序列,它們可能是結構基因、調節基因或在生化代謝途徑中影響性狀表達的基因。研究者一般通過了解相關生理機制來確定人格的候選基因。例如,用于治療活動過度的藥物常含有多巴胺,因而像多巴胺受體、多巴胺啟動子和多巴胺轉運體這樣與多巴胺有關的基因便成為候選基因研究的目標。我們通常缺乏哪些基因是人格候選基因的強假設,因此試圖將那些與具有生理作用的DNA標記有關的基因與人格聯系起來的做法是很有道理的(張麗華,宋芳,鄒群,2006)。
3.2 研究策略
人格分子遺傳學研究者主要采用連鎖策略和關聯策略來尋找和鑒別對特定人格或行為特質有廣泛遺傳影響的具體基因。連鎖策略(linkagestrategy)采取從行為水平到基因水平的“自上而下”的研究思路,它以攜帶某種人格特質或障礙的家系為研究對象,對連續幾代人的DNA樣本進行分析,以確定是否有對該人格特征影響較大的特定基因存在。由于研究者并無假定的候選基因,這種策略對定位單基因遺傳特質的強效基因十分有效,但當牽涉若干個作用較小的基因時它便不再那么有效。然而,大多數復雜的人格或行為特質往往牽涉多個微效基因,于是另一種較新的關聯策略(association strategy)便成為最常用的確定人格基因的策略。關聯策略采取由基因到行為的“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通過考察擁有某種特定基因(或等位基因)的個體比沒有該基因的個體在某種特定人格特質上的得分是高還是低,來確定候選基因與人格或行為特質之間的關聯情況,即一種可能的因果關系。關聯策略比連鎖策略更容易找到只有微弱效應的特定基因,但系統性不夠強。
隨著人類基因組多態性研究以及SNP分型技術的發展,全基因組掃描(genome-wide scanning)逐漸成為一種標志性的分子遺傳學人格研究策略(Strobel & Brocke,2011)。它主要包括對人格表現型的全基因組連鎖分析和全基因組關聯分析,先將人格表現型的相關位點定位于染色體某個區域,然后再進行候選基因研究或連鎖不平衡分析,確定其具體基因位點。例如,一項用全基因組掃描做的研究表明,傷害回避與8p21染色體區域存在顯著相關(zohar et al.,2003)。
3.3 具體研究與發現
基因主要是通過大腦中的神經遞質系統來影響人格的,因而參與調節神經遞質系統的基因便成為主要的候選基因。在Cloninger等人的人格心理生物模型中,新穎性尋求(novelty-seeking)、傷害回避(harm-avoidance)和獎賞依賴(reward-dependence)三種氣質維度被假定分別與大腦調節不同類型刺激反應的三種神經遞質系統即多巴胺(dopamine)系統、5-羥色胺(serotonin)系統和去甲。腎上腺素(noradrenaline)系統相聯系。此類理論假設促使人格分子遺傳學研究者們主要從這三種神經遞質路徑考察了基因多態性與人格之間的關系。
3.3.1 多巴胺系統
多巴胺是腦部負責快樂和興奮的一種積極化學物質,它的缺乏會促使個體積極尋求有效物質或新異經驗以增加多巴胺釋放。到目前為止,人格研究中最早且最多關注的DNA標記是位于第11號染色體短臂上的多巴胺D4受體基因(DRD4)。1996年,兩個獨立研究小組同時在《自然遺傳學》上報告了DRD4基因的3號外顯子中的48-bp VNTR多態性與新穎性尋求之間存在正相關,標志著人格分子遺傳學研究的初步登場(Ebstein & Israel,2009)。其中,Ebstein領導的小組運用三維人格問卷(TPQ)對124名猶太健康志愿者進行了測量,發現長重復段DRD4等位基因對新穎性尋求具有6%的解釋效應,而未發現它與另外三個TPQ指標(獎賞依賴、傷害回避和堅持性)有顯著關聯(Ebstein et al.,1996);Beniamin領導的小組運用大五人格量表修訂版(NEO-PI-R)對315名美國成人和兄弟姐妹進行了預測測量,也發現擁有長重復段DRD4等位基因的個體比擁有短重復段DRD4等位基因的個體新穎性尋求水平顯著高,并且發現長重復段DRD4等位基因與NEO-PI-R量表的外傾性和責任心兩個維度顯著相關,而在其他三個維度即神經質、開放性和宜人性上未見此結果(Benjamin et al.,1996)。對于這兩種研究的結果可能的解釋是,擁有長重復段DRD4等位基因的個體對多巴胺的相對缺乏反應敏感,需要尋求外界新異經驗來增加多巴胺釋放,而擁有短重復段DRD4等位基因的個體傾向于對腦中已經存在的多巴胺作出高度反應,無需尋求新異經驗便可使多巴胺含量達到適當水平。
此后,一系列研究對DRD4基因與新穎性尋求這種人格特質之間的關聯進行了重復驗證,但結果并不完全一致。兩項分別以德國人和日本人為被試的研究證實DRD4基因與新穎性尋求特質之間的確存在顯著關聯(strobel,Wehr,Michel,&Brocke,1999;Tomitaka et al.,1999);Burt等人對明尼蘇達137個雙生子家庭所做的研究發現,DRD4基因與新穎性尋求測量指標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Bun,McGue,Iacono,Comings,&MacMurray,2002);Ekelund等人則得出了與1996年研究相反方向的結果,即在新穎性尋求水平較高的群體中,2次和5次重復等位基因而非7次重復等位基因的頻率更高(Ekelund,Lichtermann,Jarvelin,& Pelmnen,1999)。除此之外,有些研究還發現DRD4基因與其他人格候選基因存在聯合效應。一項關于1歲新生兒對新異事物反應的研究發現,DRD4基因中的48-bp VNTR與5-羥色胺轉運體基因(5-HTT)中的一種多態性存在聯合效應(Lakatos et al.,2003)。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多樣的研究結果,可能與樣本大小、被試特點(年齡、性別和種族文化等)、測量工具、研究設計等因素有關。例如,分組方法不同所得研究結果就會有很大差異(Tsuchimine et al.,2009)。不管怎樣,這都有待于進一步研究證實。
除DRD4基因外,研究者還對多巴胺系統中的其他人格候選基因進行了考察,如多巴胺D2受體基因(DRD2)、多巴胺D3受體基因(DRD3)、多巴胺D5受體基因(DRD5)以及多巴胺轉運體基因(DATl)等。一項用多種人格測驗所做的研究表明,DRD2基因的-141C插入/缺失多態性與卡氏人格量表(KSP)測量的冷漠以及北歐大學人格量表(SSP)測量的自信缺乏之間存在關聯(JSnsson et al.,2003,),而利用氣質性格量表(TcI)對被試所做的一項研究表明,-141C插入/缺失多態性和DRD2/ANKK1基因的TaqlA多態性與人格特質之間可能并非存在直接強相關,而是在DRD2基因與ANKKl基因的交互作用條件下才對人格產生影響(Tsuchimine et al.,2012)。在一個由862名個體組成的樣本中發現DRD3基因與神經質和行為抑制存在關聯,而當該樣本擴大到1465人時這種關聯未得到驗證(Henderson et al.,2000)。有研究表明,DRD5基因可能與人格的持續性發展有關(Vanyukov,Moss,Kaplan,Kirillova,&Tarter,2000)。由于發現DAT1基因與具有某些新穎性尋求特征的注意缺陷多動癥(ADHD)存在關聯(Jorm et al.,2001,),有人用極端分數個體為被試考察了DATl基因與新穎性尋求之間的關聯,結果表明這種效應只在女性被試身上有所顯現(van Gestel et al.,2002)。
3.3.2 5-羥色胺系統
5-羥色胺作為一種生物胺,對于人類的攻擊性、抑郁、焦慮、沖動、幸福感等情緒情感具有重要調控作用。此系統中最經常被研究的人格候選基因是5-羥色胺轉運體基因(5-HTT),該基因越長釋放和回收5-羥色胺的效率越高,已有許多研究考察了它與傷害回避等焦慮類人格特質之間的關聯。5-HTT基因具有兩種多態性:5-HTT基因連鎖的多態性區域(5-HTTLPR)和5-HTT基因2號內含子中的VNTR多態性,其中人格研究關注最多的是5-HTTLPR。
1996年的一項經典研究發現,短5-HTTLPR等位基因攜帶者較長5-HTTLPR等位基因攜帶者在神經質和傷害回避維度上的表現水平更高(Lesch et al.,1996)。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表明,攜帶一個或兩個短5-HTTLPR等位基因復本的個體在對恐怖刺激的反應中表現出更強的杏仁核神經元活動(Harid et al.,2002)。這種由遺傳導致的杏仁核對情緒刺激的興奮性差異支持了該結論。不過,也有一些其他研究并未發現此種關聯(Flory et al.,1999;Tsai,Hong,& Cheng,2002)。還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結果。例如,使用極端得分個體做的一項研究發現,短5-HTTLPR等位基因在低傷害回避群體中比在高傷害回避群體中出現的頻率更高(van Gestel et al.,2002)。2004年的一份元分析指出。這種可重復性的缺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樣本量過小以及所使用的量表不同而導致(Sen,Burmeister,& Ghosh,2004)。分析者發現,運用大五人格量表測量的神經質與5-HTTLPR有顯著關聯,而運用氣質性格量表測量的傷害回避與5-HTTLPR不存在任何顯著關聯。2008年的另一份元分析也得出了類似結論(Munaf6 et al.,2008)。然而,使用NEO-PI-R量表對4000多名被試進行的一項大型研究發現,5-HTTLPR與神經質或其各維度(焦慮,抑郁,憤怒,敵意,自我意識,沖動。易受傷害性)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Terracciano etal.,2009)。近年來,有研究者發現,與其雜合子同伴或短等位基因的純合子同伴相比,具有長5-HTLPR等位基因的純合子個體通常更關注積極情感畫面,而選擇性地回避一同呈現的消極情感畫面(Fox,Ridgewell,& Ashwin,2009)。這表明他們通常更加樂觀。使用信息加工眼動跟蹤評估法進行的另一項研究發現,短5-HTLPR等位基因攜帶者在視覺上更加偏愛積極場景而回避消極場景,長5-HTLPR等位基因的純合子個體更加無偏地看待情緒場景(Beevers,Ellis,Wells,& McGeary,2009)。這表明,短5-HTLPR等位基因攜帶者可能比長等位基因純合子個體對環境中的情緒信息更加敏感。對于5-HTLPR與人格特質之間關系的這些看似不一致的結論,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確證。此外,一項最新研究顯示,5-HTLPR與Val66Met兩種多態性對傷害回避存在顯著交互作用(Ariaset al.,2012)。
除5-HTT基因外,研究者還對5-羥色胺系統中的另外兩個人格候選基因5-羥色胺2A受體基因(5-HT2A)和5-羥色胺2C受體基因(5-HT2C)進行了考察。有研究者在雙極性精神障礙患者和健康控制組群體中檢驗了5-HT2A的1號外顯子中的一種單核苷酸多態性與傷害回避維度之間的關聯,但是沒有發現任何關聯存在(Blairy et al.,2000)。還有研究者以健康日本人為樣本對5-HT2A的5種單核苷酸多態性進行了考察,沒有發現它們與氣質性格量表的任何維度存在關聯(Kusumi et al.,2002)。就5-HT2C與人格的關系而言,研究者發現5-HT2C中的一個點突變與三維人格問卷的獎賞依賴維度和堅持性維度存在關聯,并且DRD4與5-HT2C對獎賞依賴存在顯著交互效應(Ebstein et al.,1997)。然而,后來的一項重復性研究發現,5-HT2C對獎賞依賴不存在主效應,但DRD4與5-HT2C對獎賞依賴確實存在顯著交互效應(Kühn et al.,1999)。
3.3.3 去甲腎上腺素系統
在人格的分子遺傳學研究中,人們對去甲腎上腺素系統的關注遠不及對多巴胺系統和5-羥色胺系統的關注多,但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有研究以健康被試為樣本,考察了去甲腎上腺素轉運體(NET)的一種外顯子限制性片段長度多態性(RFLP)與氣質性格量表中各維度之間的關系,但沒有發現任何關聯存在(Samochowiec et al.,2001)。不過,另一項以朝鮮人為被試的研究表明,去甲腎上腺素轉運體的T-182C基因多態性與氣質性格量表的獎賞依賴維度存在顯著關聯(Ham,Choi,Lee,Kang,& Lee,2005)。有研究表明,在中國人被試中,αla腎上腺素受體基因(ADRAlA)和0c2a腎上腺素受體基因(ADRA2A)的多態性與三維人格問卷各維度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Tsai,Wang,& Hong,2001)。而之前的另一項研究發現,ADRA2A的一種常見單核苷酸多態性與易怒性、敵對性和沖動性諸測量值之間的確存在某些關聯(comings et al.,2000)。關于去甲腎上腺素系統的諸候選基因與人格之間關系的研究,有待進一步加強。
4 總結與展望
行為遺傳學通過數量遺傳學和分子遺傳學兩條取徑對人格遺傳性問題進行了不同層次的詳細探索,取得了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推進了我們對人格遺傳程度和遺傳機制的深刻認識,也有利于促進人格研究的科學化。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的兩類取向各具優勢和不足。數量遺傳學取向借助生態研究設計從宏觀上估計遺傳變異對人格差異的解釋程度,資料獲取經濟簡單、技術要求低,并且結果解釋相對容易,但它無法確切地告訴我們究竟哪些基因或多態性導致了人格差異以及具體作用過程如何(Parens,2004),對研究設計和被試取樣的依賴性較強,況且面對遺傳與環境實際存在相關或交互作用的不爭事實,遺傳率的解釋意義往往遭到質疑(Lerner,2011)。分子遺傳學取向擺脫了數量遺傳學取向存在的諸多不足,可以從DAN水平精確細微地探知造成人格障礙或差異的特定基因及其作用機制,但研究程序繁瑣復雜,對新興生物技術要求較高,在人格候選基因的選擇上帶有推測性,迄今為止尚未產生符合最初預期的可重復的實質性人格研究成果(McClellan & King,2010)。除此之外,兩類研究取向還存在諸多共同的問題:一是受測量手段限制,對被試自陳報告依賴性高,往往會造成某些人格特質在防衛或偽裝心理作用下被隱藏;二是由于研究設計和技術、被試取樣、人格和基因自身復雜性以及環境與基因的交互作用等原因,研究結果的可重復性不高(Kim & Kim,2011);三是受過去百余年消極心理學研究傳統的影響,所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精神分裂癥、抑郁癥、多動癥等病理人群(張文新,王美萍,曹叢,2012),缺乏對健康人群積極人格品質的遺傳研究;四是研究成果的現實利用率低,未能把研究所得成果及時有效地轉化為現實效益。
鑒于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所存在的諸多問題,未來研究應特別注意以下五個方面:
(1)強調兩種研究取向的有機結合,在數量遺傳設計中加入對特定基因型的直接測量。這兩種研究取向各有優缺,可以相互彌補,況且分子遺傳學的許多工作需用傳統數量遺傳學設計綜合考慮環境與遺傳因素來完成。未來研究可以在數量遺傳設計中加入對特定基因型的直接測量,例如,可以先用數量遺傳學方法確定某種人格特征是否具有遺傳性以及遺傳到什么程度,然后再用分子遺傳學方法從根本上細微探究影響人格的具體基因及其作用方式。
(2)注重多學科和多范式的有效整合。人格的行為遺傳學研究是一項綜合性很高的困難工作,涉及遺傳學、心理學、生物學、神經科學、醫學和社會學等多門學科,因此需要在更廣泛的視野下進行多學科的整合研究。人格的遺傳機制相當復雜,靠單一研究工具(如自陳問卷)或研究范式很難獲得理想結果,今后應在傳統研究范式的基礎上綜合采用腦成像、誘發電位、前脈沖抑制和計算機博弈模型等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從多個角度綜合考察和相互印證人格與基因的關系,從而彌補由自陳報告帶來的弊端,同時克服可重復性低的問題。
(3)擴大對健康人群積極人格品質的研究。未來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不僅要研究病理人群的消極人格品質,而且更要研究正常人群甚至超常人群的積極人格品質,探究它們的遺傳性及分子作用機制,為積極人格品質的培養提供遺傳學依據。
第2篇:分子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形態學;分子遺傳學;免疫表型;預后
彌漫性大B細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B-cell lymphoma,DLBCL)占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s lympho-mas,NHL)的31%~34%,在亞洲國家一般大于40%,是NHL中最常見的一個亞型。2008年WHO將DLBCL定義為一類彌漫生長的B細胞性淋巴瘤,瘤細胞核大于或等于正常吞噬細胞核,或大于正常淋巴細胞的2倍[1]。DLBCL在臨床特征、侵襲部位、組織形態學、分子遺傳學、免疫表型等方面,均表現出明顯的異質性。本研究著重從臨床、免疫、分子遺傳學等方面,對近年來的國內外研究工作及進展進行綜述。
1病因學
DLBCL的病因尚不清楚,大多數為原發,也可從慢性B淋巴細胞白血病/小淋巴細胞淋巴瘤、濾泡淋巴瘤、淋巴漿細胞性淋巴瘤、某些霍奇金淋巴瘤等發展和轉化而來,這種轉化可能與一些染色體結構改變有關。
DLBCL的發生可能與病毒感染、免疫缺陷以及自身免疫有關。EB病毒、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人類皰疹病毒8型(HHV-8)等感染與DLBCL的發生有著較為密切的關系。2011年5月第十二屆全國淋巴瘤學術大會肯定了我國近年來惡性淋巴瘤發病率逐年上升與環境污染和食品添加劑之間具有密切關系[2]。
2流行性病學與臨床特征
DLBCL是成人淋巴瘤中發病最多的一型,多見于60歲以上的老年人,也可見于兒童,男性比女性稍多。DLBCL臨床上以迅速增大的無痛性腫塊為典型表現,部分患者可有發熱、體重減輕等癥狀。DLBCL的臨床過程呈侵襲性,多為單個淋巴結或結外病灶出現迅速長大的局限性腫塊,約1/3的患者有全身癥狀[3]。腫瘤主要原發于淋巴結內,但有約30%~40%的患者首發于淋巴結外,一般呈局限性病灶。結外發生部位常見于胃腸道、皮膚、中樞神經系統、肺、肝、縱隔、骨骼、生殖器、及韋氏環,骨髓和血液的原發或累及少見,最常見的部位是胃腸道(胃和回盲部)[4]。
3分子遺傳學
DLBCL具有多種特征性的細胞分子遺傳學改變,許多病例往往具有復合性基因異常[5]。DLBCL常見的分子遺傳學改變包括1號染色體q2~23、6號染色體q21~25、14號染色體q11~12等區域出現缺失,12號染色體q12~14增多,非整倍體核型(+5,+6,+7,+18)及6q缺失,bcl-1、bcl-2、bcl-6、bcl-10、c-myc基因易位[5],等等。
20%~30%的DLBCL中可發生bcl-2基因和IgH基因易位,有研究表明多數bcl-2基因易位的DLBCL是由濾泡性淋巴瘤轉化而來。DLBCL中常涉及3 q27區域的改變,包括bcl-6基因易位、5'-非編碼區高頻突變及bcl-6基因內部缺失等,導致原癌基因bcl-6異常。在約30%~40%的DLBCL中可以檢測到bcl-6的t(3;14)(q27;q32)易位,該易位與預后不良有關,并且是一個獨立的危險因素;40%~70%的DLBCL發生bcl-6突變;此外,MU M-1基因易位到第14號染色體I g H增強位點,即t(6;14)(p25;q32)染色體易位,導致MUM-1蛋白過表達,從而促進DLBCL形成。少數DLBCL中還可檢出染色體易位t(1;14)導致的bcl-10基因易位,t(11;14)導致的bcl-1基因易位,8號染色體t(8;14)(q24;q32)導致的c-myc基因易位,等等。
在DLBCL中發現少數的p53基因的失活,p53抑癌基因在細胞增殖和存活的調控中起著重要的作用[6]。在DLBCL病例中因P16基因沉默表達或者表達量減少,從而誘發細胞周期調節失控,發生癌變。有研究發現DLBCL的發病還與原癌基因擴增有關,相關的原癌基因包括:rel、myc、bcl-2、rel基因編碼NF-rB信號途徑中的轉錄因子REL蛋白,REL蛋白對于惡性B細胞的增殖與生存十分重要[7]。
4免疫表型特征
DLBCL免疫分型方法有Hans分型、Choi分型、Tally分型[8],目前國內大多數醫院采用Hans的方法,通過免疫組織化學技術檢測CD10、BCL-6和MUM-1三種蛋白的表達,從而將DLBCL分為GCB亞型和非GCB亞型,后者包括ABC亞型和少數未分類者,其與基因表達譜分型的符合率可達80%~86%。有研究顯示兩個亞型間在化療反應性和預后上與基因表達譜分型相似[8]。
DLBCL分類采用免疫表型、組織學及臨床資料相結合,對指導臨床治療和判斷預后有重要意義。
第3篇:分子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
1.巴氏小體案例在遺傳學教學中的應用
2.下一代測序技術在表觀遺傳學研究中的重要應用及進展
3.遺傳學教學中在細胞與分子水平上理解等位基因的顯性與隱性
4.果蠅唾腺多線染色體研究進展及其在遺傳學教學中的應用
5.以人類血型為遺傳學案例教學的思考與實踐
6.表觀遺傳學藥物的研究進展
7.表遺傳學幾個重要問題的述評
8.構建優質教學體系,促進《遺傳學》精品教育
9.小鼠毛色遺傳的控制機制及其在遺傳學教學中的應用
10.肝癌發生的分子遺傳學和表遺傳學研究
11.景觀遺傳學原理及其在生境片斷化遺傳效應研究中的應用
12.以遺傳信息為主線的遺傳學教學架構及與其他課程的銜接
13.認知過程中的表觀遺傳學機制
14.我國高校遺傳學教材的出版與使用現狀的調查
15.表觀遺傳學:生物細胞非編碼RNA調控的研究進展
16.表觀遺傳學視角下運動干預阿爾茨海默病的機制分析
17.遺傳學與基因組學整合課程探討
18.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19.癲癇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20.不僅僅是遺傳多樣性:植物保護遺傳學進展
21.利用文獻精讀教學新模式優化遺傳學教學
22.2015年中國醫學遺傳學研究領域若干重要進展
23.發展行為遺傳學簡介
24.光遺傳學技術應用于動物行為學在神經回路中的研究進展
25.表遺傳學推動新一輪遺傳學的發展
26.生物教育專業《遺傳學》教學改革的探索
27.糖尿病腎病遺傳學研究進展
28.腫瘤表觀遺傳學研究熱點的聚類分析
29.淺談高校《遺傳學》課程教學改革與實踐
30.2015年中國微生物遺傳學研究領域若干重要進展
31.利用經典文獻優化《遺傳學》雙語教學
32.孟德爾豌豆基因克隆的研究進展及其在遺傳學教學中的應用
33.表觀遺傳學在肺癌診治中的研究進展
34.人格行為遺傳學研究的兩類取向
35.害蟲遺傳學控制策略與進展
36.表觀遺傳學及其應用研究進展
37.阿爾茲海默病的表觀遺傳學機制及相關藥物研究
38.胃癌遺傳學及表遺傳學研究進展
39.遺傳學在膽管細胞癌發展中的重要性
40.子癇前期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41.行為遺傳學:從宏觀到微觀的生命研究
42.遺傳學史在遺傳學教學中的作用
43.男性不育的遺傳學評估
44.表觀遺傳學與腫瘤干細胞
45.開放式教學在遺傳學實驗教學中的探索與實踐
46.表觀遺傳學調控與婦科腫瘤發生、演進及治療的研究進展
47.規律運動干預人類衰老過程的表觀遺傳學機制研究進展
48.表觀遺傳學及其在同卵雙生子研究中的新進展
49.分子群體遺傳學方法處理鯉形態學數據的適用性
50.番茄果重數量性狀基因的研究進展及在遺傳學教學中的應用
51.遺傳學教學中遺傳學史及科學方法論的教育
52.景觀遺傳學:概念與方法
53.孤獨癥的遺傳學和神經生物學研究進展
54.肺癌表觀遺傳學的研究進展
55.腫瘤的表觀遺傳學研究
56.遺傳學課程群的設置和思考
57.《遺傳學》課程的建設與優化
58.表觀遺傳學在中樞神經系統退行性疾病中的研究進展
59.遺傳學實驗教學體系的改進
60.肝癌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61.保護生物學一新分支學科——保護遺傳學
62.表觀遺傳學在淋巴系統腫瘤研究中的新進展
63.大腸癌的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64.重視經典遺傳學知識體系構建和學生自學能力的培養
65.植物化學遺傳學:一種嶄新的植物遺傳學研究方法
66.關聯分析及其在植物遺傳學研究中的應用
67.表觀遺傳學及現代表觀遺傳生物醫藥技術的發展
68.三陰性乳腺癌與表觀遺傳學研究現狀
69.構建培養新型醫學人才的醫學遺傳學課程體系改革
70.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的遺傳學檢測研究進展
71.釘螺遺傳學及其生物學特性的研究進展
72.羞怯:來自行為遺傳學的觀點
73.遺傳學探究性實驗教學的思考及實踐
74.“教學、實踐、科研、臨床”四位一體的醫學遺傳學教學體系建設探索與實踐
75.國內高校遺傳學教材發展研究
76.男性生殖遺傳學檢查專家共識
77.腫瘤表遺傳學研究的進展
78.創新性遺傳學大實驗對提高大學生綜合能力的研究
79.白內障表觀遺傳學研究的現狀及進展
80.遺傳學研究性實驗教學模式探索與創新人才培養
81.表觀遺傳學在木本植物中的研究策略及應用
82.高通量測序技術結合正向遺傳學手段在基因定位研究中的應用
83.激發與培養學生學習遺傳學興趣的教學途徑
84.從表觀遺傳學開展復雜性疾病證候本質的研究
85.藍藻分子遺傳學十年研究進展
86.建設遺傳學課件體系 提高多媒體教學質量
87.表觀遺傳學與腫瘤
88.原發性肝癌的表觀遺傳學及其治療
89.青少年焦慮、抑郁與偏差行為的行為遺傳學研究
90.兒童孤獨癥的遺傳學研究進展
91.本科生遺傳學實驗教學的改革探討
92.與閉經有關的遺傳學問題
93.多媒體教學在遺傳學“三點測驗”教學中的實踐
94.一個實用的群體遺傳學分析軟件包——GENEPOP3.1版
95.論從“腎為先天之本”到“中醫遺傳學”
96.《遺傳學》多媒體教材的編寫與實踐
97.肺癌的表觀遺傳學研究進展
98.無創性產前遺傳學檢測研究進展
第4篇:分子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
Biology, University of Toronto, Canada
(Ed.)
Genes, Development
and Cancer
The Life and Work of Edward B. Lewis
2004, 557pp.
Hardcover $ 190.00
ISBN 1-4020-7591-X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愛德華?B?劉易斯(Edward B. Lewis)因在遺傳學和發育生物學方面的貢獻而聞名世界,此外,他在電離輻射與癌癥關系的研究方面也走在前列。但由于種種原因他的論文很少有人拜讀過。本書由與劉易斯共事20年的Howard Lipshitz編輯出版,書中收集了劉易斯在遺傳、發育生物學和輻射與癌癥關系三方面的重要文章,將他在這三方面發表的重要論文結集出版是第一次。
在遺傳學的研究中,20世紀的前50年中實驗遺傳學是主導,而最后的25年中分子遺傳學方法引發了該領域中的革命,愛德華?B?劉易斯的研究正是連接這二者的橋梁。劉易斯因在發育遺傳學領域的突出貢獻獲得了諾貝爾獎,也為我們目前采用的控制動物發育的廣泛的、進化保守的策略打下了基礎。劉易斯在電離輻射和人類癌癥關系的研究也曾經推動了公眾在核武器試驗方面的大討論。
全書共分五個部分:基因、基因與發育、分子與發育、輻射與癌癥和歷史觀點,這些也反映了他研究焦點的改變。但是很多文章都是以總結的形式發表,結果也往往以摘要的形式給出,書中的實驗方法、結果等對讀者而言比較晦澀。所以Howard Lipshitz在編輯此書時,在每個部分的前面都從歷史的角度講述了當時的研究基礎和背景,包括劉易斯自己的觀點和當時學術界的觀點,還闡述了劉易斯采用的科學方法以及驅使他作出課題選擇的動力,這些信息可以幫助讀者很好的理解本書。
本書對廣大從事生命科學和生物醫學的研究人員會有莫大的幫助,其中包括遺傳學家、發育生物學家、分子生物學家、放射生物學家和癌癥研究者。本書也可以作為高年級本科生和碩士研究生在遺傳學、發育生物學、輻射與癌癥的課程學習資料。另外,這本書不僅收錄了原始的論文,也包括相應的注釋,故而對科學史學家也有重要的價值。
劉玉琴,教授
(中國醫學科學院基礎醫學研究所)
第5篇:分子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
【論文摘要】1937年美籍奧地利生物學家貝塔朗菲提出了一般系統論原理。系統中每個要素都處于一定的位置,起著特定的作用。個體發育中,基因按一定的時、空次序有選擇地表達。基因是組成染色體的遺傳單位,并證明基因在染色體上作直線排列。一定的基因在一定的條件下,控制著一定的代謝過程,從而體現在一定的遺傳特性和特征的表現上[1]。基因還可通過突變而改變。隨著人類基因譜的逐步闡明、遺傳工程技術的充分發展,基因治療很可能在臨床疾病治療中產生革命性變化,這就需要研究人員在實踐中,用自然辯證法系統論理論,來指導思想,拓展研究思路,從而解決這一重大難題。
【Abstract】in 1937 the American nationality Austria biologist bright Philippines proposed the general system theory principle. In the system each essential factor all is in the certain position,is playing the specific role. In ontogenesis,gene according to certain when,the spatial order have the choice expression. The gene is composes the chromosome the hereditary unit,and the proof gene makes the line spread in the chromosome. The certain gene under the certain condition,is controlling the certain metabolism process,thus manifests in the certain heredity characteristic and in the characteristic performance The gene also passable sudden change has changed. Along with the human gene spectrum gradually expounded,the genetic engineering technology full development,the gene treatment very possibly treats at the clinical disease has the revolutionary change,this needs the researcher in the practice,with natural diagnostic method system theory theory,guiding ideology,development research mentality,thus solves this single layer big difficult problem.
【Key word】system theory;Gene and heredity;Gene treatment
系統論是21世紀以來科學技術、文化和社會發展的自然亦必然的思維趨向,是比知識更有力量的一種客觀存在,它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是當代人認識對象的工具和手段。西沃爾-賴特在1929年寫到:一個群體中“單個基因的選擇系數(即基因的適合度),一定受到這個群體整個基因頻率系統的影響[2]”。本文從系統論觀點來分析基因與遺傳之間的因果聯系以及基因在臨床上的應用。
1 系統論相關論點
1937年貝塔朗菲提出了一般系統論原理,使人類的思維方式發生了深刻變化。以往研究問題人們總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簡單的因素來,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質去說明復雜事物。這種方法的著眼點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單項因果決定論,它不能如實地說明事物的整體性,不能反映事物之間的聯系和相互作用,它只適應認識較為簡單的事物,在人類面臨許多規模巨大、關系復雜、參數眾多的復雜問題時,就顯得無能為力了。系統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著,每個要素在系統中都處于一定的位置上,起著特定的作用[3]。系統科學方法是認識、調控、改造復雜系統的有效途徑,為人們提供了制定系統最佳方案以實行優化組合和優化管理的手段,為人們提供了新的思維模式,倡導從整體上進行思維。
2 基因與遺傳
20世紀20年代,摩爾根學派在孟德爾的豌豆雜交試驗的基礎上,開展了遺傳規律的研究,建立了以基因學說為基礎理論的細胞遺傳學,肯定了基因是遺傳的基本單位,存在于細胞的染色體上。到30年代,知道染色體結構和數目的變化會影響到遺傳,知道一個基因可以突變成若干等位基因。到了40年代,遺傳學有了兩個重要的進展或突破:一是初步發現去氧核糖核酸簡稱DNA,是遺傳物質;一是提出了一個基因一種酶的原理。直到50年代,建立了分子遺傳學,解決了有關遺傳的若干重大問題。DNA和另一類核酸即核糖核酸(RNA)都是由核苷酸所組成的多聚體,是大分子。核苷酸的主要特點存在于所含的有機堿,即兩種嘌呤和兩種嘧啶。
1953年,形成雙螺旋的分子結構。根據DNA中堿基互補的原理,一個DNA分子可以成為內容一致的兩個DNA分子。蛋白質是由氨基酸所組成的多聚體,是大分子。組成蛋白質的可以是一條多肽鏈或幾條多肽鏈。多肽鏈就是由若干氨基酸前后連接而成的分子。蛋白質的合成就是遺傳信息從遺傳物質流入蛋白質的過程。這包括兩個步驟:一是轉錄,一是翻譯。由于組成DNA 和RNA的零件都是核苷酸,所以遺傳信息從DNA流入RNA 叫做轉錄。由于蛋白質是由另一種另件(氨基酸)組成的,所以遺傳信息從RNA流入蛋白質叫做翻譯。這里的RNA叫做信使RNA,意思是說,它是基因遺傳信息的使者。在分析蛋白質分子的合成中也查明了各氨基酸的遺傳密碼,于是建立了遺傳密碼理論。遺傳信息都是由遺傳密碼組成。每一個遺傳密碼都由三個堿基組成,氨基酸不同,其遺傳密碼就不同。
從70年代開始,分子遺傳學的進一步發展,誕生了基因重組技術,即生物基因工程,它開創了改造生物和創造生物的新時期。
3 用系統論的觀點來看待基因與遺傳的因果聯系
系統科學可以把一個原子看作系統,它也可以把器官、生物機體、家庭、社區、國家、經濟以至生態看作系統。生物體是由細胞構成的多層次的復雜系統。盡管在細胞和分子水平對發育的分析已取得長期的進展,但個體發育仍不能從分子水平和細胞水平的分析得到全部解釋。個體發育中,基因按一定的時、空次序有選擇地表達。這首先表現在細胞表面形態調節分子的變化,從而導致胚層分離、形態速成運動和組織發育等細胞的集體行為。
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考慮環境對基因的自上而下的約束與引導作用。其一,我們知道環境的改變會迫使生物個體和種群盡可能調節自身以適應環境的變化。顯然生物體為適應環境變化而做的調節又必定會引起生物體內生物化學、生物磁電等的變化。在生物史上地球環境的巨變是造成大量新物種產生的直接原因。我們可以設想,基因有向緩解環境對生物壓力的方向突變的趨勢,如果這一假說成立的話,顯然就會使來自上層變化的信息產生對下層生物體基因變異的自上而下的約束與引導作用。其二,我們知道基因的復雜結構具有巨大的信息存儲能力。生物體的基因中記錄了該生命體全部歷史的重要信息。
4 基因治療的前景
隨著對基因治療研究的深入,我們不能忽視子系統的系統性和整體性,不能用局限的、部分的、單一的觀點來以偏概全。事實上,人體的復雜性程度,各個系統的相關性、相互作用及相互制約程度,遠不是我們所能完全解釋得了的,只有在系統環境中解決這些難題,才會有實用價值和臨床價值。這就需要研究人員在實踐中,用自然辯證法系統論理論,來指導思想,拓展研究思路,從而解決這一重大難題。
參考文獻
[1] 范怊.系統論整體觀在醫學科學中的地位[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0,(11)1:10
第6篇:分子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
南方紅豆杉細胞培養及次生代謝研究
紅豆杉資源非常有限且紫杉醇含量極低,遠遠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植物細胞培養具有繁殖速度快,培養條件易于優化,培養過程易于人工控制,不受時間、地域等因素的限制等優點。因此,采用紅豆杉細胞培養生產紫杉醇以及對紫杉醇合成代謝途徑進行調控來提高紫杉醇的產量已成為當今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課題之一,并已取得了較大進展。對其細胞培養、紫杉醇合成與代謝調控、擴大培養及分離純化[16-19]等方面開展了廣泛深入的研究,研究發現,營養調控[20-23]、物理控制[24-26]、前體飼喂[27]、添加抑制劑[28]、誘導子調控[20-21,29-33]、雙液相培養[34]、兩步法培養[35]等一系列技術均能影響南方紅豆杉的次生代謝。細胞離體培養縮短了培養周期,這樣不僅有利于培養條件的優化,也為通過多種誘導途徑來提高細胞中次生代謝產物的含量成為可能,南方紅豆杉組培體系的不斷完善為進一步研究次生代謝產物的合成與代謝奠定了良好基礎。細胞培養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提高紫杉醇的產量,因此利用生物反應器替代搖瓶進行紅豆杉細胞規模培養以及工業化生產就成為另一個研究熱點和重點。目前,喜馬拉雅紅豆杉[17]、中國紅豆杉[36-37]、歐洲紅豆杉[17]、曼地亞紅豆杉[38]和云南紅豆杉[39]等均實現了生物反應器的大規模培養,部分并已投產[38]。但南方紅豆杉細胞懸浮培養尚未實現生物反應器的大規模培養,還正處在研究階段。另外,近幾年來,國內外利用微生物發酵來生產紫杉醇的研究報道也不少,但目前利用內生真菌來產生紫杉醇的產量并不高,尚未能進行工業化。
南方紅豆杉分子標記研究
近年來,隨著分子生物技術的迅速發展,植物在蛋白質和DNA水平上的遺傳多樣性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并在物種鑒定和瀕危物種保護中得到廣泛的應用。20世紀90年代以來,分子標記技術被廣泛用于動、植物遺傳育種、基因診斷、居群遺傳學、生物系統學與進化研究上,如RAPD標記技術和ISSR分子標記技術,這2種分子標志均可揭示種間與種內的遺傳多樣性及其進化的親緣關系(但后者比前者穩定性和重復性要好),可進一步為開展植物分子輔助育種、遺傳轉化及其轉基因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有價值的理論依據。2000年,王艇等[40]采用RAPD技術,在分子水平上對南方紅豆杉的系統發育進行了探討。2003年,張宏意等[41]通過隨機擴增多態性方法對廣東、湖南、江西3省的12個南方紅豆杉自然居群進行了基因組DNA多態性分析,分析表明南方紅豆杉居群間的遺傳距離與這些居群的地理分布相關,相同或相鄰產地的居群間的遺傳距離較小,不同產地個體間的遺傳距離較大。2005年,王貴榮等[42]通過對6個紅豆杉種進行RAPD遺傳多樣性分析和染色體鑒定,得出南方紅豆杉與中國紅豆杉的遺傳距離最小,紅豆杉與曼地亞紅豆杉的親緣關系最遠,6個紅豆杉種染色體數均為2n=24,為進一步保護和利用中國的紅豆杉資源提供進化分子遺傳學方面的依據。2007年,李振宇[43]根據cpDNA基因間隔區對南方紅豆杉的種群遺傳結構和系統地理進行了研究,同年,黃麗潔[44]采用葉綠體SSR技術對南方紅豆杉的遺傳多樣性和遺傳距離進行了研究,并認為南方紅豆杉具有中等水平遺傳多樣性,不同地區間遺傳分化小,種群和地區間基因流較大。2008年,茹文明等[45]通過RAPD技術對南方紅豆杉8個自然種群的遺傳多樣性進行了分析,得出南方紅豆杉種群瀕危的主要原因不是其遺傳多樣性,而可能是由其本身生物學和生態學特性及其生存環境破壞所致的。為進一步探討南方紅豆杉瀕危原因和對該物種的保護、進化潛力及種質資源利用等方面提供分子遺傳學數據。2009年,張蕊等[46]利用ISSR分子標記對來自10省區15個南方紅豆杉代表性種源進行了種源遺傳多樣性及地理變化、種源遺傳分化等方面的研究,得出了與上面相一致的結論。同年,張玲玲[47]通過RAPD和ISSR2種分子標記對福建省的南方紅豆杉遺傳多樣性進行了初步研究,并對其RAPD和ISSR2種指紋圖譜進行了比較分析。2010年,李乃偉等[48]采用ISSR標記技術對南方紅豆杉遷地保護小種群及其衍生自然種群小斑塊(小居群)的遺傳多樣性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南方紅豆杉遷地保護各自然小居群間的遺傳距離與其地理生境有關,而與其地理距離并無顯著的相關性。2011年,李乃偉等[49]又對南方紅豆杉野生種群、遷地保護栽培種群及遷地保護衍生種群的遺傳多樣性和遺傳結構進行ISSR分析和比較,得出南方紅豆杉遷地保護衍生種群的遺傳多樣性與野生種群接近,這為南方紅豆杉的物種遷地保護提供了有力依據。
第7篇:分子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
其實,大多數環境適應都涉及相關疾病。如乳制品代謝過程中存在乳糖不耐受、紫外輻射適應中的光敏性皮炎以及維生素D缺乏性佝僂病等。
隨著群體遺傳學信息、環境因素和表型資料的不斷累積,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環境因素在人類的適應性進化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簡單而言,人類群體環境適應性研究就是應用達爾文進化論的思維,分析不同環境對生存于其中的人群的自然選擇作用。”中國科學院院士張亞平說。
張亞平等從自然氣候因素、環境中的病原體分布及食物來源等方面,對人類的適應性進化進行了綜述。文章第一作者、寧波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系講師季林丹認為,人類群體環境適應性研究的意義之一,是可為人類的歷史提供印證信息甚至新的線索。“從采集狩獵型社會逐漸過渡為農耕社會,人類的飲食組成發生了極大變化,牛奶及其他乳制品、麥類等開始出現在人們的食物中。現有的遺傳學數據顯示,不同人群中與上述食物代謝相關的基因可能經歷了自然選擇,不同人群的遺傳背景與他們的飲食習慣密切相關。”
為什么北方人通常比南方人高大?為什么隨著緯度升高,人的膚色逐漸變淺?“通過環境適應性研究,可以直接從環境角度來尋找不同人群表型差異的根本原因。”季林丹說。
此外,人類群體環境適應性研究還可為今后氣候變遷應對策略的制定提供參考信息。
為更好地研究臨床疾病服務
在張亞平看來,人類群體環境適應性研究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研究臨床疾病。
從達爾文醫學角度,疾病就是一種不適應體內外綜合環境而導致的狀態,只是這個不適應要經由一個很長的進化學上的時間尺度才顯現出來而已。因此,這些疾病的發病機制及診療可以嘗試從分子進化角度進行新的探討。
“隨著科技發展,不同人群的表型數據、分子遺傳學數據、環境數據逐步累積,統計分析方法不斷改進,從分子進化角度來研究人類的進化歷史和相關疾病的研究日益增多,逐步開始從整體、多維的角度分析人類表型/基因型的分子進化。”
寧波大學醫學院預防醫學系副教授徐進舉了兩個國外的研究例子:2010年,劍橋大學研究人員發現大猩猩能夠攜帶一種導致瘧疾的惡性瘧原蟲,這種瘧原蟲曾被認為只存在于人類身上。瘧疾每年導致200萬人死亡,其中85%的死亡發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他們認為,隨著靈長類動物和人類的接觸增加――這主要是由于非洲的伐木和森林砍伐――人類與動物之間的寄生蟲傳播風險會增加。
近期,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員通過研究人群中基因變異頻率與環境因素的關系,發現病原體尤其是寄生蟲在人類基因變異中的作用最為重要;同時這些變異或許使人類對自身免疫性疾病更加易感。
第8篇:分子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
基礎醫學專業主要課程 人體解剖學、組織學與胚胎學、正常人體形態學實驗、細胞生物學、分子生物學、生物化學、醫學遺傳學、醫學生物學實驗、醫學微生物學、醫學免疫學、病原生物學與免疫學實驗、生理學、病理生理學、藥理學、基礎醫學機能學實驗、神經生物學、細胞與分子免疫學、分子遺傳學、分子病理學、內科學、外科學、婦產科學、兒科學、醫學統計學、預防醫學;普通心理學、醫學倫理學;基本原理、思想道德修養、法律基礎;英語、高等數學、醫用物理學、化學等。
基礎醫學專業就業前景 不得不說,基礎醫學專業的就業面是非常廣的,而且薪資待遇也是比較豐厚。但也要求本專業畢業生具有較全面的綜合素質、較強的創新精神、較好的學習能力以及外語和計算機應用能力。學生畢業后可以在高等醫學院校和醫學科研機構等部門從事基礎醫學各學科的教學、科學研究及基礎與臨床相結合的醫學實驗研究工作。如此看來,基礎醫學專業的就業前景還是很廣闊的。
基礎醫學專業培養能力 1.掌握基礎醫學的基本理論、基本知識;
2.掌握醫學實驗的分析、設計方法和操作技術;
3.具有基礎醫學科學研究的基本能力;
4.熟悉基礎醫學教學工作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5.熟悉臨床醫學基本知識并了解臨床醫學的新進展和新成就;
6.掌握文獻檢索、資料查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學研究和實際工作能力。
第9篇:分子遺傳學研究方法范文
〔關鍵詞〕父母影響;兒童影響;行為遺傳學;親子互動
〔中圖分類號〕G7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2684(2011)10-0010-03
一直以來我們都知道,父母影響孩子的成長。在父母影響孩子的過程中,兒童就如同陶泥一般,被動地任由父母揉捏成各種形狀。我們用父母影響這個概念來代表父母對孩子的影響,具體來說是父母對孩子行為和發展的各種影響方式[1]。但直到不久前,人們才認識到這個影響過程的可逆性。兒童對父母也有影響,孩子的個性將影響父母對教養行為的選擇,對這個孩子行得通的方式并不一定適用于其他的孩子。即便是年齡很小的孩子,都是交往行為的主動參與者。我們把以上現象稱為兒童影響,是指兒童因自身特質而對其養護人所造成的獨特的影響[1]。
行為遺傳學是指以解釋人類復雜的行為現象的遺傳機制為其研究的根本目標,探討行為的起源、基因對人類行為發展的影響,以及在行為形成過程中,遺傳和環境之間的交互作用 [2]。其實在兒童心理與行為的發展過程中,遺傳與環境的作用從來都是不可分割的。遺傳提供了生理上的基礎,而環境提供了發展的空間。行為遺傳學一方面強調遺傳因素對行為有決定性影響,但它同時認為遺傳并不直接決定行為,它只是行為產生的生理基礎,而行為的發展則受環境的影響。
本文旨在探討在孩子社會化過程中的父母影響和兒童影響,并結合行為遺傳學的有關研究成果,探討在兒童的發展過程中以父母教養方式為主的父母影響和兒童影響以及兩者的交互作用,以期進一步了解兒童發展中的影響機制。
一、遺傳因子的存在
隨著行為遺傳學的發展,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研究設計中證明帶著遺傳因子的兒童影響的存在。有些看起來是環境產生的影響卻能夠反映出遺傳的影響,因為這種經驗受到了個體遺傳差異的影響,在用環境測量衡量雙生子和收養研究的心理結果時,研究結果一致顯示了某些遺傳因素的影響 [3]。
研究表明,在家庭環境變量和孩子行為結果之間的聯系上,親生子女比撫養子女的這種聯系要強 [4]。這些結果暗示的信息是遺傳因素承載著一些可推測性的環境影響,如果忽略了遺傳的影響,那么會高估了父母親對孩子的影響。
例如,研究者廣泛使用了一種結合觀察和面談的家庭環境測量,這種方法被稱為“家庭觀察之環境測量”,簡稱HOME,其評價的是家庭環境方面,主要是父母的養育行為,比如父母的應答性、對孩子發展進步的鼓勵等。研究發現,同胞1歲和2歲時,HOME分數的相關高于被收養的兄弟姐妹,結果說明了HOME受到了遺傳的影響,遺傳因素能解釋HOME分數方差的40%左右 [4]。
鄧恩(Dunn)等人通過幼兒期母親―嬰兒互動的觀察研究并采用了收養設計和雙生子設計,發現了遺傳的影響 [5]。
戴卡德(Deckard)等人考察了雙生子和收養子女的一個研究設計,研究發現相同的母親對她的兩個孩子有不同的親子互動水平,以及兄弟姐妹之間的基因相似性解釋了大部分親子互動中的相似性。更令人覺得驚訝的是,遺傳上沒有相關關系的養子女與他們相同的收養母親有著不同的親子互動的水平 [6]。這個研究結果也說明了在親子互動中,帶著遺傳特征的兒童自身的特性對父母的教養方式的影響。
普洛明等人的一項研究命名為:非共享環境與青少年發展,簡稱NEAD,在這項研究中表明對應不同的教養方式,遺傳因子是不同的,例如苛刻的教養方式、溫柔的教養方式和監控的教養方式遺傳因子有著很大的差異。NEAD顯示了兒童遺傳影響大約有50%的概率解釋了母親對其孩子苛刻的對待方式[7]。這就說明了父母的養育行為和孩子的行為發展中,不是純粹的社會機制,還有遺傳機制,孩子自身的影響也在其中起著作用。這也證明了孩子的行為發展中,由遺傳因素帶來的孩子自身特征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即兒童影響再一次得到了驗證。
以上的研究都證明了在父母對兒童的教養方式中,遺傳因素的調節作用。不僅是父母通過教養方式對兒童的發展產生影響;同時,兒童由遺傳因子帶來的自身的特征也反過來影響父母。兒童不同的特征會引起父母不同的反應,因而使父母采用不同的方式對待他們。父母是根據兒童的行為特點來選擇和調整自己的教養方式的。
二、遺傳因子具體作用機制
那么父母的教養方式是怎樣部分地受到了遺傳因子的調節作用的呢?
1.基因型―環境相關
基因型―環境相關指的是遺傳在個體與環境接觸中起的作用[4]。行為遺傳學家普洛明提出了基因型―環境相關,這里他是指人的基因組成和所處環境之間的聯系,這種聯系有著不同的形式,見表一。
表一 基因型―環境相關的三種類型
按照表中所述,有三種基因型―環境相關:被動的、喚起的和主動的。涉及到兒童與父母的關系主要有兩種關系:被動關系,即父母不僅為孩子提供了基因特征,也提供了相應的經歷,例如,繼承了父母高智商的兒童很可能也同時享受著父母所給予的文化氣息較濃的成長環境,父母對兒童的教養方式中滲透著這種文化因素,而兩種因素相互作用,使得該兒童在學業上更容易取得成功;喚醒關系,即兒童與生俱來的特質會誘發其父母作出不同的回應。與天性安靜、嚴肅的孩子相比,天生外向、熱愛社交的兒童更容易得到父母的積極回應。過去人們通常認為,是由于成人對待孩子的方式使孩子更愿意與人交往,但從這個研究中,我們對這種因果關系可能要有新的認知了,可能是孩子自身的特點使其獲得了這樣的對待方式[1]。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基因型―環境的相關并非指獨立于個體之外的環境受到遺傳的影響,而是指個體經驗卷入的程度或個體接受環境影響的程度具有一定的遺傳性。遺傳的影響是通過被其作用的心理特質來傳遞的:遺傳影響著個體的心理特質,心理特質影響著個體的環境[10]。
隨著行為遺傳學的發展以及以上三種關于基因型―環境相關方法的發展,我們可以更加深入地研究父母的教養方式對兒童的心理發展背后的遺傳因素的作用。
2.基因型―環境的交互作用
基因型―環境的交互作用是指遺傳對環境的敏感性或易感性。它是指基因型不同的個體對相同的環境反應不同[11]。
有兩項收養研究發現了犯罪行為的基因型―環境交互作用的例子。研究發現,對于一個被收養者,如果他的養父母和親生父母都有犯罪記錄的話,那么他出現犯罪行為的概率更高,也就是說,如果兒童的親生父母被定過罪,那么養父母的定罪會使兒童更容易被定罪。
基因和環境的交互作用以及父母教養方式和兒童氣質的研究證明了這種相互影響。克堪斯卡的研究很好地闡述了這個問題,他的研究發現,父母溫和的教導措施能有效地使膽小的孩子發展其道德感,但對于膽大的孩子則沒有什么效果。
雙生子的研究方法可以用來鑒別基因型―環境交互作用。為了探測遺傳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可以把雙生子之一的表現型基因作為另外一個雙生子的遺傳風險的指標。采用這種方法分析顯示,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一般認知能力的遺傳率(74%)顯著高于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26%)。
大量的研究都在尋找基因型―環境交互作用的證據,但是鮮獲成功,原因之一可能是缺乏像動物實驗那樣高度的實驗控制,比如制造出極端的環境操控,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要在具有合理統計效力的方差設計分析中檢測到交互作用,所需的被試量則遠遠高于檢測主效應所需的被試量。因此,在父母教養方式的研究中,要找到基因與環境的交互作用,還需要進一步的實驗設計。
總之,過去,我們習慣于將發展結果歸因于環境,現在看來,基因對發展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覷的。基因和環境的相互影響是以雙向方式進行的,不是一個決定另一個,不能說究竟哪一個是發展的先決條件[1]。在父母對兒童的教養方式中,我們要看到父母對兒童的影響和兒童自身特性的雙向互動作用。
三、研究趨勢和展望
第一,研究內容更加豐富。現在大量的研究都是從行為遺傳學的角度證明了在父母的教養方式中遺傳因子的存在,以后會從各個方面具體探討父母的教養方式和兒童的社會化發展,內容更加豐富,主題更加深化。例如,父母教養方式與兒童依戀的研究、與兒童學業的相關研究等,從這些方面探討在父母教養方式中,遺傳與環境的交互作用。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行為遺傳學一般采用收養研究設計、雙生子研究和混合研究設計,以后的研究可能深入發展這些研究設計,設計出更好的實驗設計,更加巧妙地分離遺傳和環境的影響。特別是現在研究設計與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相結合,開發出一些心理學的統計應用軟件,例如LISREL、EQS等統計軟件的開發,大大提高了量化研究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分子遺傳學在逐步發展,運用分子遺傳技術去尋求對復雜心理特質產生影響的特定基因將是心理學研究最激動人心的方向之一[10]。分子遺傳學的相關研究可以運用到父母教養方式的研究中,隨著技術的進步,我們就可以找到影響兒童發展的基因,我們就可以根據不同基因的兒童適合什么教養方式,對兒童進行更好的指導,或是對一些不良兒童的基因進行改進,使得不良兒童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這些設想隨著行為遺傳學的發展會成為現實。
第三,雙向互動作用深入發展。在以往的研究中,針對父母對兒童的單向研究比較多,對親子互動的研究很少[9]。隨著相關學科的發展,特別是行為遺傳學的發展,以后的研究將更加注重雙向互動的研究。特別是現在理論界提出的動力系統觀,從另一個角度證明了行為遺傳學所證明的雙向互動的存在。動力系統觀點認為,一個家庭就是一個很好的動力系統,它是一個由兩種亞系統組成的三級組織,兩種亞系統分別是個人和個人之間的關系。家庭的整體特性不能由其成員的特點來推論,它包含一個極端復雜的循環影響的過程,任何部分的改變都會與其他部分以及系統整體形成循環往復的相互影響。因此,簡單的線性因果關系并不適應于家庭情境。在孩子的社會化過程別是父母的教養方式中,父母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孩子的影響也是有作用的,他們同屬于家庭這個系統中,在這個系統中,他們的關系是一種相互影響的作用,而不是一種簡單的單向關系[1]。因此,從動力系統的觀點看,我們發現在一個家庭中,兒童和父母同屬于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這種觀點和行為遺傳學的觀點是一致的。因此,以后的研究會綜合行為遺傳學、動力系統等多種觀點,在多種分支學科的基礎上,更好地探討父母教養方式的具體機制。
第四,在實際運用上,如上所述,親子互動中父母的教養方式的理念在實際運用中還不是很廣,與傳統的家庭教育觀念相比較,現代家庭關系和家庭教育的觀念與實踐發生了一系列的變革,這更加激勵有關研究者深入地探討父母教養方式對兒童心理、行為發展的影響[11]。以后會進一步運用到社會、家庭和學校中去,理論和實際相互促進,才更有利于兒童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H.Rudolph Schaffer.發展心理學的關鍵概念[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2] 白云靜,鄭希耕等.行為遺傳學:從宏觀到微觀的生命研究[J]. 心理科學進展,2005,(3):305~313.
[3] 夏明珠,劉文.兒童氣質與父母教養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新進展[J]. 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 2004,(2):65~69.
[4] 普洛明等.行為遺傳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5] Dunn,Plomin.Determinants of masternal behavior toward three-year-old siblings.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 pmental Psychology[J],1986,(4):127~137.
[6] Kirby Deater-Deckard,Stephen A. Petrill. Parent child dyadic mutuality and child behavior problems: an investigation of gene environment processes.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J] , 2004,(6):1171~1179.
[7] David Reiss. Social Processes and Genetic Influences in Child Development: Novel Uses of Twin and Adoption Designs. 心理學報 [J] 2008,(10):1099~1105.
[8] 張麗華,宋芳.人格研究中的行為遺傳學取向的發展[J]. 心理與行為研究,2006,4(1):61~65.
[9] 張坤,李其維.遺傳與環境的相關及交互作用分析[J].心理學探新,2006,(2):13~17.
[10] 陳陳.家庭教養方式研究進程透視[J].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6):95~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