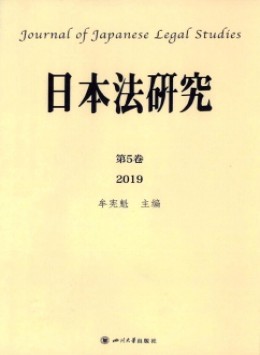刑法哲學(xué)論文精選(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誕生,需要你不斷地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編為你收集了豐富的刑法哲學(xué)論文主題范文,僅供參考,歡迎閱讀并收藏。

第1篇:刑法哲學(xué)論文范文
一、國際私法性質(zhì)的不同觀點(diǎn)
前已述及,在當(dāng)前的國際社會,各國學(xué)者對國際私法的性質(zhì)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具體來說,由于各國學(xué)者在定性時的著眼點(diǎn)不同,強(qiáng)調(diào)的方向不同,以至于有以下幾種不同觀點(diǎn):其一,國際私法是國際法,不是國內(nèi)法。其理論根據(jù)是,國際私法產(chǎn)生于國際社會,其所調(diào)整的關(guān)系是國際民商事關(guān)系,其作用在于劃分國家擴(kuò)及的范圍,其淵源主要是國際條約和國際慣例,而且國際私法本身所包含的原則、制度等其中不少是與國際公法一致的等等。此種主張實(shí)際上是把國際私法當(dāng)作調(diào)整國家與國家之間關(guān)系的法律,沒有把國際私法與國際公法嚴(yán)格區(qū)別開來,沒有意識到國際私法畢竟是“私法”性質(zhì)的法律,在本質(zhì)上與國際公法有許多不同之處。至少目前國際私法不能稱為國際法。
其二,國際私法是國內(nèi)法,不是國際法。該觀點(diǎn)認(rèn)為,每個國家都可以制定本國的國際私法,斷然否認(rèn)有一種凌駕于一切國家之上的“超國家的國際私法”的存在,而各國國際私法只是本國國內(nèi)法的一個分支。其理論根據(jù)是,國際私法調(diào)整的對象是不同國家之間的非者的自然人、法人之間的民商事關(guān)系,其主要淵源是國內(nèi)法,且主要是由一個國家的立法機(jī)關(guān)制定的,其爭議也一般是由一個國家的法院或仲裁機(jī)構(gòu)來處理,等等。基于此,該主張所指的國際法,僅僅是國際公法,似乎除了國際公法外就不存在其他具有國際性的法律了。這是一種狹義的觀點(diǎn)。
眾所周知,國際私法首先是從國內(nèi)法產(chǎn)生的,在一個很長的階段內(nèi),它的確只具有國內(nèi)法的性質(zhì),但是它沒有停留在這個階段內(nèi),它是發(fā)展的,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它的國際法成分越來越多。對于這個事實(shí),我們不能視而不見[2].故這第二種觀點(diǎn)用來解釋早期的國際私法尚可,但用來解釋現(xiàn)代社會的國際私法則有失偏頗。因?yàn)楫?dāng)前的國際私法是一種內(nèi)容復(fù)雜的法律,不應(yīng)該對它的性質(zhì)作出“非國內(nèi)法即國際法”或“非國際法即國內(nèi)法”的結(jié)論,而應(yīng)該實(shí)事求是地對它的性質(zhì)作出科學(xué)的概括。
其三,國際私法是介于國際法與國內(nèi)法之間的一種獨(dú)立的法律。該觀點(diǎn)認(rèn)為,國際私法的基本原則既有屬于國際法方面的,也有國內(nèi)法方面的;國際私法本身既涉及一國國內(nèi)的利益又涉及他國的利益;其淵源既有國內(nèi)法又有國際條約和國際慣例。因此,不能簡單地說國際私法是國際法或是國內(nèi)法,可以說國際私法既具有國際法性質(zhì)又具有國內(nèi)法性質(zhì)。該觀點(diǎn)可以說是前兩種理論的折衷,有一定的現(xiàn)實(shí)意義。但遺憾的是支持此觀點(diǎn)的學(xué)者甚少,其影響力也就顯得微乎其微。
其四,國際私法在當(dāng)前主要還是國內(nèi)法,但是隨著國際民商事交往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和國際私法統(tǒng)一化運(yùn)動的不斷推進(jìn),國際私法將逐漸增加國際法的成分或因素。國際私法的調(diào)整對象主要是發(fā)生在不同國家的自然人和法人之間的民商事關(guān)系,這是國際私法主要是國內(nèi)法的最根本的因素。
上述幾種關(guān)于國際私法性質(zhì)的主張,從歷史發(fā)展的觀點(diǎn)來看,除第四種以外均有一定的局限性,盡管其對國際私法基本理論的研究和發(fā)展均有不同程度的推動作用。
二、國際私法性質(zhì)的辯證法分析
關(guān)于國際私法的性質(zhì),筆者認(rèn)為,從歷史的角度和發(fā)展的觀點(diǎn)來分析,用哲學(xué)的術(shù)語來表達(dá),就是質(zhì)量互變規(guī)律在國際私法中的體現(xiàn)。而之所以引用質(zhì)量互變規(guī)律,是因?yàn)椤霸谏飳W(xué)中,以及在人類社會歷史中,這一規(guī)律在每一步上都被證實(shí)了”[3].質(zhì)量互變規(guī)律的內(nèi)容主要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具有一定的質(zhì)和一定的量,是質(zhì)和量的統(tǒng)一體。事物的運(yùn)動、變化和發(fā)展是通過質(zhì)變和量變表現(xiàn)出來的。量變和質(zhì)變是事物變化的兩種形式或兩種狀態(tài)。當(dāng)事物變化超出度的范圍,事物數(shù)量的變化就向事物性質(zhì)的變化轉(zhuǎn)變。量變是質(zhì)變的準(zhǔn)備,質(zhì)變是量變超過度后的必然結(jié)果;質(zhì)變鞏固著量變的成果,質(zhì)變又引起新的量變;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中,量變和質(zhì)變的表現(xiàn)形式都是豐富而復(fù)雜的。質(zhì)量互變規(guī)律揭示了事物存在與發(fā)展的最基本的狀態(tài),它對我們認(rèn)識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對國際私法性質(zhì)的科學(xué)定性,當(dāng)然也可以引用質(zhì)量互變規(guī)律來加以分析。
國際私法作為調(diào)整國際民商事關(guān)系的法律,首先是從國內(nèi)法產(chǎn)生的,在一個很長的階段內(nèi),它只側(cè)重于一國中各城市國家間或各地區(qū)間的法律沖突的研究和解決,并且認(rèn)為從理論到實(shí)踐,它的確只具有國內(nèi)法或“區(qū)際私法”的性質(zhì)。這個階段的國際私法只是處于量變階段,為以后向國際法的過渡作準(zhǔn)備。但自《法國民法典》頒布以后,法國各地方的法律得到了統(tǒng)一,尚待解決的只是國內(nèi)外的法律沖突問題,于是國際私法才真正取得了“國際”的意義[4].這時期的國際私法也具有了一定的國際法成分,應(yīng)屬于一種質(zhì)變。而根據(jù)質(zhì)量互變規(guī)律,國際私法產(chǎn)生一定成分的國際法之后,國際私法的國際法成分的不斷增加是質(zhì)變完成以后的量變階段。這將會是一個很長的階段。
在目前直至今后相當(dāng)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國際私法仍將主要是國內(nèi)法,這是因?yàn)椋浩湟唬瑖H私法的調(diào)整對象主要是發(fā)生在不同國家的自然人和法人之間的民商事關(guān)系,即使國家作為主體參與到這種民商事關(guān)系中,它所享有的權(quán)利、承擔(dān)的責(zé)任以及司法管轄等方面是與國家作為主體參與國際公法方面的活動迥然不同的。調(diào)整對象的不同是決定國際私法主要是國內(nèi)法的最根本的要素;其二,國際私法最主要的淵源仍將是國內(nèi)法,而有關(guān)的國際條約一般只約束締約國,至今并不存在約束所有國家的國際私法規(guī)范,并且某些國際條約中的公共秩序保留條款以及任意性條款的性質(zhì)可以排除條約規(guī)定的法律的適用。[5]但是能不能因此就認(rèn)為國際私法將停留在主要是國內(nèi)法這一階段長期停滯不前呢?答案當(dāng)然是否定的。根據(jù)前述哲學(xué)原理,事物發(fā)生質(zhì)變以后所引起的量變過程在時間上的延續(xù)很不相同。如微觀世界的一些量變,經(jīng)歷的時間極其短暫;而導(dǎo)致生物物種更替的變異因素的積累,則要以億年來計(jì)算。國際私法的整個發(fā)展過程中國際法成分的增加或者說從國內(nèi)法向國際法轉(zhuǎn)變的過程就是一個漫長的量變過程,這個過程將會是由最初的國內(nèi)法的不斷增多(量變)到出現(xiàn)國際法成分(質(zhì)變)到國際法成分的不斷增多(量變)及至最終過渡到國際法(質(zhì)變)。因?yàn)閲H私法越發(fā)達(dá),其國際因素就越強(qiáng)。[6]故國際私法的性質(zhì)隨著國際法成分的增加而由國內(nèi)法發(fā)展到國際法,是一個由量變到質(zhì)變的過程。問題的關(guān)鍵是要找到一個臨界點(diǎn),找到一個能科學(xué)地揭示國際私法由國內(nèi)法轉(zhuǎn)變?yōu)閲H法的轉(zhuǎn)折點(diǎn)。但在現(xiàn)有的條件下,要發(fā)現(xiàn)這個臨界點(diǎn)是相當(dāng)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們現(xiàn)在只能認(rèn)識到這一程度:國際私法現(xiàn)在主要是國內(nèi)法,但將來必定成為國際法。[7]因?yàn)槭挛镔|(zhì)變的發(fā)生決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量變的必然結(jié)果。國際私法由國內(nèi)法發(fā)展到國際法也是一個由量變到質(zhì)變的必然過程。
21世紀(jì)以來發(fā)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已證明國際私法正在逐步由國內(nèi)法向國際法過渡。這主要是由于科技的進(jìn)步使各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全球化的形勢下各國的法律正逐漸趨于一致,而且由于從事統(tǒng)一國際私法的國際組織的種類、數(shù)量日益增多,再加上國際社會的合作等使國際私法的國際法法源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在當(dāng)今國際社會中,國際的國際私法,包括國際統(tǒng)一沖突法和統(tǒng)一實(shí)體法,正在日益發(fā)展和壯大,這已是不爭的事實(shí)。[8]以歐洲聯(lián)盟國際私法為例,歐盟國際私法是由各成員國共同制定或由共同體機(jī)關(guān)的立法通過并對各成員國適用的。它所規(guī)范的對象也主要是涉及不同成員國的民商事關(guān)系。因此,在這種意義上,不妨說歐盟國際私法是廣義上的國際法。歐盟國際私法具備國際法的特征,應(yīng)該屬于國際法。但它又不是全球性的國際法,而只是適用于歐盟的區(qū)域國際法。[9]但畢竟歐洲聯(lián)盟國際私法已從國際私法的國內(nèi)法性質(zhì)發(fā)展到了區(qū)域國際法性質(zhì),為國際私法性質(zhì)的發(fā)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證。這也是量變的積累,或者說是局部性的部分質(zhì)變,為以后向國際法的過渡創(chuàng)造條件。
在理解國際私法的性質(zhì)時,也應(yīng)注意到,事物的發(fā)展并不都是一帆風(fēng)順的,在發(fā)展的過程中總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障礙。國際私法的發(fā)展也不例外。到目前為止,國際私法無疑已完成了由國內(nèi)法向兼具有國際法和國內(nèi)法性質(zhì)的轉(zhuǎn)變,但它要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國際法,尚存在兩種障礙因素:其一,統(tǒng)一規(guī)范從其通過程序來看雖帶有國際法的性質(zhì),但并沒有國際審判組織,因此即使締結(jié)了統(tǒng)一法公約,也會由于它在不同國家的司法機(jī)關(guān)適用,因而并不能保證它在適用上的統(tǒng)一性;其二,各國在沖突法領(lǐng)域雖可達(dá)成統(tǒng)一,也因它指引的實(shí)體法往往是各國的國內(nèi)法,而各國國內(nèi)法是不可能完全統(tǒng)一的;而在實(shí)體法領(lǐng)域,由于它尚不可能在所有民商法領(lǐng)域達(dá)成統(tǒng)一,它總會留有空白,這些又只能借助沖突規(guī)則確立的國內(nèi)法來解決。因而國際私法在可遇見的將來并不會完全脫離國內(nèi)法制度。但隨著人類社會的進(jìn)步,隨著趨同化進(jìn)一步發(fā)展,國際私法的國際法性質(zhì)將會逐步加強(qiáng),而趨向于以國際法為主要性質(zhì)。[1](P42)其最終的結(jié)果將會是過渡到國際法。
事物發(fā)展的質(zhì)量互變規(guī)律表明事物由量變發(fā)展到質(zhì)變是一個必然的過程。筆者相信,隨著社會的進(jìn)步,國際私法由最初的國內(nèi)法性質(zhì)發(fā)展到國際法性質(zhì)也是一個必然的結(jié)果。因?yàn)榉杀仨毞倪M(jìn)步所提出的正當(dāng)要求。一個法律制度,如果跟不上時代的需要或要求,而死死抱住上個時代的、只具有短暫意義的觀念不放,顯然是不可取的。在一個變幻不定的世界中,如果把法律視為一種永恒的工具,那么它就不可能有效地發(fā)揮作用。[10]如果國際私法停留在國內(nèi)法性質(zhì),那將等同于故步自封,國際私法將因其作用得不到充分的發(fā)揮而失去存在的意義。國際私法為了發(fā)揮其作用,就必須逐步增加其國際法成分并最終演變成國際法性質(zhì),這既是時代所需,也是符合唯物辯證法的。
三、結(jié)束語
盡管目前對國際私法的性質(zhì)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主張,但根據(jù)唯物辯證法的質(zhì)量互變規(guī)律進(jìn)行考察,其中的有些觀點(diǎn)不攻自破,或應(yīng)當(dāng)廢除,或有待修改。筆者認(rèn)為,在考察國際私法的性質(zhì)時,應(yīng)當(dāng)堅(jiān)持:
1.要從實(shí)際出發(fā)。當(dāng)今國際私法是一個內(nèi)容復(fù)雜的法律部門,其復(fù)雜性遠(yuǎn)非“法則區(qū)別說”時代所能比擬。故不能簡單地用“非此即彼”的結(jié)論對其定性,而應(yīng)當(dāng)實(shí)事求是地對它的性質(zhì)作出科學(xué)的概括。
第2篇:刑法哲學(xué)論文范文
中國期刊投稿熱線,歡迎投稿,投稿信箱1630158@163.com 所有投稿論文我們會在2個工作日之內(nèi)給予辦理審稿,并通過電子信箱通知您具體的論文審稿及發(fā)表情況,來信咨詢者當(dāng)天回信,敬請查收。本站提供專業(yè)的服務(wù)和論文寫作服務(wù),省級、國家級、核心期刊快速發(fā)表。
【摘要】折衷主義: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之融和19 世紀(jì)末,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激烈論戰(zhàn)正酣,難分伯仲。與此同時,世界范圍內(nèi)的帝國主義侵略活動也日益猖獗,這使得在國內(nèi)要有堅(jiān)強(qiáng)的后盾做支撐。
【關(guān)鍵詞】折衷主義 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之融和19 世紀(jì)末 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激烈論戰(zhàn)正酣
【本頁關(guān)鍵詞】 期刊征稿 論文投稿 省級期刊征稿
【正文】二、折衷主義: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之融和19 世紀(jì)末,客觀主義與主觀主義的激烈論戰(zhàn)正酣,難分伯仲。與此同時,世界范圍內(nèi)的帝國主義侵略活動也日益猖獗,這使得在國內(nèi)要有堅(jiān)強(qiáng)的后盾做支撐。顯然,這要求國家要有絕對的權(quán)威,要形成統(tǒng)一的國家集權(quán)。作為維護(hù)帝國主義統(tǒng)治工具的刑法理論,國家當(dāng)然不容許長期存在的對立狀態(tài),于是就采取了一定程度的行政干預(yù)的辦法,使學(xué)派之間的激烈對立調(diào)和統(tǒng)一起來,以便更好地為帝國主義的對外瘋狂侵略和對內(nèi)高壓統(tǒng)治服務(wù)。于是,到20 世紀(jì)20 - 30 年代,兩派開始有了緩和的跡象。同時,面對紛繁復(fù)雜的社會問題,論戰(zhàn)雙方也都逐漸注意到了自身理論的缺點(diǎn)和對方的優(yōu)點(diǎn)。20 世紀(jì)40 - 50 年代,開始了影響深遠(yuǎn)的第三次技術(shù)革命,自然科學(xué)向著深度和廣度兩個方向飛速發(fā)展。信息論、系統(tǒng)論、控制論等現(xiàn)代方法的出現(xiàn),帶來了認(rèn)識論與方法論上的革命,對哲學(xué)、自然科學(xué)與社會科學(xué)研究影響巨大。在刑法學(xué)領(lǐng)域,系統(tǒng)論和信息論迅速地取代了傳統(tǒng)的哲學(xué)方法而一躍成為占主導(dǎo)地位的方法論,這無疑有利地推動了學(xué)派之爭的調(diào)和理論的形成。到50 年代以后,學(xué)派之爭開始消停,折衷主義走向興盛。兩大陣營彼此站在各自的立場之上,吸收對方的合理因素來發(fā)展和充實(shí)自己的理論。就意志自由問題,折衷主義形成了相對意志自由論的觀點(diǎn)。一方面承認(rèn)人的意志是被素質(zhì)、環(huán)境等因素決定的,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完全被動和無能為力的,它具有自己的能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因此,在具體情況下,如果行為人有選擇的自由意志,即既可為犯罪行為,又可不為犯罪行為,卻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犯罪行為,那理所當(dāng)然應(yīng)受刑法譴責(zé);但如果行為時缺乏自由選擇的意志,即只能實(shí)施犯罪行為而不能選擇其他,此時,刑法則沒有譴責(zé)該行為的理由。“從理論脈絡(luò)出發(fā),相對意志自由論可以視為意志自由論和意志決定論的折衷和調(diào)和,它一方面擺脫了意志決定論的固有缺陷,跳出了機(jī)械因果決定鏈條的理論樊籬,另一方面又吸納了意志自由論的理論養(yǎng)分, 得到了道義倫理的有力支撐, 可以說相對意志自由理論發(fā)展到今已經(jīng)成為這一哲學(xué)領(lǐng)域最為有力的學(xué)說。”折衷主義就犯罪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及責(zé)任問題,提出了諸多思想,形成了多種學(xué)說,但具有較大影響的主要有后期舊派(后期古典學(xué)派)的規(guī)范責(zé)任論和新派的人格責(zé)任論和新社會防衛(wèi)論。(一)后期舊派:規(guī)范責(zé)任論規(guī)范責(zé)任論由德國學(xué)者麥耶首先提及,自20 世紀(jì)20年代由德國學(xué)者Frank首創(chuàng),后經(jīng)Goldschmidt、Freudenthal加以發(fā)展,目前在德國、日本居于支配地位的責(zé)任理論。該論的形成肇始于19 世紀(jì)末新康德主義法學(xué)①對后期舊派的影響。新康德主義以價(jià)值和事實(shí)的嚴(yán)格區(qū)分為前提,試圖建立與自然科學(xué)不同的、獨(dú)具特色的人文科學(xué)和社會科學(xué)的方法論基礎(chǔ)。它與實(shí)證主義的因果的、機(jī)械的考察方法相反,通過導(dǎo)入價(jià)值、評價(jià)、規(guī)范等考察方法,以圖恢復(fù)人文科學(xué)的人的、文化的本來特征。后期舊派以新康德主義價(jià)值哲學(xué)為基礎(chǔ),將價(jià)值評判納入法律體系,認(rèn)為法律規(guī)范是社會公意和價(jià)值觀念的體現(xiàn),是制約和評判人們行為的準(zhǔn)繩。而后又立于道義責(zé)任論的立場之上,并對其進(jìn)行了修正,提出刑事責(zé)任的根據(jù)在于行為人違反了法律根據(jù)普通理性人設(shè)立的基本規(guī)范要求,即法規(guī)范對行為人實(shí)施合法行為的合理期待。因此,只有行為人違反遵守法律規(guī)范的義務(wù),在具有避免實(shí)施違法行為的可能性的情況下,作出相反的意思決定而實(shí)施了違法行為,這才具備了應(yīng)受責(zé)任的充足條件。可見在責(zé)任的三要素(心理事實(shí)、規(guī)范評價(jià)和期待可能性)中,真正決定責(zé)任界限的是期待可能性這一規(guī)范要素。這有利于限制責(zé)任的擴(kuò)張,間接地制約了犯罪與刑事處罰的界限和范圍,體現(xiàn)了刑法的謙抑性。
【文章來源】/Downloadshow.asp?id=11
【本站說明】中國期刊投稿熱線:專業(yè)致力于期刊論文寫作和發(fā)表服務(wù)。提供畢業(yè)論文、學(xué)術(shù)論文的寫作發(fā)表服務(wù);省級、國家級、核心期刊以及寫作輔導(dǎo)。 “以信譽(yù)求生存 以效率求發(fā)展”。愿本站真誠、快捷、優(yōu)質(zhì)的服務(wù),為您的學(xué)習(xí)、工作提供便利條件!自05年建立以來已經(jīng)為上千客戶提供了、論文寫作方面的服務(wù),同時建立了自己的網(wǎng)絡(luò)信譽(yù)體系,我們將會繼續(xù)把信譽(yù)、效率、發(fā)展放在首位,為您提供更完善的服務(wù)。
聯(lián)系電話: 13081601539
客服編輯QQ:860280178
論文投稿電子郵件: 1630158@163.com
投稿郵件標(biāo)題格式:投稿刊物名 論文題目
如:《現(xiàn)代商業(yè)》 論我國金融改革及其未來發(fā)展
聲明:
本站期刊絕對正規(guī)合法
并帶雙刊號(CN,ISSN),保證讓您輕松晉升
第3篇:刑法哲學(xué)論文范文
[論文摘要]刑法因果關(guān)系是一個十分具體的司法實(shí)踐問題,也是理論界爭議最大的問題。刑法界的學(xué)者和專家圍繞這一問題進(jìn)行了深入的研究,到目前為止仍未形成統(tǒng)一的認(rèn)識。刑法因果關(guān)系雖有它的哲學(xué)基礎(chǔ),但它畢竟是一個法律問題,有其自身的特征。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各形成了自己關(guān)于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理論學(xué)說,我國當(dāng)然也不例外。其實(shí),刑法因果關(guān)系僅是危害行為與危害結(jié)果間的一種聯(lián)系與刑事責(zé)任沒有關(guān)系。但這如何它與犯罪構(gòu)成要件的關(guān)系,它在犯罪論體系中的地位又怎樣呢?很少人論述。在不作為犯罪、疫學(xué)上的犯罪中刑法因果關(guān)系又各有其特點(diǎn)。
一、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概念
因果關(guān)系本來是一個哲學(xué)上的概念,后來被引入刑法中。哲學(xué)上的因果關(guān)系是一種引起和被引起的關(guān)系。引起別的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現(xiàn)象是原因,被引起的現(xiàn)象則是結(jié)果,即外因與結(jié)果之間的關(guān)系。具體到刑法中是指危害結(jié)果的產(chǎn)生首先在于客體事物內(nèi)部具有在這種外在力量作用下產(chǎn)生有害變化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是一種抽象可能性,本來事物存在的實(shí)在可能性是朝著有利于社會的方向發(fā)展的,由于外部危害行為的干擾,影響原來實(shí)在可能性的繼續(xù)發(fā)展,而是原來處于抽象可能性位置的危害可能性變成了新的實(shí)在可能性,成為事物發(fā)展新的必然趨勢,并在一定條件下轉(zhuǎn)變成現(xiàn)實(shí)性,就產(chǎn)生了危害結(jié)果。
二、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特征
(一)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客觀性
辯證唯物主義認(rèn)為,因果關(guān)系作為客觀現(xiàn)象之間引起與被引起的關(guān)系,是客觀存在的,并不以人們主觀是否認(rèn)識到為準(zhǔn)。當(dāng)發(fā)生了一個刑事案件時,我們首先要從客觀性這一點(diǎn)著手,看危害結(jié)果的發(fā)生是否由犯罪嫌疑人的危害行為造成,如果之間存在引起和被引起的關(guān)系,即存在刑法因果關(guān)系,我們再去考慮犯罪構(gòu)成要件,因?yàn)橐粋€人只對自己的行為負(fù)責(zé),而不對他人的行為負(fù)責(zé)。如果兩者之間不存在因果關(guān)系,案件到此為止就不必再去考慮其它。堅(jiān)持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客觀性,可以少走彎路,為迅速的解決刑事責(zé)任奠定基礎(chǔ)。
(二)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相對性
原因和結(jié)果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在辯證唯物主義因果論看來,引起一定現(xiàn)象發(fā)生的現(xiàn)象是原因;被一定現(xiàn)象引起的現(xiàn)象是結(jié)果。兩者對立統(tǒng)一于因果關(guān)系之中。由于世界是普遍聯(lián)系的,原因在一個案件中是原因,但在另一個案件中卻是結(jié)果,因此要靈活運(yùn)用。理解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相對性要注意以下兩點(diǎn):1.刑法因果關(guān)系中的原因是指危害社會的行為。2.作為刑法因果關(guān)系中的結(jié)果,是指法律所要求的已經(jīng)造成的、能被查明和確定的現(xiàn)象。在行為犯、犯罪的預(yù)備、未遂和中止等犯罪的未完成形態(tài)中一般不存在解決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問題。
(三)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時間序列性
從唯物辨證主義的角度出發(fā),原因和結(jié)果是有先后順序的,原因必定在先結(jié)果只能在后,順序不能顛倒。因此,在刑事案件中,我們只能從危害結(jié)果發(fā)生以前的危害行為中去查找原因。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節(jié)省更多的時間,因?yàn)橐蚬P(guān)系非常復(fù)雜,有一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果多因,我們可以根據(jù)它的這個特征去找出所有的原因和結(jié)果,避免了原因和結(jié)果的混亂。
(四)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在這里探討的只是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必然性與偶然性,而不是指必然因果關(guān)系和偶然因果關(guān)系,因此我們必須把這兩個概念區(qū)別開來。其實(shí),刑法因果關(guān)系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統(tǒng)一。在西方哲學(xué)史上,黑格爾第一個辨證的解決了必然性與偶然性之間的關(guān)系。恩格斯把黑格爾的觀點(diǎn)歸納為這樣一個命題:“偶然的東西正因?yàn)槭桥既坏?所以有某種根據(jù),而且正因?yàn)槭桥既坏?所以也就沒有根據(jù);偶然的東西是必然的,必然性自己規(guī)定自己為偶然性,而另一方面,這種偶然性又寧可說是絕對的必然性。”必然性與偶然性并不是事物發(fā)展的兩個互相對立的過程,而是事物發(fā)展過程中互相矛盾又相互轉(zhuǎn)化的兩個方面。“必然性通過偶然性為自己開辟道路,偶然性背后隱藏著必然性。”危害結(jié)果的發(fā)生是偶然的,但其客體內(nèi)部有一種向不利方向發(fā)展的抽象可能性,這種抽象可能性又是必然的,必然通過偶然性表現(xiàn)出來。
三、刑法因果關(guān)系與刑事責(zé)任
我國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刑法因果關(guān)系是刑事責(zé)任的客觀基礎(chǔ)。” 這也是刑法學(xué)界的通說。形成該觀點(diǎn)的原因是許多學(xué)者把刑法因果關(guān)系當(dāng)作犯罪構(gòu)成的一個客觀要件了,又因?yàn)樾淌仑?zé)任的根據(jù)是犯罪構(gòu)成,當(dāng)然就得出了上面的結(jié)論了。我認(rèn)為,刑法因果關(guān)系只是一種聯(lián)系,危害結(jié)果的發(fā)生是由于原因使客體內(nèi)部的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變化。因此,刑法中的因果關(guān)系與刑事責(zé)任沒有關(guān)系,它只我們解決刑事責(zé)任時的一種思維方式。在剛開始分析案例時,只要分析原因和結(jié)果之間是否有引起與被引起的關(guān)系就夠了,不要考慮態(tài)度的因果關(guān)系。對于介入因素的問題,借鑒英美法系的近因說的觀點(diǎn)就可以了。接下來要根據(jù)犯罪構(gòu)成理論來分析,看結(jié)果是否是危害社會的結(jié)果,是否是刑法所禁止的結(jié)果,主觀上有無故意、過失等問題全面分析。
關(guān)于刑法因果關(guān)系與犯罪論體系的關(guān)系我可以從以下幾點(diǎn)分析。
首先從我國的犯罪構(gòu)成理論來分析。在目前的情況,由于“必然說”和“偶然說”遭到不少人的批評,已經(jīng)沒有多少人堅(jiān)持了。但雙層因果關(guān)系說卻得到了許多人的人的支持,可能是受英美法系因果關(guān)系學(xué)說的影響。但雙層因果關(guān)系說認(rèn)為因果關(guān)系是結(jié)果犯的一個必備構(gòu)成要件,是行為犯、危險(xiǎn)犯、未完成形態(tài)犯罪的選擇要件,而且是一個客觀要件。但在分析法律因果關(guān)系時卻又分析了主觀方面,一個因果關(guān)系怎么既成了犯罪客觀方面,又成了犯罪的主觀方面,與因果關(guān)系的客觀性自相矛盾。因此我們必須重新考慮因果關(guān)系與犯罪論體系的關(guān)系。
如果把刑法中的因果關(guān)系僅看作是一種引起與被引起的關(guān)系,即起一種橋梁作用,不屬于犯罪構(gòu)成要件,問題就容易解決了。案件結(jié)果發(fā)生以后,看哪些是危害行為引起的就可以了,接下來,再根據(jù)犯罪構(gòu)成理論決定刑事責(zé)任的承擔(dān)問題。
雙層因果關(guān)系是受英美法系的影響,但英美法系是實(shí)行判例法的國家,注重實(shí)用,而我們國家講究的是理論的體系化、系統(tǒng)化,各個理論要自圓其說。如果我們真要使因果關(guān)系融入整個犯罪論體系中,我們可以借鑒大陸法系的犯罪論。即構(gòu)成要件該當(dāng)性、違法性、有責(zé)性。在大陸法系中,刑法因果關(guān)系是放在構(gòu)成要件的該當(dāng)性中的,目前理論界的“通說”是相當(dāng)因果關(guān)系說,而該說中既有主觀因素又有客觀因素,避免了雙層因果關(guān)系說中的矛盾,而且通過違法性、有責(zé)性的判斷可以排除一些不應(yīng)處罰的行為。不像我國構(gòu)成要件中主觀方面、客觀方面、主體、客體那樣截然分開,有時會自相矛盾。但是要放棄我國的犯罪構(gòu)成理論去接受大陸法系的犯罪論也許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認(rèn)為因果關(guān)系僅是一種聯(lián)系的觀點(diǎn)是可行的。
參考文獻(xiàn)
[1]趙秉志主編,《犯罪總論問題探索》,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頁
[2]王作富主編,《刑法》,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
第4篇:刑法哲學(xué)論文范文
[論文關(guān)鍵詞]期待可能性;可行性;判斷標(biāo)準(zhǔn);形式理性
新時期我國刑法學(xué)理論得到繁榮發(fā)展,積極引進(jìn)和借鑒外國刑法理論的同時,不斷豐富和完善著我國刑法學(xué)理論體系。外國刑法學(xué)理論尤其是德日刑法理論的引入,對于開拓學(xué)科視野,客觀的認(rèn)識和解決當(dāng)前我國刑法理論和立法、司法實(shí)踐中的問題提供了來源性的支持。然而,每一種刑法理論的引入和借鑒都必須立足于我國的本土實(shí)踐和實(shí)際需要,期待可能性理論作為德日刑法理論中的重要內(nèi)容,一般放在犯罪論中“有責(zé)性”的范疇內(nèi)進(jìn)行探討,對于該理論的引入,很多學(xué)者持積極肯定的態(tài)度。筆者認(rèn)為,需要在對該理論全面認(rèn)識深化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當(dāng)前我國實(shí)際,
一、期待可能性的回顧與解讀
期待可能性,亦稱適法行為的可能性,始于德國帝國法院19世紀(jì)末關(guān)于“癖馬案”的判例,作為規(guī)范責(zé)任論的核心內(nèi)容,期待可能性理論發(fā)源于德國,但在日本才得到了實(shí)際意義的發(fā)展,同一理論在兩個國家理論及實(shí)踐的情況是截然不同的,期待可能性在德國司法實(shí)踐中已經(jīng)基本不被適用,并且受到德國刑法理論界的冷遇。而在日本,雖然在司法實(shí)踐中的作用相對較弱,但在日本國內(nèi)的刑法理論中期待可能性理論卻得到了廣泛的研究與承認(rèn)。正如日本學(xué)者山中敬一所說:“現(xiàn)在雖然被認(rèn)為‘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實(shí)踐的作用相對低下’,但在學(xué)說中,位于規(guī)范的責(zé)任論的核心,給予作為阻卻責(zé)任論的理論以支柱的作用,并且認(rèn)為期待可能性不存在是超法規(guī)的阻卻責(zé)任事由,是壓倒性的通說”。關(guān)于期待可能性在責(zé)任論中的地位,學(xué)者有著不同觀點(diǎn),總結(jié)起來大概有三種學(xué)說:第一種學(xué)說認(rèn)為期待可能性屬于責(zé)任階層中的例外責(zé)任要素,也就是消極的責(zé)任要素。第二種學(xué)說認(rèn)為“由于故意與過失是責(zé)任的種類或形式,如果缺乏期待可能性,就沒有故意責(zé)任與過失責(zé)任”。第三種學(xué)說認(rèn)為期待可能性是能與故意.過失和責(zé)任能力相并列的責(zé)任要素。關(guān)于期待可能性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又有三種不同學(xué)說:一是行為人標(biāo)準(zhǔn)說,也就是根據(jù)當(dāng)時行為人的能力為判斷標(biāo)準(zhǔn),二是平均人標(biāo)準(zhǔn)說,也就是以一般人,平均人的標(biāo)準(zhǔn)判斷是否存在實(shí)施適法行為的可能性,三是國家標(biāo)準(zhǔn)說,即根據(jù)國家秩序或法規(guī)范對秩序的要求作為判斷標(biāo)準(zhǔn)。
二、引入的必要性分析
(一)期待可能性引入的“可能”
關(guān)于期待可能性的引入,學(xué)者也是從不同的路徑和視角進(jìn)行了闡釋,從哲學(xué)的高度對期待可能性所蘊(yùn)含的哲學(xué)基礎(chǔ)的認(rèn)可,從實(shí)質(zhì)理性對形式理性的補(bǔ)充,到意志自由的討論。到也有從犯罪論體系的角度闡述了期待可能性理論引入對我國犯罪論體系的影響和相應(yīng)的修正。也有很多學(xué)者對該理論的引入是從期待可能性的歷史起源和發(fā)展,以及在德日犯罪論體系中的定位和作用來進(jìn)行分析的。在他們看來,期待可能性理論的引入,“會使我國刑法理論中的許多問題得到合理解決,比如緊急避險(xiǎn)行為及執(zhí)行上級命令的行為”。認(rèn)為期待可能性理論同時也契合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和思想,也是對人性的固有弱點(diǎn)的承認(rèn)和寬宥。還有的學(xué)者從個案正義與一般正義的平衡上為期待可能性理論引入找尋法理依據(jù),認(rèn)為期待可能性理論本身就是在事實(shí)和規(guī)范、普遍正義和一般正義之間尋求一種妥當(dāng)性的平衡。
然而,任何一種理論的引入,都必須結(jié)合本國的現(xiàn)實(shí)場景,都必須從宏觀的角度去討論該理論的引入對我國現(xiàn)行刑法理論的影響并進(jìn)行客觀的可行性評估,都必須深刻認(rèn)識該理論產(chǎn)生的的時間背景和現(xiàn)實(shí)價(jià)值。
(二)期待可能性引入之我見
1.刑法理論的合理性依附于其產(chǎn)生的時代和地域背景。期待可能性產(chǎn)生于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快速發(fā)展的時期,當(dāng)時的資本主義世界過分注重對利潤及生產(chǎn)力擴(kuò)大的追求,忽視對于勞動者的關(guān)懷和保護(hù),勞動者處于弱勢群體的地位,出于其相對脆弱的法律地位因而做出的“癖馬案”中有利于馬車夫的判決,也就可以理解和接受。二戰(zhàn)之后,隨著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和普通勞動者福利待遇的提高使得該理論適用的價(jià)值大大降低。加之風(fēng)險(xiǎn)社會的形成,使得刑法的關(guān)注焦點(diǎn)向日常的預(yù)防和管理上傾斜,強(qiáng)調(diào)對危險(xiǎn)的預(yù)防成為當(dāng)代刑法理論的發(fā)展趨勢與特征。在充滿風(fēng)險(xiǎn)和社會緊密聯(lián)系之下,以往的普通犯罪行為在當(dāng)代都可能引起極為嚴(yán)重的后果。還是以“癖馬案”為例,設(shè)想如果是公共汽車司機(jī)駕駛一輛剎車有問題的客車,公司因追求利益而勒令該司機(jī)駕駛,某日因剎車失靈致使多名乘客傷亡,那么是不是也應(yīng)當(dāng)排除司機(jī)的責(zé)任性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2.期待可能性理論爭議點(diǎn)太多,而且其適用會減弱弱刑法一般預(yù)防的效果。由于期待可能性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體系定位都存在著很大的模糊性和極大地爭議性,僅判斷標(biāo)準(zhǔn)就有三種主要不同的學(xué)說。該理論在德國逐漸弱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該理論可能會導(dǎo)致司法適用上的恣意,最終導(dǎo)致國家刑罰權(quán)的濫用,不利于保障人權(quán)。德國學(xué)者耶塞克教授認(rèn)為:“刑法在責(zé)任領(lǐng)域需要標(biāo)準(zhǔn),這些標(biāo)準(zhǔn)雖然應(yīng)當(dāng)包含對意志形成的評價(jià),但必須被形式化,并從法律上加以規(guī)定。不可期待性這一超法規(guī)免責(zé)事由,無論從主觀上還是從客觀上加以理解,均會削弱刑法的一般預(yù)防效果”。即使在該理論接受較為完全的日本,在司法適用上都顯得十分謹(jǐn)慎,期待可能性的判例僅僅出現(xiàn)在日本下級法院當(dāng)中,大審院和最高法院還沒有判例出現(xiàn)過。
3.期待可能性在我國的刑法及司法解釋中已有體現(xiàn)。我國刑法中的防衛(wèi)過當(dāng)體現(xiàn)了期待可能性的思想。由于防衛(wèi)行為本身就是對不法侵害的一種防護(hù)措施,如果防衛(wèi)人的法益受到緊迫的危險(xiǎn)或侵害,在心理極度緊張焦慮的情形下,很難準(zhǔn)確把握制止不法侵害所應(yīng)實(shí)施的必要防衛(wèi)行為的強(qiáng)度,所以刑法容許一定范圍內(nèi)超過限度的防衛(wèi)行為,只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才應(yīng)當(dāng)負(fù)刑事責(zé)任,但也是規(guī)定了應(yīng)當(dāng)減輕或免除處罰。緊急避險(xiǎn)也體現(xiàn)了該思想,出于人性趨利避害的本能,在面臨緊迫危險(xiǎn)時,刑法不能期待行為人不保護(hù)自己的利益。除此之外還有我國刑法總則中關(guān)于脅從犯的相關(guān)規(guī)定。脅從犯是被脅迫參加犯罪的,也就是其參加犯罪時受到了外力和精神上的強(qiáng)制,雖然對自身行為性質(zhì)有著清楚的認(rèn)識,但也不得不為之,刑法規(guī)定應(yīng)當(dāng)按照犯罪情節(jié)減輕處罰或免除處罰。這也是對行為人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脅時實(shí)施危害他人和社會行為的理解和包容,也正是期待可能性理論思想的一種體現(xiàn)。另外刑法分則中第134條強(qiáng)令違章作業(yè)罪中關(guān)于犯罪主體的規(guī)定,把主體限定為強(qiáng)令違章作業(yè)的人,而非作業(yè)工人。司法解釋中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維護(hù)農(nóng)村穩(wěn)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jì)要》中,對于迫于生活困難、生活確實(shí)難以為繼,出賣親生子女和收養(yǎng)子女的,可不作為犯罪處理。
4.期待可能性理論缺乏形式理性的精神,而且過分強(qiáng)調(diào)個案正義。由于期待可能性判斷標(biāo)準(zhǔn)的混亂,根本不可能把期待可能性在刑法上予以類型化的表述和說明,其本身就是一種游離于情與法邊緣的理論,表面上似乎彰顯了對人性的關(guān)懷,但實(shí)際上與刑法的價(jià)值立場是背離的,“期待可能性只是更大膽、甚至冒險(xiǎn)式地邁進(jìn)了一步,認(rèn)為在非緊急情況下,可以犧牲重大公共利益,保護(hù)較小的利益”。何況期待可能性與罪行法定原則之間本身就具有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在大陸法系的犯罪階層式判斷中,期待可能性作為超法規(guī)責(zé)任阻卻事由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對于我國傳統(tǒng)平面耦合式刑法理論中的“責(zé)任”與大陸刑法學(xué)中的“有責(zé)性”完全不是一回事。如果說引進(jìn)該理論,其作用的發(fā)揮相當(dāng)大程度上依賴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如何限制司法權(quán)的濫用和把這樣一個超法規(guī)的事由植入我國現(xiàn)行犯罪論體系,實(shí)在是成本太高,而且個人認(rèn)為效果也會差強(qiáng)人意。對該理論能夠最大程度實(shí)現(xiàn)個案正義的觀點(diǎn),實(shí)際上是一種危險(xiǎn)的理念,即公共利益讓位于個人主義的思想。就刑法而言,把安定性價(jià)值作為刑法價(jià)值理念的首位價(jià)值取向,不僅僅是罪行法定的要求,更是對當(dāng)前我國形式理性傳統(tǒng)的一種有力的更正。當(dāng)前中國迫切需要的不是個別正義的過度追捧,而是普遍法律信仰的確立和罪行法定原則的嚴(yán)格遵循,這也是刑法安定性與明確性的必然要求。
第5篇:刑法哲學(xué)論文范文
〔關(guān)鍵詞〕 作為義務(wù),法律義務(wù),道德義務(wù),區(qū)判標(biāo)準(zhǔn),義務(wù)學(xué)說
〔中圖分類號〕B546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2)03-0125-04
法律與道德的關(guān)系問題,誠可謂法學(xué)論域中的永恒話題,歷經(jīng)了由古昔的水融至近現(xiàn)代截然分野的嬗遞過程。法律與道德的分途肇端于康德哲學(xué),在康德看來,“法僅僅涉及行為,道德僅僅涉及信念” 〔1 〕 (P458 ),自其以還,近現(xiàn)代各法學(xué)流派幾乎都對兩者關(guān)系表現(xiàn)出極大的學(xué)術(shù)熱忱,均試圖在法哲學(xué)層面提出二者分際的宏觀標(biāo)準(zhǔn)。而在刑法學(xué)領(lǐng)域,嚴(yán)格界分法律與道德的則當(dāng)首推被譽(yù)為“近代刑法學(xué)之父”的費(fèi)爾巴哈。他指出,在法的領(lǐng)域中,人只能作為自然的存在者受自然因果律的支配,在道德領(lǐng)域中,人作為理性的存在者是自由的,是一種先驗(yàn)的、道德的自由。〔2 〕 (P90 )不難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法規(guī)范與道德規(guī)范之區(qū)判,無論是法哲學(xué)家抑或是部門法學(xué)家均未找到可通貫法學(xué)理論與實(shí)務(wù)踐行之判準(zhǔn)。在刑法論域內(nèi),有關(guān)法律與道德的關(guān)系問題則聚焦于不作為犯之作為義務(wù)問題。本文便擬從不作為犯之作為義務(wù)視角,立基于我國的實(shí)定法規(guī)范,從中尋究區(qū)辨法律義務(wù)與道德義務(wù)之標(biāo)準(zhǔn),進(jìn)而為公民的權(quán)利和自由劃定界域。
一、作為義務(wù)的性質(zhì)判定
作為義務(wù)問題歷來皆為不作為犯理論中的核心性論題,而作為義務(wù)的定性判斷則是探究作為義務(wù)問題的邏輯始點(diǎn),若對其定性錯誤勢必導(dǎo)致整個作為義務(wù)理論體系的悖謬,故此,有必要首先對其性質(zhì)作出準(zhǔn)確的判斷分析。有關(guān)不作為犯作為義務(wù)的性質(zhì),中外刑法理論的通行見解是,作為義務(wù)必須是法律性質(zhì)的義務(wù)而不能是純粹的道德義務(wù)。至于作為義務(wù)的更具體性質(zhì),即它到底是刑事義務(wù)還是民事、行政等法律義務(wù),抑或兼而有之?對此,研究者們通常循經(jīng)此般邏輯理路證成:違反道德義務(wù)擔(dān)負(fù)道德責(zé)任,違反法律義務(wù)承擔(dān)法律責(zé)任。不過,不同性質(zhì)的法律義務(wù)對應(yīng)著性質(zhì)迥異的法律責(zé)任,違反民事義務(wù)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違反行政義務(wù)承擔(dān)行政責(zé)任,違反刑事義務(wù)則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不作為犯罪因系犯罪,其法律后果是刑事責(zé)任,故與刑事責(zé)任相對應(yīng)的作為義務(wù)也就無疑僅限于刑事法律義務(wù)了。〔3 〕 (P139 )
上述推理看似言之鑿鑿、無懈可擊,但實(shí)則似是而非。違反純粹的道德義務(wù)僅承擔(dān)道德責(zé)任,違反法律義務(wù)須承擔(dān)法律責(zé)任,這無可厚非,但若認(rèn)為不作為犯罪因最終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便斷定其作為義務(wù)為刑事法律義務(wù),此等推論就未免過于武斷。因?yàn)椋袚?dān)刑事責(zé)任的唯一條件是犯罪,亦即惟有犯罪方得違反刑事義務(wù),故刑事義務(wù)之內(nèi)容就當(dāng)是“禁止實(shí)施犯罪行為之義務(wù)”,而眾所共知,作為義務(wù)乃是“命令義務(wù)主體為特定行為之義務(wù)”。可見,作為義務(wù)與刑事義務(wù)在內(nèi)容上迥然有別。再者,若把作為義務(wù)定性為刑事義務(wù),將導(dǎo)致不履行作為義務(wù)本身就構(gòu)成犯罪,如此不作為犯的成立條件僅需作為義務(wù)一要件即可而無需其他要件,或者導(dǎo)致不作為犯罪內(nèi)部還包含一個犯罪行為,這顯然有悖事實(shí)。事實(shí)上,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wù)并非刑事義務(wù)還可從刑法對純正不作為犯的明文規(guī)定中獲得驗(yàn)證,如遺棄罪、拒不執(zhí)行判決裁定罪、拒不支付勞動報(bào)酬罪等罪的作為義務(wù)均無一例外的為刑法之外的其他部門法義務(wù),我們無從找尋作為義務(wù)為刑事義務(wù)之適例。可見,將作為義務(wù)斷定為刑事法律義務(wù),實(shí)質(zhì)是將作為不作為犯成立條件之一的作為義務(wù)與不作為犯作為行為整體所違反的刑事法律義務(wù)并為一談。除卻刑事法律義務(wù)后,作為義務(wù)便只能是刑事義務(wù)之外的其他部門法義務(wù)或是道德、宗教等非法律性質(zhì)的義務(wù)。有關(guān)作為義務(wù)可否為道德、宗教等非法律性質(zhì)義務(wù)的問題,筆者贊同通行之論見,即不作為犯之作為義務(wù)僅限于法律性質(zhì)的義務(wù),主要理由在于:刑法的保障法地位決定了它只有在民事、行政等法律制裁措施不足以抗制相關(guān)違法行為時方才發(fā)動,以是但凡犯罪無不以違反其它部門法為前提,而純粹違反道德、宗教等非法律性質(zhì)義務(wù)的行為連其他部門法責(zé)任都無需承擔(dān),更無由要求其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了。
綜上所析,不作為犯之作為義務(wù)在性質(zhì)上只能是刑事義務(wù)以外的其他部門法如民法、行政法和訴訟法等性質(zhì)的義務(wù),也不含道德、宗教等非法律性質(zhì)的義務(wù)。而在對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wù)準(zhǔn)確定性后,需要進(jìn)一步做的是探析具法律性質(zhì)的作為義務(wù)與純粹道德義務(wù)之法規(guī)范區(qū)辨標(biāo)準(zhǔn)。
二、實(shí)定法范域內(nèi)的法律義務(wù)與道德義務(wù)判準(zhǔn)
(一)法規(guī)范與道德規(guī)范區(qū)辨之法哲學(xué)掠影。在法哲學(xué)領(lǐng)域,論及法規(guī)范與道德規(guī)范之聯(lián)系與區(qū)別時,法學(xué)家們往往從道德的價(jià)值等級體系中分離出兩類要求及原則:“第一類是社會有序化之基本要求,它們對一個有組織的社會為有效地履行必須擔(dān)負(fù)的任務(wù)來說,被視為是必不可少的或極為可欲的。第二類道德規(guī)范是那些能提升生活質(zhì)量和加強(qiáng)人與人之間聯(lián)系的原則,但這些原則之要求遠(yuǎn)遠(yuǎn)超出了維持社會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要求。那些被認(rèn)為是社會交往所必需而基本的道德原則,在任何社會都被賦予了極大的強(qiáng)制性。該類道德原則的強(qiáng)制性是通過將其上升為法律規(guī)范而變現(xiàn)”,并指出,“任何被用來保護(hù)法律權(quán)利的強(qiáng)制措施均無力適用于純粹的道德要求的”。〔4 〕 (P391-392 )據(jù)此引申出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或是道德的底線之論斷,至于該最低限度或底線的具體法規(guī)范標(biāo)準(zhǔn)為何,在法哲學(xué)家們的宏大敘事中并未給出明晰的答案。有關(guān)道德規(guī)范與法規(guī)范界分的困難及重要意義,德國著名法學(xué)家耶林曾感喟:“法律與道德的關(guān)系問題是法學(xué)中的好望角;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夠征服其中的危險(xiǎn),就再無遭受滅頂之災(zāi)的風(fēng)險(xiǎn)了。” 〔5 〕 (P21 )
(二)“法律性質(zhì)的義務(wù)”之刑法論域歧見。有關(guān)作為義務(wù)之性質(zhì),雖然中外刑法學(xué)者均認(rèn)為,作為義務(wù)僅限于法律上的義務(wù)或法律性質(zhì)的義務(wù),但對于何謂“法律上(或法律性質(zhì))的義務(wù)”則無論在理論界還是司法實(shí)務(wù)界都存在不同的理解。例如,在日本,盡管理論和判例均認(rèn)同,不作為犯之作為義務(wù)僅限于法律義務(wù),但對其來源卻多將習(xí)慣、公序良俗、條理等的要求涵括其中;在德國,對其刑法典第13條所規(guī)定的“依法必須保證結(jié)果不發(fā)生的義務(wù)”,雖認(rèn)為須是法律所承認(rèn)的避免危害結(jié)果發(fā)生之義務(wù),因而排除道德義務(wù)作為刑事責(zé)任直接基礎(chǔ)之可能性,〔6 〕 (P745 )但仍認(rèn)為,不以明文的法律規(guī)定為限,還包括一般的法律原則。〔7 〕 (P133 )我國臺灣地區(qū)最高法院就其刑法典第15條所規(guī)定的“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wù)”也藉判例釋義:不作為犯罪,須以行為者于法律上負(fù)作為義務(wù)為前提,該作為義務(wù),雖不局限于明文之規(guī)定,要必以法之精神考察擔(dān)負(fù)此義務(wù)時,始能令其擔(dān)負(fù)刑責(zé)。我國臺灣學(xué)者林山田教授就法院的此等釋義提出了批評,指陳,“就法之精神考察擔(dān)負(fù)此義務(wù)”,亦屬法律之作為義務(wù)見解,極易使人誤以為基于倫理道德、宗教等所要求之防止義務(wù),或就公序良俗所認(rèn)定之防止義務(wù),均屬基于法之精神考察,而具有法律之防止義務(wù),……有導(dǎo)致不當(dāng)擴(kuò)張作為義務(wù)之弊,顯有違于罪刑法定原則。〔8 〕 (P1297-298 )我國刑法學(xué)界也有論者主張,在特殊場合,社會公德和公共秩序要求履行的義務(wù)也可以成為作為義務(wù)的來源。〔9 〕 (P168 )故如何嚴(yán)格界分法律性質(zhì)的義務(wù)與純粹的道德義務(wù)就成為不作為犯理論無法回避的問題,否則,將純粹的道德義務(wù)與法律義務(wù)相混同勢必極大地?cái)U(kuò)張不作為犯罪的成罪范圍進(jìn)而違背罪刑法定原則。不過,頗感遺憾的是,在此一問題上,中外刑法學(xué)者除了一味地簡單強(qiáng)調(diào)作為義務(wù)僅限法律上的義務(wù)而不得為純粹的道德義務(wù)外,迄今依然未找到界分二者的具體規(guī)范標(biāo)準(zhǔn)。有關(guān)道德可否成為作為義務(wù)的根據(jù)問題,已然成為每一不作為犯研究者頭頂揮之不去的疑云。
(三)法律義務(wù)與道德義務(wù)之實(shí)定法判準(zhǔn)掘發(fā)。犯罪作為違法行為的極端形式,一般而言,其對社會道德底線規(guī)范的違反顯而易見,即多數(shù)情況下,刑事義務(wù)與純粹的道德義務(wù)之間可謂涇濁渭清、不易混淆。但由于犯罪之成立依賴于犯罪構(gòu)成諸要件的判定,而發(fā)展迄今的罪刑法定原則雖不承認(rèn)習(xí)慣、條理等作為刑法規(guī)范的直接淵源,但還是肯認(rèn)其可作為犯罪構(gòu)成要件理解的依據(jù)。〔10 〕 (P22 )如此,當(dāng)依據(jù)習(xí)慣、條理等間接刑法淵源來理解具體罪的構(gòu)成要件時,就將使得違反刑事義務(wù)的犯罪行為與違反純粹道德義務(wù)的行為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不清,這種模糊性在不作為犯罪中表現(xiàn)得最為突出;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因作為犯罪后果的刑罰以剝奪公民的基本人權(quán)為內(nèi)容,其無以復(fù)加的嚴(yán)厲性又使得嚴(yán)格界分純粹的道德義務(wù)與法律義務(wù)顯得尤為必要。
筆者以為,法律義務(wù)與純粹道德義務(wù)之間的模糊地域存在于如下兩種情形之中:一是法規(guī)范明確設(shè)定了某項(xiàng)義務(wù),但卻對違反該項(xiàng)義務(wù)之行為并未配置相應(yīng)的法律制裁措施,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16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第5條、《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條、《刑事訴訟法》第48條等條文之規(guī)定,學(xué)界就此類義務(wù)究竟是法律性質(zhì)的義務(wù)亦或是純粹的道德義務(wù)存在較大爭議。二是那些已經(jīng)上升為部門法基本原則的道德規(guī)范,因難以確定其本身的內(nèi)涵和外延,使得違反此類基本原則的行為到底該如何定奪也往往存在困難,如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勞動合同法第3條、物權(quán)法第7條等條文規(guī)定的“誠信原則”和“公序良俗原則”。這兩項(xiàng)原則均可謂系由純粹的道德規(guī)范上升為部門法基本原則的,但各自意涵的不確定性勢必模糊其他部門法義務(wù)與純粹道德義務(wù)間的界限。
對于上述第一種情形,當(dāng)我們對此類規(guī)范的邏輯結(jié)構(gòu)辨析后不難發(fā)現(xiàn),雖然這些義務(wù)已被相關(guān)法律確認(rèn),但對違反此類義務(wù)之行為的制裁措施卻付諸闕如。而眾所周知,在國家公權(quán)領(lǐng)域,國家機(jī)關(guān)及其工作人員的任一職權(quán)均須法律的明確授權(quán),即必須嚴(yán)格循守“法無授權(quán)即禁止”之原則,否則便是僭權(quán)違法。換言之,因制裁措施的缺位使得即便公民違反此類規(guī)范,國家機(jī)關(guān)也無制裁之權(quán)力,故此類義務(wù)與純粹道德義務(wù)并無本質(zhì)差異,也就不能成為不作為犯罪之作為義務(wù)。對于第二種情形,即已被部門法原則化的基本道德規(guī)范所設(shè)定的義務(wù)能否成為作為義務(wù)的問題,則存在極大地爭議,肯定者有之,否定者更有之。對此,筆者以為,因作為義務(wù)只能是民法、行政法或訴訟法等性質(zhì)的義務(wù),在這些部門法中,因民事制裁措施在強(qiáng)度上相對于其他部門法最為輕弱,這即意味著在整個法規(guī)范體系中,民事違法行為與違反純粹道德義務(wù)的行為最易混同,更兼誠實(shí)信用、公序良俗作為民法基本原則地位之確立,這又使得二者間的界限愈顯撲朔迷離。就此而言,法律義務(wù)與純粹道德義務(wù)之界分基本集中在民法中的誠實(shí)信用、公序良俗原則之適用范圍上,即只要厘清民事義務(wù)與純粹道德義務(wù)之關(guān)系,其他部門法義務(wù)與純粹道德義務(wù)的界限也將水到渠成。
倘若僅從語義學(xué)視角界定誠實(shí)信用、公序良俗原則之意涵,進(jìn)而認(rèn)定在兩原則之下設(shè)定的義務(wù)均可成為不作為犯罪之作為義務(wù),一方面不僅否定了作為義務(wù)之法律性質(zhì),另一方面也確實(shí)會無限擴(kuò)展不作為犯之成立界域而有悖罪刑法定原則,這也是我國多數(shù)刑法學(xué)者對此持徹底否定態(tài)度之緣故。但筆者認(rèn)為,徹底否定兩項(xiàng)原則能夠成為作為義務(wù)來源之舉措并不妥宜,理由在于,是否違反誠實(shí)信用、公序良俗原則的行為均不產(chǎn)生民事責(zé)任呢?果真如此,民法基本原則在民法規(guī)范體系中的最高效力及對立法和司法實(shí)踐的指導(dǎo)作用又從何體現(xiàn)?民法中的誠實(shí)信用、公序良俗原則的適用范圍真如多數(shù)論者所認(rèn)為的是渺無邊際嗎?于筆者看來,否定論者乃至整個我國刑法學(xué)界在探究不作為犯罪之作為義務(wù)與純粹道德義務(wù)間之界限時,均忽視了這兩項(xiàng)原則適用的前置條件,即“民事活動”之限制條件!換言之,依據(jù)我國民法通則之規(guī)定,并非任何違反誠實(shí)信用、公序良俗原則的行為都會受到民事制裁,惟在民事活動中違反誠實(shí)信用、公序良俗原則的行為方得承擔(dān)民事責(zé)任之法律后果。而民事責(zé)任以違反民事義務(wù)為前提,故作此等限定并未改變作為義務(wù)之法律義務(wù)性質(zhì),這便極大地限定了誠實(shí)信用、公序良俗原則之適用畛域。同時,因誠實(shí)信用、公序良俗乃人與人相處的底線倫理,也是社會整體秩序(含法律秩序)正常維系及運(yùn)轉(zhuǎn)的基本條件,故不論是民事活動亦或是行政活動和訴訟活動,相關(guān)主體均應(yīng)恪守這兩項(xiàng)基本原則。析論自此,違反誠實(shí)信用、公序良俗的行為能否引起作為義務(wù)的答案便已昭然若揭,即民事活動、行政活動及訴訟活動中的違反誠實(shí)信用、公序良俗的行為能夠成為作為義務(wù)之發(fā)生根據(jù),反之則否。
三、法律義務(wù)與道德義務(wù)區(qū)辨標(biāo)準(zhǔn)之運(yùn)用
如上限定不僅為辨別法律義務(wù)與純粹的道德義務(wù)提供了具體的法規(guī)范標(biāo)準(zhǔn),從而為公權(quán)與私權(quán)劃定了界域,而且也能夠?qū)σ恍╅L期困擾我國刑法理論和司法實(shí)務(wù)的疑難事案給出合情合理合法的詮解。譬如,在瀕死之傷者邊圍觀的看客或經(jīng)其旁路過而未予施救的路人,雖然違反了公序良俗但因并非發(fā)生在民事活動中,故不產(chǎn)生法律上救助之作為義務(wù);又如乳母受雇哺乳嬰兒,在嬰兒親屬較長時間的外出期間合同期滿,乳母在未盡善良告知義務(wù)的情形下旋即以合同期滿為由停止哺乳,便屬于民事活動中違反公序良俗原則的行為,故能夠引起法律上的作為義務(wù)。
再有如此般事案:1993年3月,李某和項(xiàng)某(女)相識并相戀,不久項(xiàng)懷孕。同年6月,李提出分手并要求項(xiàng)去醫(yī)院流產(chǎn)。項(xiàng)斷然拒絕,幾次欲跳樓輕生。同年9月5日中午,李回宿舍,見項(xiàng)在屋內(nèi),便起爭吵。項(xiàng)當(dāng)面喝下預(yù)先備好的一瓶敵敵畏。此時,李不僅未及時救人,反一走了之,臨走時怕被人察覺還將房門鎖上。當(dāng)日下午,項(xiàng)被人發(fā)現(xiàn)后送往醫(yī)院,終因搶救無效死亡。本案中,被告人作為房屋的所有人(或占有人),從公序良俗的角度來說,當(dāng)他人在其居所內(nèi)面臨生命危險(xiǎn)時,縱使他對該危險(xiǎn)并無過錯,但在這危急關(guān)頭若將房門鎖上,就顯然屬于行使民事權(quán)利違反公序良俗原則的行為,因此,被告人的行為成立(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
又復(fù)如:山區(qū)公路上,執(zhí)法人員甲開車追趕騎摩托車運(yùn)輸假煙的乙,并命其停車接受檢查,乙為逃避追查而不僅未停車反而加速疾馳,慌亂中撞向了路邊大樹而身受重傷,甲追上后見乙血流不止也未予理會而開車徑行離去,兩小時后乙死亡。本案中,甲的行為就是在行政執(zhí)法活動中違反公序良俗原則,故能夠產(chǎn)生救助之作為義務(wù),因如上所述,誠實(shí)信用、公序良俗乃整個社會(含法律秩序)有效運(yùn)轉(zhuǎn)的基本條件,普通公民在民事活動中都應(yīng)遵守這兩項(xiàng)基本原則,國家工作人員在執(zhí)行職務(wù)時還代表著國家,當(dāng)然更應(yīng)以身作則,不能例外。因此,本案中甲具有救助乙之作為義務(wù)。
四、實(shí)質(zhì)作為義務(wù)學(xué)說之否定
在不作為犯的作為義務(wù)理論中,存在兩種頗具影響力的學(xué)說——形式作為義務(wù)學(xué)說和實(shí)質(zhì)作為義務(wù)學(xué)說,后者是在批判前者的基礎(chǔ)上逐漸形成的。在實(shí)質(zhì)作為義務(wù)論者看來,以列舉的方式來闡釋作為義務(wù)的來源固然具有外在形式上的明確性和確定性,但它卻未能從實(shí)質(zhì)上解答為何這些情形(法律、契約和先行行為等)能夠引起作為義務(wù)的問題。于是學(xué)者們便試圖透過形式作為義務(wù)來源以探尋其背后的所謂實(shí)質(zhì)法理依據(jù),為此,他們提出了形形的實(shí)質(zhì)作為義務(wù)學(xué)說。對于前述系列疑難案件,學(xué)者們也都往往訴諸于實(shí)質(zhì)作為義務(wù)學(xué)說,冀圖從中尋獲破解之道。但在筆者看來,實(shí)質(zhì)作為義務(wù)理論存在著根基性的錯誤,理由在于,如前所析,作為義務(wù)只能是民法、行政法或訴訟法等性質(zhì)的義務(wù),而非刑事法律義務(wù),故所謂作為義務(wù)的實(shí)質(zhì)法理依據(jù)實(shí)際就是揭示其他部門法為何要設(shè)定這些法律義務(wù)的問題,例如,民法為何要在父母子女間設(shè)定撫(扶)養(yǎng)義務(wù)?契約、無因管理等產(chǎn)生民事義務(wù)之理據(jù)何在?如此等等,顯然,這些義務(wù)發(fā)生的法理依據(jù)早已為其他部門法理所揭示,而無需刑法學(xué)者越俎代庖。可見,在刑法學(xué)論域,實(shí)無另行探究作為義務(wù)實(shí)質(zhì)理據(jù)之必要。理論本身的錯謬必將導(dǎo)致難以合理析解司法實(shí)務(wù)中的疑難案件,所謂形枉而影曲。因此,那些依據(jù)實(shí)質(zhì)作為義務(wù)理論對上述案件作出的處理意見雖然有時結(jié)論正確,但論證本身不具合理性。
參考文獻(xiàn):
〔1〕〔蘇〕 A·古謝伊諾夫,T·伊爾利特茨.西方倫理學(xué)簡史〔M〕.劉獻(xiàn)洲,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2.
〔2〕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學(xué)說史略〔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
〔3〕段鳳麗,李金明.不作為犯罪的作為義務(wù)來源新論〔J〕.〔美〕國家檢察官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4,(5).
〔4〕〔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xué):法律哲學(xué)與法律方法〔M〕.鄧正來,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4.
〔5〕〔美〕羅科斯·龐德.法律與道德〔M〕.陳林林,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2003.
〔6〕〔德〕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M〕.徐久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
〔7〕許成磊.不純正不作為犯比較研究〔D〕.中國人民大學(xué)博士學(xué)位論文,2003.
〔8〕林山田.刑法通論〔M〕.臺北:三民書局,1985.
第6篇:刑法哲學(xué)論文范文
論文關(guān)鍵詞 錯誤 概念 分類
一、錯誤的概念及剖析
美國學(xué)者喬治·P·弗萊徹把錯誤問題看作各國刑法事實(shí)上都會面臨的處于刑法理論上最困難的12個問題之列,明確其定義尤為重要。英美國家把“不知或錯誤”簡稱錯誤,是指行為人對事實(shí)或法律沒有認(rèn)知(不知)或者主觀認(rèn)識同事實(shí)本身或法律本身不一致。前蘇聯(lián)刑法學(xué)家別利亞耶夫等認(rèn)為:“錯誤是犯罪主體對它所實(shí)施行為的法律評價(jià)或事實(shí)情況錯誤的認(rèn)識。”筆者認(rèn)為相較以下幾種定義較為可取,但也非無缺。
有學(xué)者從形式上或?qū)嵸|(zhì)上把錯誤僅僅理解客觀事實(shí)上之錯誤。如:日本學(xué)者中山研一認(rèn)為:“所謂錯誤是指客觀的事實(shí)與行為人的主觀認(rèn)識不一致。”我國臺灣地區(qū)劉清波認(rèn)為:“錯誤者,主觀認(rèn)識與客觀之事實(shí)不相符合之狀態(tài)也。即行為人對于犯罪之認(rèn)識與所預(yù)見者不一也。”筆者認(rèn)為,法律錯誤是錯誤中的另一半,即便是在“事實(shí)的不知得以抗辯,法律的不知不得抗辯”這一古老的羅馬法原則下,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也逐步和緩與動搖。所以,無論是在概念表達(dá)上還是實(shí)質(zhì)上,都應(yīng)給予其必要地位。這里的“事實(shí)”范圍如何也未明確。有學(xué)者把錯誤的對象表述為社會危害性和犯罪構(gòu)成事實(shí)。基里欽科認(rèn)為:“錯誤是行為人對其所實(shí)施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那些組成某種犯罪構(gòu)成之重要因素的情況所產(chǎn)生的不正確觀念。”阮齊林教授在《論刑法中的認(rèn)識錯誤》一文中指出,刑法中的認(rèn)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對自己實(shí)施的犯罪構(gòu)成事實(shí)或者對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質(zhì),主觀認(rèn)識與客觀實(shí)際不一致。對于社會危害性是否與違法性相同,這在理論上還有爭議,有的認(rèn)為社會危害性就是違法性,違法性認(rèn)識錯誤即法律認(rèn)識錯誤。筆者認(rèn)為社會危害性與違法性的關(guān)系是內(nèi)容和形式的關(guān)系。基于此,社會危害性應(yīng)為違法性所取代,筆者將在對錯誤的分類中進(jìn)行詳述。有學(xué)者對刑法中錯誤的定義過于籠統(tǒng),定義項(xiàng)不夠清晰明了,有犯“定義含混”的邏輯錯誤。如:有論者認(rèn)為刑法中的認(rèn)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實(shí)施直接故意犯罪時,對與其行為相關(guān)的犯罪情況的不完全(或曰不準(zhǔn)確)反映。”這里的“相關(guān)的犯罪情況”究竟是指“事實(shí)”的情況還是“法律”的情況,抑或是兼具兩者的情況,指代不明。舊中國《法律大辭書》中定義“‘錯誤'是觀念(刑法)與現(xiàn)象差異之謂也”(“現(xiàn)象”是指事實(shí)還是法律抑或是指二者之和并未明確)。
從以上各學(xué)者對錯誤所下的定義中,可以發(fā)現(xiàn)不少觀點(diǎn)把錯誤限制在認(rèn)識上,這樣有犯“定義過窄”的邏輯錯誤之嫌。筆者認(rèn)為,刑法中的錯誤不僅僅是一種主觀的心理態(tài)度,還包括行為錯誤,如打擊錯誤(又叫方法錯誤,在西方刑法理論界受到較大重視,對其理論研究較為深入。但我國一般將其排除)。刑法中的錯誤包含兩個因素:一是作為主體的具有辨認(rèn)和控制能力的人,二是是能為主體所認(rèn)識的客觀方面。從哲學(xué)實(shí)踐觀和認(rèn)識論的關(guān)系來看,主體之認(rèn)識是在實(shí)踐的基礎(chǔ)上對客體的能動反映,客體是實(shí)踐和認(rèn)識活動所指向的對象,是主體以外的客觀事物方面。整個人類社會都處于主客體之間是認(rèn)識與被認(rèn)識、改造與被改造的關(guān)系,刑法中的錯誤認(rèn)識論也不例外。就客觀面來講,刑法錯誤論中能被主體所認(rèn)識的客觀面包括一切具有刑法規(guī)范意義的事物,總體上可以分為事實(shí)方面和法律方面。事實(shí)錯誤應(yīng)當(dāng)限制為具有刑法重要意義的事實(shí),是指那些被刑法規(guī)定為某罪必須具備的構(gòu)成要件要素和影響定罪量刑的事實(shí)。法律方面應(yīng)當(dāng)限制至具有刑法評價(jià)意義的法律規(guī)范。這樣不僅符合罪刑法定主義,而且符合刑法的平等性和謙抑性原則。避免傳統(tǒng)的事實(shí)錯誤與法律錯誤過于泛化而不易把握,節(jié)約司法成本。因此,為準(zhǔn)確揭示刑法中錯誤的本質(zhì)屬性和特有屬性,明確其內(nèi)涵和外延,筆者認(rèn)為刑法中的錯誤是指,行為主體對其所實(shí)施行為的具有刑法重要意義的事實(shí)情況或刑法規(guī)范評價(jià)有不知或誤解以及行為上的差誤。
二、國外關(guān)于錯誤的劃分及剖析
古羅馬法處理錯誤問題繼承了法學(xué)家帕烏魯斯提出的“不知法律不赦”的原則。該原則始于私法領(lǐng)域,后引申到刑法學(xué)中來。根據(jù)這一原則,以錯誤的對象為標(biāo)準(zhǔn)通常把錯誤分為事實(shí)錯誤和法律錯誤兩類,事實(shí)錯誤是指行為人主觀上認(rèn)識的事實(shí)與客觀上發(fā)生的事實(shí)不一致。廣義的事實(shí)錯誤還包括在構(gòu)成要件以外的正當(dāng)化前提事實(shí)的錯誤,既可能是純粹的事實(shí),也可能是關(guān)于法律的事實(shí)(如關(guān)于物品的“性”)。法律錯誤是指行為人對自己行為的法律性質(zhì)有不正確的認(rèn)識,廣義的法律錯誤還包括非刑法法規(guī),日本改正刑法草案說明書第21條第1項(xiàng)中的“法律的錯誤”即屬之。狹義的理解該種劃分,則與德國刑法學(xué)家威爾澤爾所作劃分意義相同。此種分類簡單明了,概括性強(qiáng)。同時,這種概括也缺少限制,也容易造成誤解。因?yàn)槿绻麖膹V義的角度來理解,有犯“定義過寬”的邏輯錯誤,這是其所產(chǎn)生的十分重要之問題。二戰(zhàn)后,德國刑法學(xué)家威爾澤爾以犯罪的成立要件為標(biāo)準(zhǔn),把刑法中錯誤分為構(gòu)成要件的錯誤和禁止的錯誤。構(gòu)成要件的錯誤是有關(guān)構(gòu)成要件要素上的錯誤,是行為時事實(shí)的認(rèn)識錯誤。禁止的錯誤是有關(guān)行為違法性的錯誤,所以又稱為“違法性的錯誤”,是對規(guī)范認(rèn)識的錯誤。這種分類為目的行為論者所提倡,在德國形成廣泛影響并為現(xiàn)行的刑法典所采納。但也有不足之處,如“容許構(gòu)成要件錯誤”將置于何處?這就有犯“劃分不全”的邏輯錯誤之嫌。在對一個概念進(jìn)行劃分應(yīng)當(dāng)遵循的一個規(guī)則就是劃分子項(xiàng)外延之和必須等于母項(xiàng)的外延,如果劃分后各子項(xiàng)的外延之和小于母項(xiàng)的外延,就會出現(xiàn)“劃分不全”的邏輯錯誤。“容許構(gòu)成要件錯誤”是指阻卻違法事由的事實(shí)錯誤。正當(dāng)化事由前提事實(shí)的錯誤是對違法阻卻事由是否成立的前提“事實(shí)”的錯誤認(rèn)識,不是構(gòu)成要件要素的錯誤。該錯誤通常也不屬于法律錯誤,但在某些情況下會成為法律的錯誤。前蘇聯(lián)的刑法理論界大多數(shù)刑法學(xué)者都贊同傳統(tǒng)的兩分法,但基里欽科根據(jù)錯誤的概念,把刑法中的錯誤分為三種:對于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錯誤、對于組成犯罪構(gòu)成因素的情況的錯誤、法律的錯誤或法律上的錯誤。筆者認(rèn)為,社會危害性究其本質(zhì)而言屬于法律錯誤,尤其是在我國。首先,從我國《刑法》第13條對犯罪定義的規(guī)定可以看出犯罪是違反我國刑法所實(shí)施的嚴(yán)重危害社會并且應(yīng)受刑事處罰的行為,違反刑法所實(shí)施的嚴(yán)重危害社會的行為是一個整體,也就是說違反刑法的行為必定具有嚴(yán)重的社會危害性,可以說兩者是內(nèi)容與形式的關(guān)系:第一,內(nèi)容和形式相互區(qū)別,但這種區(qū)別終究是同一事物中的兩個方面。社會危害性和違法性就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第二,內(nèi)容和形式相互聯(lián)系、相互依存。任何事物都有內(nèi)容和形式兩個側(cè)面,都是二者的統(tǒng)一體。形式必須以一定的內(nèi)容為基礎(chǔ),而內(nèi)容必須有其外在形式,作為內(nèi)容的社會危害性就必須以違法性作為形式;第三,內(nèi)容和形式相互作用,內(nèi)容決定形式,形式必須適合內(nèi)容。形式反作用于內(nèi)容,形式使內(nèi)容成為某一特定事物的內(nèi)容。犯罪是嚴(yán)重的社會危害性和刑事違法性的統(tǒng)一體。嚴(yán)重的社會危害性是其實(shí)質(zhì)內(nèi)容和本質(zhì)屬性,是違法性和應(yīng)受懲罰性的前提和決定條件,違反刑法是其法律形式,如果把兩者對立起來,違反刑法的行為是空洞的,同時,嚴(yán)重的社會危害性也就失去了判斷的標(biāo)準(zhǔn)。其次,基里欽科在《蘇維埃刑法中錯誤的意義》一書中對誤想犯罪究竟是社會危害性錯誤還是法律上的錯誤也不明確。
第7篇:刑法哲學(xué)論文范文
論文關(guān)鍵詞 犯罪故意 明知 認(rèn)定
我國《刑法》第11條規(guī)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fā)生危害社會的結(jié)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jié)果發(fā)生,因而構(gòu)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應(yīng)當(dāng)負(fù)刑事責(zé)任。”這是關(guān)于犯罪故意的法定概念,也是我國刑法理論界關(guān)于犯罪故意概念的通說。其中,“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fā)生危害社會的結(jié)果”是犯罪故意具備的認(rèn)識因素;“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jié)果發(fā)生”是犯罪故意具備的意志因素,兩者均揭示了行為人承擔(dān)故意犯罪刑事責(zé)任的主觀要件。如何理解犯罪故意的涵義一直是刑法理論界討論的問題。在司法實(shí)踐中,對于故意犯罪的刑事案件中行為人的犯罪故意的證明,也成為司法認(rèn)定的一大難題。本文擬從犯罪故意中“明知”的理解入手,具體分析犯罪故意認(rèn)定在司法實(shí)踐中存在的問題及認(rèn)定的途徑。
一、犯罪故意中“明知”的涵義及內(nèi)容
要正確認(rèn)識犯罪故意的前提是正確理解“明知”的含義。目前,對于“明知”的理解,大陸法系國家的刑法理論界存在三種說法:廣義說、狹義說、折衷說。廣義說(抽象符合說),認(rèn)為行為人所意圖實(shí)施的行為與實(shí)際發(fā)生的犯罪行為具有某種性質(zhì)上的一致,就可定義為犯罪故意中的“明知”。狹義說(具體符合說),則要求行為人只有對自己具體實(shí)施的能構(gòu)成犯罪所有事實(shí)具有完全正確的認(rèn)識,才能認(rèn)定為刑法上的犯罪故意中的“明知”。狹義說和廣義說因?qū)Α懊髦钡睦斫膺^于狹隘或?qū)挿海蚨撾x法律實(shí)際。目前,在大陸法系國家被廣泛認(rèn)可的是折衷說(法定符合說)。該觀點(diǎn)遵循的是犯罪構(gòu)成理論,要求行為人對犯罪客體要有明確的認(rèn)知,認(rèn)為只有行為人認(rèn)識或者預(yù)見的事實(shí)與其實(shí)際發(fā)生的事實(shí)在符合同一犯罪構(gòu)成要件的范圍,才能認(rèn)定為行為人具備犯罪故意的“明知”。目前,該學(xué)說在我國刑法學(xué)界也得到不少權(quán)威人士的肯定。從犯罪構(gòu)成的理論角度看,“折衷說”是把行為人在其意志因素下實(shí)施的行為定義為要符合法定構(gòu)成的客觀要件,這是值得肯定的,但該學(xué)說在概念上仍然存在的一定的模糊。我國刑法學(xué)教授林就此提出了對“明知”要作實(shí)質(zhì)的理解的“認(rèn)識符合說”,即犯罪故意中的明知是行為人行為時對自己希望或者放任中的行為是否具有某罪特有的客觀性質(zhì)的明確認(rèn)識。
筆者贊成以上觀點(diǎn),并認(rèn)為在此基礎(chǔ)上,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對“明知”進(jìn)行理解:
一是明知的對象,是行為人在自我意識的導(dǎo)向下,意欲(希望或者放任)發(fā)生的行為,而不一定就是行為人客觀上實(shí)施的某種行為。因此,判斷行為人“明知”是否成立首要關(guān)注的應(yīng)該是行為人希望或者放任的行為是否具備特定犯罪的特有性質(zhì)。但在司法實(shí)踐中,也要區(qū)別行為人認(rèn)識到自己的行為會發(fā)生危害社會的結(jié)果但客觀上沒有發(fā)生和行為人以為自己的行為可能會發(fā)生危害社會的結(jié)果但客觀根本不會發(fā)生危害社會結(jié)果的兩種情形。在前者的情形下,可能構(gòu)成犯罪未遂,除非是不符合客觀規(guī)律的迷信犯。在后者情形下,則有可能因?yàn)椴环戏缸飿?gòu)成的客觀要件而不構(gòu)成犯罪。
二是明知的內(nèi)容,既包括對自己行為的明知,也包括對自己的行為會引起什么樣的危害社會的結(jié)果的明知。行為人雖然無法直接知曉自己的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結(jié)果究竟損害了某種法益,但是其對自己的意圖實(shí)施的行為是否具備某罪客觀方面應(yīng)有的性質(zhì)是應(yīng)該有所認(rèn)知的。比如,容留罪中的行為人,雖然可能不知道其實(shí)際上損害的法益是社會治安管理秩序,但是其一般都知曉其為者提供一定場所,是一種有損風(fēng)化的不良行為。
三是明知應(yīng)符合自然規(guī)律和社會規(guī)律。明知的對象是行為人意識中希望或放任的行為,行為人一般會認(rèn)為只要按照自己意思表示來展開行為,就能發(fā)生自己意欲發(fā)生的結(jié)果。這實(shí)際上是行為人對自己主觀罪過展開的行為的一種規(guī)律性認(rèn)識。因此,只有行為人對自己意圖實(shí)施的行為的認(rèn)識合乎常理、常識和常情,才可認(rèn)定為犯罪故意的“明知”,反之,就不能認(rèn)定為“明知”。比如,客觀不能犯的迷信犯及無刑事責(zé)任能力者對行為的認(rèn)識就不能認(rèn)定犯罪故意中的明知。
二、犯罪故意的“認(rèn)定”在司法實(shí)踐中存在的問題
犯罪故意本質(zhì)上是行為人一種主觀心理態(tài)度,是存在于人類內(nèi)心深處的精神世界。作為外界人,很難被直接認(rèn)知、查明和認(rèn)定,即使使用偵查、心理實(shí)驗(yàn)等科學(xué)方法,也不能還原行為人當(dāng)時之心態(tài)。如有學(xué)者所言:“意識問題一直是科學(xué)和哲學(xué)研究中極其困難和復(fù)雜的問題”,“意識是心理學(xué)中的一個傳統(tǒng)基本理論問題,更是哲學(xué)、心理學(xué)上的老大難議題。”可見,犯罪故意的認(rèn)定問題,不僅是困擾刑法理論的難題,也是歷來困擾刑事司法實(shí)務(wù)的難題。
我國法律明確規(guī)定了案件事實(shí)中的“故意”必須要用證據(jù)證明。目前,在我國的司法實(shí)踐中,主要是通過兩種證據(jù)來認(rèn)定犯罪故意,一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系證明犯罪故意存在的唯一直接證據(jù);二是能形成證據(jù)鏈的間接證據(jù)。這兩種途徑的使用也面臨著眾多的問題。就第一種途徑而言,如果一案件中只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論是根據(jù)我國刑事訴訟法的關(guān)于“僅有被告人供述不能認(rèn)定有罪”的規(guī)定,還是“孤證不能定罪”的原則,均不能直接認(rèn)定其具有犯罪故意。加之,犯罪嫌疑人時常會出現(xiàn)翻供的情形,讓我們更加難以判斷認(rèn)定其真實(shí)的心里狀態(tài)。由此可見,犯罪故意不可能單獨(dú)依靠直接證據(jù)來直接證明。當(dāng)我們在尋求間接證據(jù)來證明犯罪故意的時候,就必須要形成一個完整、緊密的證據(jù)鎖鏈,這是必然要需要使用“推定”這一邏輯方法來填補(bǔ)證據(jù)鏈存在的一定的縫隙或空白處。
在證據(jù)學(xué)中,推定是指在缺乏證據(jù)直接證實(shí)A事實(shí)時,基于已經(jīng)得到證明的B事實(shí),根據(jù)B事實(shí)與A事實(shí)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從而推定A事實(shí)的存在。推定,實(shí)際上就是人們在對社會某種現(xiàn)象的進(jìn)行反復(fù)認(rèn)識研究之后所得出的一種經(jīng)驗(yàn)法則,在不同的事實(shí)之間尋求一種因果關(guān)系,這種因果關(guān)系是非必然的,存在一定的或或然性的。在司法實(shí)踐中,近些年出現(xiàn)的佘祥林、莫衛(wèi)奇、謝開其、浙江張高平兄弟兩等冤家錯案的發(fā)生,或多或少都是在證據(jù)推定上出了問題。
三、犯罪故意的認(rèn)定途徑
犯罪故意的認(rèn)定問題,從實(shí)體法上看是對行為人的歸責(zé)問題,但解決的落腳處應(yīng)是訴訟法上的證明問題。這是一個程序法與實(shí)體法交錯的問題,更是司法實(shí)踐工作者不可逃避而必須要面對的問題。筆者嘗試從刑法思維模式、無罪推定原則、推定方法的角度對犯罪故意的認(rèn)定及證明問題進(jìn)行探討。
(一)克服刑法主觀主義的思維模式
在司法實(shí)踐工作中,很多司法人員根據(jù)我國刑法理論關(guān)于犯罪構(gòu)成四要件的規(guī)定,在犯罪認(rèn)定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本末倒置的認(rèn)定順序——先憑自我感覺該行為像什么罪,而后依次按照犯罪構(gòu)成四要件再比對論證。在具體審查證據(jù)的過程中,更是習(xí)慣于先主觀證據(jù)(犯罪嫌疑人口供等)后客觀證據(jù)(書證物證等)的思維模式。這是一種典型的刑法主觀主義思維,容易使司法人員陷入重視口供或者絕對依賴口供、口供優(yōu)于物證書證、主觀判斷優(yōu)于客觀判斷的誤區(qū),不利于犯罪故意的認(rèn)定。因此,司法工作者在思維模式上,必須要從刑法主觀主義轉(zhuǎn)變?yōu)樾谭陀^主義。在認(rèn)定犯罪故意時,不要按圖索驥,要從客觀的事實(shí)、證據(jù)、要素出發(fā),重視口供以外的證據(jù)的收集,讓犯罪嫌疑人在事實(shí)面前供認(rèn)不諱”,從而較為準(zhǔn)確地展示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狀態(tài)。
(二)堅(jiān)守?zé)o罪推定原則的底線
犯罪故意作為一種主觀性事實(shí),外界人要想有所了解,需要綜合考量行為人的主客觀基礎(chǔ)事實(shí)。評價(jià)者在進(jìn)行評價(jià)時,不自覺地會加入自身和社會的評價(jià)標(biāo)準(zhǔn)。在司法實(shí)踐中,當(dāng)犯罪嫌疑人對犯罪事實(shí)是否“明知”難以認(rèn)定時,控訴方往往基于追訴犯罪的需要,進(jìn)行“有罪推定”,傾向性地認(rèn)為行為人存在犯罪故意。然而,故意的認(rèn)定在實(shí)體法的最終意義上是歸責(zé)問題。故意的有無,故意的大小,有著天壤之別,這不僅表明罪與非罪的差異,也表明罪責(zé)輕重的差異。因此,對于犯罪故意的認(rèn)定,應(yīng)該杜絕“有罪推定”,堅(jiān)持“無罪推定”,在事實(shí)無法確定查證屬實(shí)的情況下,堅(jiān)持存疑有利于被告,以實(shí)現(xiàn)對人權(quán)的保護(hù)。
(三)使用科學(xué)的推定方法
推定是認(rèn)定犯罪故意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思維方法。如前所述,推定作為一種經(jīng)驗(yàn)法則在證明犯罪故意上存在著某種固有的缺陷,推定的結(jié)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蓋然性。因此,使用科學(xué)的推定方法事關(guān)重要。
犯罪故意中的“明知”既包括對行為的明知,也包括對會發(fā)生危害社會的結(jié)果的明知。無論行為人是知道(直接故意)還是應(yīng)當(dāng)知道(間接故意),外界的評價(jià)者都可依據(jù)一定的客觀基礎(chǔ)事實(shí)和主觀認(rèn)識進(jìn)行推定。筆者認(rèn)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推定:第一,行為手段。行為手段是行為人為實(shí)現(xiàn)犯罪目的的重要條件。行為人煞費(fèi)心機(jī)地設(shè)計(jì)、使用特定的手段,對一定的行為對象實(shí)施犯罪行為,則基本上能說明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后果、違法性質(zhì)等要素有認(rèn)知。第二,行為的對象、時間、地點(diǎn)。行為人有意識地選擇特定的行為對象,并在非正常的時間、地點(diǎn)實(shí)施特定的犯罪行為,也能表明了行為人對行為的違法性質(zhì)有認(rèn)知。第三,行為人案發(fā)前后的表現(xiàn)。行為人在案發(fā)前積極準(zhǔn)備工具,創(chuàng)造實(shí)施行為的條件,在案發(fā)后實(shí)施了毀滅、偽造證據(jù),干擾證人作證或者串供;四處流竄,逃避偵查;隱匿、轉(zhuǎn)移贓物等掩蓋犯罪事實(shí)、逃避法律追究等行為的,一般可以推定行為明知自己行為。第四,行為人的背景經(jīng)歷等情況。根據(jù)行為人的家庭、籍貫、職業(yè)、學(xué)歷、社會關(guān)系等背景資料,可以推定行為人對某事情的了解程度。行為人有無類似前科犯罪,有無行政處罰的經(jīng)歷,可以幫助推定行為人是否對某種行為性質(zhì)有認(rèn)知。
第8篇:刑法哲學(xué)論文范文
【關(guān)鍵詞】因果關(guān)系;事實(shí)因果關(guān)系;法律因果關(guān)系;客觀可歸責(zé)性
【正文】
查明行為人的行為與結(jié)果之間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guān)系,進(jìn)而決定能否將該危害后果歸咎于行為人,對于解決行為人應(yīng)否負(fù)刑事責(zé)任的問題無疑有著重大意義。然而關(guān)于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爭論可謂經(jīng)久不衰。我國刑法學(xué)界對于因果關(guān)系的爭論也從未停止過。從因果關(guān)系在刑法中的地位到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糾纏,再到因果關(guān)系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無不充斥著對立的見解。這些事實(shí)表明,對因果關(guān)系的認(rèn)識有必要而且可以進(jìn)一步深化。為此,筆者擬以我國因果關(guān)系的研究為主要考察對象,適當(dāng)評說西方國家的因果關(guān)系理論,以期轉(zhuǎn)換視角,為我國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理論研究找到新的切入點(diǎn)。
一、刑法因果關(guān)系論之危機(jī)
(一)因果關(guān)系在刑法中的定位問題
依照大陸法系刑法理論的通說,因果關(guān)系在刑法上的判斷所涉及的場合僅僅限于結(jié)果犯,而在其他場合則沒有必要特別考慮其因果關(guān)系的問題。{1}如舉動犯,只要單純著手實(shí)施了一定的舉動,不待具有侵害結(jié)果的發(fā)生,即可成立,因而無需考察其因果關(guān)系。我國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刑法因果關(guān)系是犯罪構(gòu)成客觀方面的一個選擇要件。具體說,它只是過失犯罪、間接故意犯罪和刑法分則強(qiáng)調(diào)只有諸如‘情節(jié)嚴(yán)重’、‘造成重大損失’、‘?dāng)?shù)額較大’才構(gòu)成犯罪的故意犯罪的構(gòu)成要件。”{2}
然而,上述觀點(diǎn)明顯存在不足。因果關(guān)系存在的必要性依賴于刑法中“結(jié)果”的界定,而“結(jié)果”及“結(jié)果犯”本身是一個不明確的概念,這樣一來,哪些情形需要論證因果關(guān)系就成為難題。例如,采納廣義的結(jié)果犯的概念,包括危險(xiǎn)犯在內(nèi),則既然構(gòu)成要件上作為實(shí)行行為的結(jié)果要求發(fā)生一定的危險(xiǎn),那么在實(shí)行行為與所發(fā)生的危險(xiǎn)之間也必須存在因果關(guān)系。但是,有人會反駁說,因果關(guān)系是指客觀事物之間引起與被引起的關(guān)系,無論原因還是結(jié)果,都應(yīng)當(dāng)是現(xiàn)實(shí)的事物,而危險(xiǎn)實(shí)際上只是一種可能性,是向現(xiàn)實(shí)性轉(zhuǎn)化的一種趨勢,把危險(xiǎn)也當(dāng)作結(jié)果,違背了因果關(guān)系的哲學(xué)原理。若反之,把因果關(guān)系定位為狹義的結(jié)果犯成立的要件之上,則因果關(guān)系在刑法中的地位卻又被大大削弱。
理論上另有一種因果關(guān)系不要論。該說認(rèn)為,法律上的行為概念是基于意欲或意欲可能性的舉止活動,這就圈定了刑法的評價(jià)范圍。刑法上的因果關(guān)系也必須在這個圈子里來確定。因果關(guān)系在把結(jié)果的預(yù)見或預(yù)見可能性作為前提的范圍內(nèi),同故意或過失有相同的界限,所以行為的因果關(guān)系理論不外乎是責(zé)任理論的某種體現(xiàn)而已,在刑法中并沒有必要來特別論述行為的因果關(guān)系。{3}我國刑法雖然與大陸法系國家刑法在體系上有重大區(qū)別,但是也有學(xué)者提出了類似結(jié)論的觀點(diǎn),認(rèn)為刑法因果關(guān)系完全依賴于危害行為和危害結(jié)果而存在,離開這兩種現(xiàn)象它什么都不是,根本沒有自身的存在。{4}這種因果關(guān)系只是在犯罪行為與犯罪結(jié)果之間起一種橋梁作用,或者說,它是為認(rèn)定犯罪行為和犯罪結(jié)果服務(wù)的。確定被告人刑事責(zé)任的客觀基礎(chǔ)是由因果關(guān)系聯(lián)結(jié)起來的犯罪行為與犯罪結(jié)果,而不是因果關(guān)系本身。既然犯罪因果關(guān)系不是追究刑事責(zé)任的客觀基礎(chǔ),當(dāng)然就不應(yīng)是犯罪客觀方面的構(gòu)成要件。{5}刑法因果關(guān)系論的危機(jī)由此可見一斑。
(二)各種學(xué)說在因果關(guān)系判斷上的危機(jī)
1大陸法系的條件說與相當(dāng)因果關(guān)系說
條件說認(rèn)為,只要在行為與結(jié)果之間存在“如無前者即無后者”這種條件關(guān)系,即認(rèn)為存在因果關(guān)系。由于具體結(jié)果通常由一系列條件所造成,按照這一學(xué)說,這些造成結(jié)果的原因均同值,因而它又被稱為“等價(jià)說”。德國理論上的通說及實(shí)務(wù)中所采均為該說。但是,徹底地依照條件說的公式,則殺人犯的母親也要對被害人的死亡結(jié)果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這顯然不合適。因此早期條件說被批評為有無限擴(kuò)大因果關(guān)系的范圍之嫌。為此,學(xué)者們提出了因果關(guān)系中斷論和禁止溯及的理論來解釋因果關(guān)系發(fā)展進(jìn)程中的異常現(xiàn)象,并就因果關(guān)系的斷絕、假定的因果關(guān)系、擇一的因果關(guān)系、重疊的因果關(guān)系等作了說明。但是這種條件理論受到了質(zhì)疑。因?yàn)闂l件說實(shí)際上只展示了一個邏輯規(guī)則,并沒有涉及具體的法律評價(jià)或認(rèn)定問題。按照大陸法系構(gòu)成要件符合性、違法性、有責(zé)性的犯罪論體系,首先要找出符合構(gòu)成要件的行為,而具有構(gòu)成要件符合性的行為并不是憑空想象的,人們不會動輒拿一個與危害結(jié)果完全不著邊際的行為去進(jìn)一步作法律上的判斷,而是在此之前需要為有可能成為構(gòu)成要件的行為劃定一個較小的范圍。如果直接運(yùn)用條件理論的邏輯規(guī)則來檢驗(yàn)因果關(guān)系的存在與否,事實(shí)上根本連判斷的對象都還不清楚。因此,條件理論本身并不能解決因果關(guān)系問題。
在條件關(guān)系基礎(chǔ)上,主張以社會經(jīng)驗(yàn)法則為依據(jù)的相當(dāng)因果關(guān)系論則在日本占據(jù)了通說地位。該說認(rèn)為,在實(shí)行行為與結(jié)果之間,根據(jù)社會生活經(jīng)驗(yàn),在通常情況下,某種行為產(chǎn)生某種結(jié)果被一般人認(rèn)為是相當(dāng)?shù)膱龊希撔袨榕c該結(jié)果之間就具有因果關(guān)系。這一學(xué)說由德國學(xué)者Kries在確率論的研究過程中創(chuàng)出,并作為法學(xué)上的概念提倡,其中“客觀的可能性”的概念是重要的概念要素。也就是使結(jié)果發(fā)生的可能性(或者危險(xiǎn))增加的條件是相當(dāng)原因。{6}(P29~30)按照這一理論,對因果關(guān)系的判斷應(yīng)采取__事后預(yù)測的客觀說,即事后站在法官的立場上,除行為人在行為當(dāng)時已認(rèn)識的情形以及客觀存在的全部事實(shí)外,即使是在行為后產(chǎn)生的情形,只要其有預(yù)見的可能,都必須予以考慮。{7}而日本目前理論界卻以行為時一般人能認(rèn)識到的情況以及行為人特別認(rèn)識到的情況作為相當(dāng)性判斷基礎(chǔ)的折衷說為主流,即在因果關(guān)系的內(nèi)容中納入了主觀的東西,將原本屬于責(zé)任判斷的內(nèi)容提前到構(gòu)成要件的判斷之中。由于它強(qiáng)調(diào)行為人的主觀認(rèn)識,因果關(guān)系的存在與否完全取決于行為人對某種事態(tài)是否有認(rèn)識,客觀的因果關(guān)系就必然隨行為人的意志而轉(zhuǎn)移,因果關(guān)系的判斷可以說是多余的,這就偏離了Kries所倡導(dǎo)的相當(dāng)因果關(guān)系理論。但客觀說也并不是沒有疑問的。其理論界限涉及“預(yù)見可能性”的問題。對結(jié)果客觀的預(yù)見可能性是出于限定行為者責(zé)任范圍的思想,實(shí)際上具體化則是困難的。不是以主觀的預(yù)見可能性,而是以虛構(gòu)的“一般人”作為判斷基準(zhǔn)的“客觀的預(yù)見可能性”的概念本身作為出發(fā)點(diǎn),很明顯只不過是一種幻想。{8}而且預(yù)見可能性的要求直接與過失的認(rèn)定相關(guān),隨著所謂“危險(xiǎn)社會的到來”與“體制社會的到來”,衡量行為對社會發(fā)展的進(jìn)步意義,一些在社會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危險(xiǎn)行為逐漸成為“被允許的危險(xiǎn)”,以預(yù)見可能容易導(dǎo)致肯定因果關(guān)系,無疑違背了法律基于衡平性的考慮而容許這種危險(xiǎn)存在的精神。
2英美法系的雙層次原因?qū)W說
在英美法系國家中,刑法因果關(guān)系理論同作為民事侵權(quán)行為責(zé)任條件之一的因果關(guān)系理論,是一脈相承的,即把原因分為兩層:第一層是“事實(shí)原因”,第二層次是“法律原因”。“事實(shí)原因”類似于大陸法系條件說圈定的原因,由“but—for”公式判斷,意指如果沒有被告的行為,就不會發(fā)生這一危害結(jié)果,則行為是結(jié)果發(fā)生的原因。但事實(shí)原因并非最終都能被認(rèn)定為刑法原因,還需要運(yùn)用一定的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限制篩選,找出其中應(yīng)當(dāng)讓行為人對結(jié)果負(fù)責(zé)的行為,這就是所謂“法律原因”。不難發(fā)現(xiàn),“法律原因”理論同相當(dāng)因果關(guān)系說的宗旨相同,都是為了限定刑法上因果關(guān)系范圍。然而,對于如何選擇法律原因,“近因說”、“普通觀念說”、“政策說”、“預(yù)見說”等各執(zhí)己見,表現(xiàn)出百家爭鳴的局面。{9}(P21)《美國模范刑法典》與近因說的觀點(diǎn)相近,同時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預(yù)見說的主張,但這兩種觀點(diǎn)都遭到了批判。《布萊克法學(xué)辭典》解釋“近因”認(rèn)為:“這里所謂的最近,不必是時間或空間上的最近,而是一種因果關(guān)系的最近。”{10}何謂因果關(guān)系的最近呢,其實(shí)質(zhì)要求也就在于危害行為對于危害結(jié)果所起的作用不能過分微弱,應(yīng)當(dāng)是足以令行為人承擔(dān)責(zé)任的。本來因果關(guān)系問題應(yīng)當(dāng)是在責(zé)任之前考慮的問題,近因說卻把確定因果關(guān)系等同于追究刑事責(zé)任,而要回答為什么可以讓行為人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時,又必然以因果關(guān)系的存在為前提,完全倒果為因。預(yù)見說的缺陷與前述預(yù)見可能的批判如出一轍,考察因果關(guān)系以行為人主觀上對所發(fā)生的結(jié)果是否有認(rèn)識或能認(rèn)識來決定,正如有人批評《模范刑法典》因果關(guān)系條款是“因果關(guān)系和主觀責(zé)任循環(huán)論證”。{11}而在判案實(shí)踐中,由于實(shí)用主義的影響,其具體判斷標(biāo)準(zhǔn)極富靈活性,隨著案情涉及的環(huán)境、當(dāng)事人的特定狀況、時代背景不同和倫理價(jià)值觀念的變異,法官可能會對相同的事實(shí)得出不同的結(jié)論。以致有的人對于刑法中是否存在一個能夠用來解決所有因果關(guān)系問題的基本原則都產(chǎn)生了懷疑。{9}(P22)
3我國刑法中的必然論與偶然論
因果關(guān)系的偶然性與必然性之爭,長期以來是我國刑法理論研究的一個熱點(diǎn)話題。必然論認(rèn)為刑法中的因果關(guān)系,只是危害行為與危害結(jié)果之間內(nèi)在的、合乎客觀規(guī)律的、必然的因果關(guān)系;偶然論認(rèn)為,刑法中的因果關(guān)系,包括危害行為與危害結(jié)果之間的必然的和偶然的因果關(guān)系。例如,甲男夜間在街道上攔截乙女,欲行,乙掙脫逃脫,甲在后面追時,乙被丙開的汽車軋死。持必然說的學(xué)者認(rèn)為,只有丙的行為同乙的死亡之間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guān)系,而持偶然說的學(xué)者認(rèn)為,甲的行為同乙的死亡之間存在偶然因果關(guān)系,甲亦應(yīng)對之承擔(dān)責(zé)任。還有學(xué)者提出了一個半因果關(guān)系的觀點(diǎn),認(rèn)為一個因果關(guān)系是指必然因果關(guān)系,半個因果關(guān)系是指一部分偶然因果關(guān)系,即高概率的偶然因果關(guān)系是刑法中的因果關(guān)系。{12}
這種劃分必然與偶然的做法,在近年來不斷被抨擊。必然性與偶然性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刑法上是難以說明的,因而我們只能求助于哲學(xué)上的范疇。但在哲學(xué)領(lǐng)域,必然與偶然是相對的概念,必然性的實(shí)現(xiàn)取決于大量偶然性的因素“,被斷定為必然的東西,是由純粹的偶然性構(gòu)成的,而所謂偶然的東西,是一種有必然藏在里面的形式”,{13}因而偶然的東西又是必然的。例如,甲的行為導(dǎo)致乙表皮__破裂,其后乙因傷口遭受破傷風(fēng)菌感染而死亡。在判斷甲的行為同乙的死亡是否有內(nèi)在的、本質(zhì)的、必然的聯(lián)系時,我們完全可以得出兩個截然不同的結(jié)論:一是由于輕傷害行為只是導(dǎo)致了表皮破裂,并不是致命傷,因此甲的傷害行為與某乙的死亡結(jié)果之間沒有內(nèi)在的、合乎規(guī)律的(必然的)因果聯(lián)系;二是由于某乙處于易受破傷風(fēng)菌感染的環(huán)境中,某甲的輕傷害行為導(dǎo)致了某乙表皮破裂,某乙因此遭破傷風(fēng)菌感染而死亡,因此,某甲的傷害行為與某乙的死亡結(jié)果就有內(nèi)在的、合乎規(guī)律的(必然的)因果聯(lián)系。{14}這就為任意出入人罪提供了可乘之機(jī)。不僅如此,必然論與偶然論之爭,在實(shí)踐中還導(dǎo)致我們很難將因果關(guān)系的客觀性原理貫徹始終。
高概率偶然因果關(guān)系之說更不可取。試想,某人意圖借飛機(jī)失事的偶然性來達(dá)到殺人的目的,給他人買飛機(jī)票,由于偶然性太弱,因而即使真的遇到機(jī)毀人亡的結(jié)果發(fā)生,也不會對行為人追究殺人罪的責(zé)任;倘若某人偶爾發(fā)現(xiàn)某架飛機(jī)有異常情況,估計(jì)很有可能在下次運(yùn)行中失事,這時為達(dá)殺人目的,而故意給被害人買來飛機(jī)票,我們就不能再以通常情況下飛機(jī)失事偶然性很小為由,不追究買機(jī)票者的殺人罪的刑事責(zé)任。{9}(P9~21)但這兩種情況究竟在因果聯(lián)系的方式上有什么不同?概率高低的標(biāo)準(zhǔn)實(shí)際上仍是不確定的,它只是建諸在社會觀念的認(rèn)識上,自然不可避免因果判斷上的差異。{{{[②]}}}
由此有學(xué)者主張,當(dāng)一事物蘊(yùn)含的可能性已經(jīng)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shí)性,那么這種現(xiàn)實(shí)性不但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統(tǒng)一的產(chǎn)物,而且也是必然性的最終反映,所以現(xiàn)實(shí)的都是必然的。因果關(guān)系是一種現(xiàn)實(shí)的聯(lián)系,所以因果關(guān)系是一種必然的聯(lián)系。{15}但這種觀點(diǎn)無助于解決任何問題,照此推斷,危害結(jié)果現(xiàn)實(shí)地發(fā)生了,行為與結(jié)果之間的聯(lián)系必定是必然的,因而就有因果關(guān)系,看似擺脫了必然性與偶然性的糾纏,實(shí)際上則是將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鏈條作了無限的延伸。
二、問題所在與理論反思
由以上論述可見,因果關(guān)系的研究似乎走上了一條不歸路。既沒有在基本問題上達(dá)成共識,也沒有提出現(xiàn)實(shí)可行的操作標(biāo)準(zhǔn),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筆者認(rèn)為,概而言之,在因果關(guān)系問題上,主要有以下問題需要解決:
第一,因果關(guān)系在刑法中是屬于構(gòu)成要件或犯罪構(gòu)成的問題,還是屬于責(zé)任的問題。刑法中應(yīng)當(dāng)研究因果關(guān)系,這一點(diǎn)是毫無疑義的。關(guān)鍵在于因果關(guān)系應(yīng)當(dāng)在哪一塊兒進(jìn)行研究。因果關(guān)系不要說的觀點(diǎn)實(shí)際上是基于因果判斷與責(zé)任的認(rèn)定在事實(shí)上重疊,主張沒有特別研究的必要,也就是將因果關(guān)系問題放在責(zé)任問題中一次性解決。相當(dāng)因果關(guān)系理論的定位,也有人與歸責(zé)問題聯(lián)系起來。如早在1949年梅茨格在其刑法教科書第三版中,已經(jīng)指出所謂“相當(dāng)性理論”,實(shí)屬歸責(zé)理論,而非因果理論。盡其所探討之主要內(nèi)容,并非造成結(jié)果發(fā)生之原因力之結(jié)構(gòu)與作用的經(jīng)驗(yàn)問題;而是另外根據(jù)可能性之經(jīng)驗(yàn),去判斷在何種因果情況之下,具有刑法上重要意義,而可以歸責(zé)于行為人的問題,從而可謂是歸責(zé)理論的方法論之一種。{16}如果屬于責(zé)任問題,確認(rèn)因果關(guān)系是否等于提供了追究刑事責(zé)任的客觀基礎(chǔ),則是接下來必須考慮的一個派生問題。
第二,因果關(guān)系的研究是否僅限于結(jié)果犯的場合。如前所述,結(jié)果犯的含義并不明確,危險(xiǎn)狀態(tài)是否結(jié)果犯所說的結(jié)果尚未達(dá)成共識。如果認(rèn)為結(jié)果僅僅是實(shí)害,對于危險(xiǎn)犯,就不必判斷因果關(guān)系,那么在刑法理論中自然可能用另外一種關(guān)系理論,去研究行為與危險(xiǎn)之間的聯(lián)系,這肯定沒有必要。所以,要承認(rèn)危險(xiǎn)也是一種結(jié)果。由于危害相對實(shí)害而言比較抽象,難于準(zhǔn)確衡量,所以行為與該危險(xiǎn)之間如何聯(lián)系,以及如何確定危險(xiǎn)的程度,都將是因果關(guān)系研究要面臨的問題。{17}而且,如果肯定只有結(jié)果犯才需要討論因果關(guān)系,邏輯上也行不通。因?yàn)樵跒榻o行為人的行為定一個確切罪名以前,是無法判斷該案是否屬于結(jié)果犯的情形的,這豈不是先定罪,再來研究該罪的要件嗎?此外,按照因果關(guān)系的本來含義,即原因與結(jié)果之間的聯(lián)系,也似乎有必要適當(dāng)擴(kuò)大因果關(guān)系的研究范圍。因?yàn)槿魏挝:π袨樽鳛樵颍急厝话l(fā)生一定的結(jié)果,而之所以會發(fā)動偵查、起訴、審判程序,就是因?yàn)樾谭ㄋWo(hù)的社會關(guān)系已經(jīng)受到了侵害或威脅,或者說法益遭到了侵犯。這是否意味著,因果關(guān)系的研究如果突破結(jié)果犯的界限,能夠擴(kuò)大到所有的犯罪情形呢?
第三,因果關(guān)系應(yīng)否區(qū)分為事實(shí)因果關(guān)系與法律因果關(guān)系。這一問題實(shí)際上是雙層次分析模式的思想產(chǎn)物。如前所述,英美國家采納了這種模式,由于該模式通過對事實(shí)原因的認(rèn)定,以基于經(jīng)驗(yàn)法則判斷的一般自然意義上的因果聯(lián)系甄別出具有刑法意義的事實(shí),然后通過對法律原因的篩選,實(shí)現(xiàn)最終將結(jié)果歸屬于行為的目的,步步限縮,因此受到了諸多學(xué)者的青睞。大陸法系的條件說與相當(dāng)因果關(guān)系說都不自覺地采納了這種兩步走的模式。如相當(dāng)因果關(guān)系說首先援引的就是條件理論,在將連條件關(guān)系都不具備的行為或事件排除以后,才運(yùn)用相當(dāng)理論,從剩下的事實(shí)中找尋相當(dāng)因果關(guān)系以決定責(zé)任歸屬。我國也有學(xué)者贊成這種雙層次模式。{18}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因果關(guān)系其實(shí)就是兩個事實(shí)之間有歸責(zé)意義的判斷,因果等于歸責(zé),它是一種評價(jià)概念。而如果承認(rèn)事實(shí)因果關(guān)系的概念,它僅僅是關(guān)于因果關(guān)系存在與否的概念,這種“關(guān)于條件是否存在的存在論的因果概念,必須與刑法意義上具有重要性的價(jià)值論的因果關(guān)系的概念區(qū)別開來”。{19}因?yàn)闊o論我們是否找出事實(shí)因果關(guān)系,它都不依人的主觀意志而存在著。有人中槍而亡,肯定有開槍的行為。刑法上所要解決的只是價(jià)值評判問題,也就是能否將死亡結(jié)果歸屬于某人的開槍行為,要求該行為人承擔(dān)責(zé)任。在這一意義上,有學(xué)者認(rèn)為“不需要判斷因果關(guān)系(指自然因果關(guān)系或事實(shí)因果關(guān)系——筆者注)”。事實(shí)因果關(guān)系果真能逐出因果關(guān)系的研究范圍嗎?
第四,因果關(guān)系是只有存在與否的問題,還是也存在定量分析的問題。即當(dāng)所謂的結(jié)果不僅有質(zhì)的規(guī)定性,而且還存在量上的差異時,對加重結(jié)果與行為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如果也應(yīng)當(dāng)確認(rèn),那么是否可以說因果關(guān)系不僅是為了解決定罪問題,而且也是為了解決定量問題,從而認(rèn)為刑法中的因果關(guān)系對于刑事責(zé)任的客觀基礎(chǔ)意義是一個變量,需要考慮具備什么程度的因果關(guān)系負(fù)多重程度的刑事責(zé)任。
第五,如何在實(shí)踐中正確認(rèn)定因果關(guān)系。這里涉及的問題比較多,例如,因果關(guān)系的判斷是應(yīng)當(dāng)抽象地提煉一個具有普適性的規(guī)則,還是應(yīng)當(dāng)具體地、個別地結(jié)合案情來把握;如何堅(jiān)持因果關(guān)系的客觀性原理;等。
上述問題應(yīng)當(dāng)說在中外刑法學(xué)中都有所涉及。此外,我國刑法理論還以哲學(xué)上的必然與偶然的原理為指導(dǎo),對因果聯(lián)系的形式進(jìn)行深究,這有無必要,也長期困擾學(xué)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顯然均非易事。而且由于我國的犯罪論體系與西方國家有較大差距,可能在某些問題上得出的結(jié)論會有所不同。限于能力,筆者在下文將只對我國刑法學(xué)中的因果關(guān)系論進(jìn)行反思,找出問題的癥結(jié)之所在。
在理清問題的頭緒之前,筆者認(rèn)為,首先應(yīng)當(dāng)明確刑法中研究因果關(guān)系究竟有何意義。只有對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任務(wù)有了認(rèn)識,才能緊緊圍繞著一宗旨來對我國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理論體系作出科學(xué)合理的評價(jià)。在筆者看來,刑法中研究因果關(guān)系的最終目的不是單純地為了肯定因果關(guān)系存在,理由有二:其一,從案件的處理過程來看,實(shí)際上遵循了“由果溯因”這樣一條道路,因此在由結(jié)果追溯至作為原因的行為時,因果聯(lián)系也就在事實(shí)上被予以了肯定。故刑法中的因果關(guān)系研究,更為重要的是一個法律評價(jià)問題,即如前所述,是為了解決結(jié)果責(zé)任的歸屬問題。詳言之,也就是能否要求行為人對具有事實(shí)因果關(guān)系的結(jié)果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承擔(dān)多大的責(zé)任。因而對所有的場合,都應(yīng)探討因果關(guān)系問題。其二,刑法旨在保護(hù)法益免受侵害,如果將因果關(guān)系研究的主旨囿于探討因果歷程的本體,絲毫不能界定侵害行為的責(zé)任范圍,也就無法實(shí)現(xiàn)刑法的任務(wù)。因此,我們在考察刑法上的因果關(guān)系時,應(yīng)當(dāng)“使其緊緊地圍繞著解決刑事責(zé)任的任務(wù),不可偏離這一既定的宗旨”。{20}
這是否意味著因果關(guān)系可以在刑事責(zé)任論中進(jìn)行研究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國的犯罪論體系仿照蘇聯(lián),采納了一種平面式的結(jié)構(gòu),也就是從犯罪客體、客觀方面、主體、主觀方面等分別判斷行為人的行為是否符合犯罪構(gòu)成要件,從而確定行為人的行為構(gòu)成犯罪。而一旦成立犯罪,刑事責(zé)任就是犯罪的必然結(jié)果,有犯罪就必然有刑事責(zé)任。如果將因果關(guān)系排除在犯罪構(gòu)成體系之外,那么在確認(rèn)犯罪成立以后,還要在刑事責(zé)任論中進(jìn)一步在客觀上說明將結(jié)果歸責(zé)于行為的可能性,無形中就承認(rèn)存在成立犯罪,但無需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的情況,明顯有違于犯罪與刑事責(zé)任關(guān)系的基本原理。而且按照這種假設(shè),既然刑事責(zé)任論中討論客觀可歸責(zé)性,根據(jù)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原則,主觀可歸責(zé)性的探討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主觀可歸責(zé)性不外乎就是要求行為人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如此一來,要么就會出現(xiàn)將故意過失的要求與故意過失的內(nèi)容分開來研究的局面,要么就是在犯罪論與刑事責(zé)任論中重復(fù)評價(jià)故意與過失,這都是不可取的。由此表明,行為與結(jié)果之間的因果關(guān)系,必須成為犯罪客觀要件的必要條件之一。{21}
遺憾的是,盡管我國學(xué)者基本上都贊成上述觀點(diǎn),但是卻往往又自覺或不自覺地把因果關(guān)系問題和刑事責(zé)任問題剝離開來,用哲學(xué)因果關(guān)系的研究代替對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研究,而完全置刑事立法精神與規(guī)范的價(jià)值判斷于不顧。筆者并不否認(rèn)刑法因果關(guān)系應(yīng)當(dāng)接受哲學(xué)因果關(guān)系的指導(dǎo),但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研究畢竟有別于哲學(xué)因果關(guān)系的研究。比如,一個女孩子因?yàn)槭俣詺ⅲ敲慈藗內(nèi)粘;谝蚬P(guān)系的判斷上,就會得出她的男友的拋棄與她死亡之間具有因果關(guān)系。但以刑法的視野觀察則不存在因果關(guān)系,因?yàn)轱@然不存在成立刑法上因果關(guān)系的犯罪行為。但是,如果是妻子因通奸而感到羞愧當(dāng)著丈夫的面上吊自殺,丈夫無動于衷而離去,雖然丈夫并不存在直接的殺人行為,但在刑法上卻認(rèn)為丈夫的不救助行為與妻子死亡之間具有因果關(guān)系,丈夫基于婚姻關(guān)系有救助的義務(wù),能救助而不救助,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的刑事責(zé)任。由此可以看出,與哲學(xué)上作為事物之間規(guī)律性的因果關(guān)系是事實(shí)上的、經(jīng)驗(yàn)上的、邏輯上的,而刑法上的因果關(guān)系卻是規(guī)范性的、有選擇的,是為了歸責(zé)而設(shè)置的。故刑法因果關(guān)系不能被哲學(xué)因果關(guān)系所代替,而只能將哲學(xué)上的因果關(guān)系原理按照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特殊性應(yīng)用于刑法。{22}
必然論與偶然論之爭顯然是力圖將哲學(xué)上的“必然性”與“偶然性”這對范疇引入刑法學(xué)中,但根據(jù)前述原理,考慮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特殊性,,必須實(shí)現(xiàn)哲學(xué)因果關(guān)系向刑法因果關(guān)系的轉(zhuǎn)移。如果一味地強(qiáng)調(diào)與哲學(xué)上的基本認(rèn)識保持協(xié)調(diào)一致,必然會將“必然”與“偶然”在哲學(xué)上的對立統(tǒng)一關(guān)系帶入刑法學(xué)。試問,這樣一對矛盾、甚至可以相互轉(zhuǎn)化的概念,怎么能“絕對性地”判斷行為人的行為是否構(gòu)成犯罪,應(yīng)否承擔(dān)刑事責(zé)任呢?因而,必然論與偶然論終究停留在哲學(xué)的層面,陷入了游移不定的怪圈。故筆者認(rèn)為,即使要討論哲學(xué)對刑法學(xué)的影響,也只能從方法論的層面來著手。
關(guān)于事實(shí)因果關(guān)系與法律因果關(guān)系的區(qū)分,筆者認(rèn)為在方法論上存在著一定的缺陷。這里所謂事實(shí)因果關(guān)系,也就是原因與結(jié)果之間依序發(fā)生的一種引起與被引起的關(guān)系。按照原因在先,結(jié)果在后的邏輯,則首先必須鑒明判斷的對象,即有可能成為原因的行為事實(shí)。原因從何而來呢?事實(shí)上它與刑法的評價(jià)毫無關(guān)系,而是來自我們自結(jié)果一幕一幕的觀念上倒推,甚至在必要時輔之以某種鑒定手段。例如,護(hù)士未經(jīng)作皮試即給小孩注射了青霉素,不久小孩死亡。從死亡結(jié)果追根溯源,可能與護(hù)士違反醫(yī)療規(guī)章制度的行為有關(guān),但解剖證明,死亡原因不是青霉素過敏,而是小孩患小葉性肺炎。很明顯,判斷護(hù)士的過失行為與小孩的死亡之間有無事實(shí)因果關(guān)系,如果一開始就從過失行為出發(fā),是無論如何也沒有辦法證明其是不是導(dǎo)致了死亡結(jié)果的。通常的情況是,在由果溯因之后,即肯定事實(shí)因果聯(lián)系的存在,根本沒有必要再回過頭來從原因出發(fā),證明原因能夠引起結(jié)果。因此,事實(shí)因果關(guān)系的判斷在邏輯上是逆序的,盡管這一步驟是解決定罪量刑問題的前提,但這一判斷完全是在案件進(jìn)入刑法意義的評價(jià)之前完成的,因而在刑法中討論事實(shí)因果關(guān)系問題毫無必要。
法律因果關(guān)系,一般認(rèn)為也就是明確地或蘊(yùn)含地規(guī)定在法律之中,作為司法機(jī)關(guān)定案標(biāo)準(zhǔn)的、定型的因果關(guān)系。{9}(P214)因而,理論上所要研究的,實(shí)際上是各種犯罪的法定犯罪構(gòu)成所要求的因果關(guān)系,而不是客觀上存在的事實(shí)因果關(guān)系如何具備了刑法上的意義,從而得以轉(zhuǎn)化為法律上的因果關(guān)系。那么,刑法上應(yīng)當(dāng)要求具備什么樣的因果關(guān)系呢?由于刑法條文中往往并沒有直接對法律因果關(guān)系進(jìn)行界定,因此人們往往根據(jù)犯罪應(yīng)受刑罰處罰性的特征,結(jié)合刑事政策、刑法的基本價(jià)值準(zhǔn)則、社會觀念等因素,自行就個案確認(rèn)事實(shí)因果關(guān)系在刑法上的意義,這就將刑法規(guī)范完全撇在了一邊,并且將應(yīng)然的問題與實(shí)然的問題混為一談。
筆者認(rèn)為,法律上的因果關(guān)系最本質(zhì)的特征應(yīng)當(dāng)是這種行為所導(dǎo)致的結(jié)果是法律規(guī)范所要加以非難的,因此主張將法律因果關(guān)系的概念轉(zhuǎn)換為客觀可歸責(zé)性的概念,這樣,一方面與因果關(guān)系論的任務(wù)保持了一致,另一方面也使得行為與結(jié)果的關(guān)聯(lián)緊扣法律規(guī)范,成為行為在規(guī)范上的標(biāo)志性特征。
三、出路:客觀可歸責(zé)性的初步構(gòu)想
由前述分析可知,筆者所倡導(dǎo)的客觀可歸責(zé)性實(shí)際上與法律因果關(guān)系是同一層次的概念。以往法律因果關(guān)系的認(rèn)定上存在將主觀方面的要素提前納入分析之中的弊病,在客觀歸責(zé)性的判斷中,為盡量避免這一現(xiàn)象發(fā)生,筆者認(rèn)為,可適當(dāng)借鑒德國學(xué)者提出的客觀歸責(zé)理論。
關(guān)于客觀歸責(zé)的整體概念,德國通說認(rèn)為它是行為人制造(或提高)了一個不被容許的風(fēng)險(xiǎn),并且此一風(fēng)險(xiǎn)在該當(dāng)與不法構(gòu)成要件的結(jié)果中實(shí)現(xiàn)。{23}也就是說,當(dāng)結(jié)果的發(fā)生是行為人所制造的被法律所排斥的風(fēng)險(xiǎn)的實(shí)現(xiàn)時,該結(jié)果對行為人而言才是可歸責(zé)的。因此,客觀歸責(zé)理論的基礎(chǔ)是從刑法規(guī)范本質(zhì)中推導(dǎo)出的認(rèn)識。{24}既然與刑法規(guī)范有著天然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這就同法律因果關(guān)系或者稱客觀可歸責(zé)性要求的法律性掛上了鉤。由于客觀歸責(zé)的判斷一般是通過其一連串的下位概念,如風(fēng)險(xiǎn)實(shí)現(xiàn)、風(fēng)險(xiǎn)降低、法律排斥風(fēng)險(xiǎn)、規(guī)范保護(hù)目的、自我負(fù)責(zé)的行為、容許信賴等的檢驗(yàn)來實(shí)現(xiàn)的,而不是從關(guān)于行為人的因素,如行為能力、預(yù)見可能等角度去考慮能否歸責(zé)的問題,所以,它又是名副其實(shí)的“客觀”歸責(zé)。
此外,筆者認(rèn)為,將這一理論潮流引進(jìn)我國刑法之中,與我們目前的刑法理論體系不會發(fā)生本質(zhì)的沖突。例如,我國刑法的犯罪構(gòu)成理論是從實(shí)質(zhì)上而非形式上來探討行為的罪與非罪問題的。以往人們?nèi)菀渍`解正當(dāng)防衛(wèi)、緊急避險(xiǎn)等行為之所以不是犯罪,并不是因?yàn)槠洳环戏缸飿?gòu)成,而是其從根本上不具有社會危害性。這種觀點(diǎn)實(shí)際上是受了大陸法系在犯罪成立與否的判斷上采取三階段論的影響,也就是在第二階段違法性的判斷中解決這一問題。但是我國的犯罪構(gòu)成的整個體系就是圍繞行為不法而展開的,不存在具備全部犯罪構(gòu)成而不構(gòu)成犯罪的情形。如果將客觀歸責(zé)性考慮為客觀方面的要件,運(yùn)用風(fēng)險(xiǎn)降低歸責(zé),上述問題就迎刃而解。所謂風(fēng)險(xiǎn)降低,就是行為制造的禁止危險(xiǎn)減少了行為對象已經(jīng)面臨的危險(xiǎn)的程度,換言之,行為對象所處的狀況因?yàn)樾袨槿说慕槿攵玫礁纳疲蛊滹L(fēng)險(xiǎn)降低,就應(yīng)當(dāng)排除結(jié)果歸責(zé),因?yàn)槿魏畏啥疾粦?yīng)禁止減少損害的行為。例如,甲持木棍從后面攻擊乙的頭部,丙見狀為救某甲,推了乙一把,致乙骨折。此例中,丙的行為就是降低危險(xiǎn)的行為,因而盡管其行為與乙骨折的結(jié)果之間有事實(shí)上的因果關(guān)系,但卻不能將該結(jié)果歸責(zé)于丙,從而丙的緊急避險(xiǎn)行為不是犯罪。
那么,如何在德國學(xué)者提出的客觀歸責(zé)論基礎(chǔ)之上,為我國刑法犯罪客觀方面中客觀可歸責(zé)性的要件創(chuàng)設(shè)一套切實(shí)可行且兼?zhèn)淇陀^性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呢?根據(jù)客觀歸責(zé)論,其基本內(nèi)容包括三點(diǎn):(1)行為人的行為對于行為客體(對象)制造了不被容許的風(fēng)險(xiǎn);(2)這個風(fēng)險(xiǎn)在具體的結(jié)果中被實(shí)現(xiàn)了;(3)這個結(jié)果存在于構(gòu)成要件的效力范圍內(nèi)時,由這個行為所引起的結(jié)果,才可以算作行為人的結(jié)果,而被歸責(zé)于行為人。{25}可見,客觀歸責(zé)性的認(rèn)定,是由行為及至結(jié)果的過程,這與哲學(xué)上對因果關(guān)系的時間先后性的認(rèn)識不謀而合。這一理論應(yīng)當(dāng)說已經(jīng)為犯罪的認(rèn)定確立了一個基本原則,但實(shí)踐中同時還派生出了一系列規(guī)則,從反面來過濾那些因不具客觀歸責(zé)性而不構(gòu)成犯罪的情形。筆者認(rèn)為,這些規(guī)則,具有排除結(jié)果責(zé)任之可歸責(zé)性的示范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以往對刑法上因果關(guān)系的判斷過于抽象的標(biāo)準(zhǔn),因而也大體可以為我們所吸納。概括地講,客觀歸責(zé)性要件主要包括以下內(nèi)容:
(一)被禁止的危險(xiǎn)
客觀歸咎理論的基礎(chǔ)是禁止的危險(xiǎn)。{26}(P53)隨著科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展以及人類生活結(jié)構(gòu)的復(fù)雜化,危險(xiǎn)可謂越來越多。但有些危險(xiǎn)行為又是社會生活必不可少的,于是理論上認(rèn)為,即使這種行為發(fā)生了法益侵害的結(jié)果,在一定范圍內(nèi)也應(yīng)當(dāng)允許。這就是被允許的危險(xiǎn)。因此,行為人雖然以其行為而制造了風(fēng)險(xiǎn),甚至引發(fā)了危害結(jié)果,由于行為人所制造的風(fēng)險(xiǎn)本身并不是法律所排斥的,因而該結(jié)果對行為人來講具有不可歸責(zé)性。如前文所舉事例,某人意圖借飛機(jī)失事達(dá)到殺人目的,而贈送機(jī)票給他人,讓他人乘坐飛行,結(jié)果飛機(jī)果真失事,他人死亡。由于航線運(yùn)營的風(fēng)險(xiǎn)人們早已習(xí)以為常,法律基于衡平性的考慮而容許這種風(fēng)險(xiǎn)存在,因而以行為人而言,制造這樣的風(fēng)險(xiǎn),即使在某一種動機(jī)狀態(tài)下是一種不道德,但是客觀上這是一種權(quán)利,所以法律不能加以非難。{27}至于哪些危險(xiǎn)是被容許的,應(yīng)當(dāng)立足于法律條文背后所隱藏的禁止性規(guī)范,凡是法律沒有禁止的,都可視為被容許的危險(xiǎn)。
(二)危險(xiǎn)實(shí)現(xiàn)關(guān)聯(lián)論
結(jié)果的發(fā)生只有是行為人所制造的危險(xiǎn)本身所致者,才能認(rèn)為結(jié)果對行為人而言具有可歸責(zé)性。當(dāng)結(jié)果的發(fā)生不是行為人所制造的風(fēng)險(xiǎn)的實(shí)現(xiàn),而是超出了因果發(fā)展的常態(tài)時,一般不能認(rèn)為最終的結(jié)果之于行為人具有可歸責(zé)性。但如果盡管客觀的因果發(fā)展發(fā)生了變化,但行為的結(jié)果仍然包括在行為所造成的禁止的危險(xiǎn)中,則不影響歸咎[②]。具體判斷上,可參照以下標(biāo)準(zhǔn):
1規(guī)范違反行為并沒有使危險(xiǎn)增加的場合,不認(rèn)為行為具有可歸責(zé)性。例如,司機(jī)超速駕車,發(fā)生交通事故,被害人死亡。但縱然司機(jī)遵守規(guī)范,以被容許的速度行車,結(jié)果也會發(fā)生,因?yàn)閷?shí)際上是被害人突然從路邊沖出,這說明司機(jī)的行為并沒有使危險(xiǎn)的程度增加,死亡結(jié)果不是司機(jī)所制造的危險(xiǎn)的實(shí)現(xiàn),司機(jī)不構(gòu)成犯罪。
2介入意外事件的場合,如果意外事件推動了結(jié)果的發(fā)生,則行為人的危險(xiǎn)行為與最終結(jié)果之間,應(yīng)被認(rèn)為不具客觀可歸責(zé)性。例如甲意圖殺乙,乙受重傷后住院,醫(yī)院失火,乙被燒死。因?yàn)橐业乃劳鲭m不能歸責(zé)于行為人,但是重傷結(jié)果是可以歸責(zé)于乙的殺人行為的,故乙應(yīng)負(fù)故意殺人未遂的刑事責(zé)任。
3遭遇潛在的危險(xiǎn)源的類型,即制造的危險(xiǎn),遭遇被害者的特異體質(zhì)和疾病等潛在的危險(xiǎn)源的場合,多根據(jù)“危險(xiǎn)的繼續(xù)作用”的程度、第一次的危險(xiǎn)遭遇潛在的危險(xiǎn)的概率、潛在的危險(xiǎn)源的結(jié)果惹起力的大小,決定有無危險(xiǎn)實(shí)現(xiàn)的關(guān)聯(lián)。{6}(P50)譬如,由于藥劑師的過失而導(dǎo)致維他命中毒的病人在住院過程中患重感冒死亡。這一死亡結(jié)果能否歸咎于藥劑師的行為,取決于死亡是否由于中毒導(dǎo)致的體質(zhì)嚴(yán)重削弱引起的。如果是,藥劑師應(yīng)對死亡結(jié)果承擔(dān)過失的責(zé)任;如果這一結(jié)果即使沒有中毒導(dǎo)致的體質(zhì)衰弱同樣會發(fā)生,藥劑師只承擔(dān)過失傷害的責(zé)任。{26}(P56)
4如果行為人實(shí)施了侵害行為以后,經(jīng)過很多年,才因?yàn)榍趾Φ暮筮z癥導(dǎo)致結(jié)果發(fā)生的,應(yīng)當(dāng)否定是原風(fēng)險(xiǎn)的實(shí)現(xiàn)。如因交通事故而失去一足的人,20年后在山道上因行動不便墜落山崖死亡的案例,由于侵害人此前已就造成被害人行動不便承擔(dān)了責(zé)任,所以其殘存的危險(xiǎn)不再是結(jié)果發(fā)生的法律上的原因。
5對于介入被害,人自己的危險(xiǎn)行為所造成之后,果,就先前的行為人而言,不具有可歸責(zé)性。如某甲販賣給某乙,乙自行注射,結(jié)果毒發(fā)而死。由于乙的死亡結(jié)果與甲販賣的行為之間介入了乙自己有意識的危害行為,也就是說損害的發(fā)生是因?yàn)楸缓θ俗约河幸庾R投身進(jìn)入的風(fēng)險(xiǎn)所實(shí)現(xiàn)的,因而行為人只需對販賣行為負(fù)責(zé),而無需對死亡結(jié)果負(fù)責(zé)。這里需要注意的是,被害人自己的危險(xiǎn)行為應(yīng)當(dāng)表明他對危害結(jié)果并不在意,如果表面上看雖然介入了被害人的危險(xiǎn)行為,但是被害人并不愿意承擔(dān)這種后果,危險(xiǎn)行為會否發(fā)生完全取決于行為人,則先前的行為人仍要對風(fēng)險(xiǎn)的實(shí)現(xiàn)負(fù)責(zé)。例如,渡船已經(jīng)超載,但乘客執(zhí)意要乘坐,渡船違章行駛,發(fā)生沉船事故的,并不能免除船長的責(zé)任。[③]
另外,如果最終結(jié)果的發(fā)生為先前行為所制造的危險(xiǎn)所包括,并且法律對這種情形作了預(yù)想,從而該后果成為犯罪構(gòu)成要件的內(nèi)容,也應(yīng)將該結(jié)果歸屬于行為人。例如,行為人婦女后,該婦女羞愧難當(dāng)而自殺身亡。將行為歸屬于行為人讓其承擔(dān)責(zé)任是毫無疑問的。而根據(jù)我國刑法規(guī)定“,造成其他后果的”是罪的加重構(gòu)成,對此情形應(yīng)處以更重的刑罰。既然法律已經(jīng)將這種介入被害人自己的行為而導(dǎo)致最終結(jié)果發(fā)生的情形作了規(guī)定,那么應(yīng)當(dāng)認(rèn)為被害人死亡也是行為人制造的風(fēng)險(xiǎn)的實(shí)現(xiàn),應(yīng)當(dāng)要求行為人承擔(dān)較重的法定刑。由此可見,客觀可歸責(zé)性事實(shí)上是有程度之分的,具體應(yīng)將何種結(jié)果歸屬于行為人,承擔(dān)多重的刑罰應(yīng)結(jié)合刑法的有關(guān)規(guī)定作出評判。
6對于介入第三人的危險(xiǎn)行為而導(dǎo)致結(jié)果發(fā)生的情形,先前的行為人也不應(yīng)當(dāng)對后一結(jié)果負(fù)責(zé)。這類似于因果關(guān)系中斷。德意志聯(lián)邦裁判所1953年的所謂尾燈事件{6}(P55)即為一例。被告人凌晨駕駛的貨車因?yàn)槲矡艄收隙幻钔S诟咚俟贰>鞛榱撕蠓降陌踩珜㈦娡仓糜谲嚨溃⒁桓鎸⒇涇囻傊料乱粋€加油站,警車將尾隨保護(hù),然后警察熄滅電筒準(zhǔn)備出發(fā)時,后方駛來另一輛貨車,正好與被告的車撞上,司機(jī)死亡。本案中,被告的過失雖然具有引起事故的危險(xiǎn),但由于介入了警察的指令性行為,被告正在致力減少危險(xiǎn),則警察對危險(xiǎn)的防御應(yīng)當(dāng)負(fù)起相應(yīng)的責(zé)任,而正是由于警察的過失行為的介入,造成了事故的發(fā)生,因此,死亡結(jié)果不能客觀歸咎于被告人的行為。
德日刑法理論關(guān)于客觀歸責(zé)理論還有重要一點(diǎn),即規(guī)范保護(hù)目的論。也就是認(rèn)為“結(jié)果之發(fā)生,若不屬于所侵害規(guī)范之保護(hù)范圍內(nèi)者,則不得歸責(zé)之。”{28}典型的事例就是,小偷深夜入室行竊,被主人發(fā)覺,于是下樓察看,但不慎滾下樓梯,摔成重傷。小偷的盜竊行為制造了主人摔傷的風(fēng)險(xiǎn),而且這一風(fēng)險(xiǎn)也事實(shí)上實(shí)現(xiàn)了。然而有關(guān)入室盜竊的法律規(guī)范的目的并不是在于保護(hù)人們的身體健康,而僅是為了保護(hù)財(cái)產(chǎn),因此重傷結(jié)果不得歸責(zé)于小偷的盜竊行為。筆者認(rèn)為,這一理論是存在問題的。因?yàn)槲覀冎蕴接懩芊駥⒅貍Y(jié)果歸責(zé)于行為人,就是要確認(rèn)行為人的行為是否可以成為傷害罪的傷害行為,而首先拿盜竊的有關(guān)規(guī)范加以考慮,自然得出的是否定的結(jié)論。而且,誠如有學(xué)者指出的:“規(guī)范的保護(hù)目的論的‘規(guī)范’,是指行為規(guī)范還是指‘注意規(guī)范’是個問題。”{29}此外,探究規(guī)范的目的,也就是探究立法者的目的,不免涉及到主觀的東西,因此,從堅(jiān)持客觀可歸責(zé)性的“客觀”出發(fā),筆者認(rèn)為,最好將這一理論摒棄在理論框架之外。
應(yīng)當(dāng)注意的是,期望由客觀可歸責(zé)性來為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zé)任提供完全根據(jù)是不可能的,查明存在著客觀可歸責(zé)性,只是解決了犯罪構(gòu)成的客觀方面問題,為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zé)任提供了客觀基礎(chǔ)。在此基礎(chǔ)上,是否追究行為人的刑事責(zé)任,還需根據(jù)行為人是否具備犯罪主體條件和主觀罪過條件等而定。
【注釋】
[①]這與國外公害犯罪場合所使用的疫學(xué)因果關(guān)系是不同的。疫學(xué)因果關(guān)系雖然也強(qiáng)調(diào)高度概然性,但其概率高低的判斷是以統(tǒng)計(jì)資料為基礎(chǔ)的。
[②]這就是以往刑法中所提到的因果關(guān)系的錯誤。
[③]同樣的道理,筆者認(rèn)為,如果乘客催促出租車司機(jī)開快車,違章駕駛,發(fā)生交通事故致他人死亡的,出租車司機(jī)知道超速的危險(xiǎn)性,他可以決定要不要超速、要超速到何種程度,司機(jī)應(yīng)負(fù)交通肇事罪是無疑的。至于乘客,如果其對司機(jī)處于優(yōu)勢地位,可以認(rèn)為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這種危險(xiǎn)性,因而也能構(gòu)成犯罪。至于是不是構(gòu)成共同犯罪,則另當(dāng)別論。
參考文獻(xiàn)
{1}{日}大冢仁.犯罪論的基本問題{M}.馮軍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xué)出版社,1993.96.
{2}侯國云,梁德新.論因果關(guān)系在刑法中的地位{J}.政法論壇,1996,(6):15.
{3}{日}瀧川幸辰.犯罪論序說(上)(王泰譯){A}.高銘暄,趙秉志.刑法論叢(第3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78.
{4}馬克昌.犯罪通論{M}.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9.212.
{5}張明楷.犯罪論原理{M}.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1.205.{6} 山中敬一.日本刑法學(xué)中相當(dāng)因果關(guān)系的危機(jī)與客觀歸屬論的抬頭{A}.罪與刑——林山田教授六十歲生日祝賀論文集{C}.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
{7}木村龜二.刑法學(xué)詞典{Z}.顧肖榮等譯.上海: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91.150.
{8}山中敬一.關(guān)于我國客觀歸屬論的展望{J}.(日本)現(xiàn)代刑事法,1999,(8):5.
{9}張紹謙.刑法因果關(guān)系研究{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1998.
{10}布萊克法學(xué)辭典{Z}.1103.
{11}儲槐植.美國刑法{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7.69.
{12}儲槐植.刑事一體化與關(guān)系刑法論{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7.263.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240.
{14}王敏遠(yuǎn).對刑法中因果關(guān)系理論的反思{J}.法學(xué)研究,1989,(5):49.
{15}楊興培.刑法新理念{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xué)出版社,2000.186~187.
{16}EdmendMezger,Strafrecht,3.Aufl.1949,S.122;Jescheck,a.a.O.S.256.,轉(zhuǎn)引自蘇俊雄.從刑法因果關(guān)系學(xué)說到新客觀歸責(zé)理論之巡歷{J}.法學(xué)家,1997,(3):74.
{17}童德華.刑法中因果關(guān)系的層次及其標(biāo)準(zhǔn){J}.政治與法律,2001,(5):16.
{18}儲槐植,汪永樂.刑法因果關(guān)系研究{J}.中國法學(xué),2001,(2):153.
{19}甘雨沛,何 鵬.外國刑法學(xué)(上){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4.293.
{20}趙廷光.中國刑法原理(總論卷){M}.武漢: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2.311.
{21}李光燦.刑法因果關(guān)系論{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86.31.
{22}侯國云.刑法因果新論{M}.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58.
{23}HaftAT1992S.62ff.;RoxinAT-1199411/36ff.;WesselsAT1994RN.178ff,轉(zhuǎn)引自黃榮堅(jiān).論風(fēng)險(xiǎn)實(shí)現(xiàn){A}.刑罰的極限{C}.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1999.141.
{24}{德}漢斯·海因里希·耶塞克.德國刑法教科書(總論){Z}.徐久生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350.
{25}駱克信(Roxin).客觀歸責(zé)理論(許玉秀譯){J}.(臺北)政大法學(xué)評論,(50):13.
{26}李海東.刑法原理入門{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7}黃榮堅(jiān).不作為犯與客觀歸責(zé){A}.刑法問題與利益思考{C}.臺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1999.153.
第9篇:刑法哲學(xué)論文范文
在此,筆者試圖通過引入本體哲學(xué)思想,從本體論的角度加強(qiáng)對國際法基本理論的研究并實(shí)現(xiàn)創(chuàng)新。新的世紀(jì)是中華民族實(shí)現(xiàn)民族復(fù)興的關(guān)鍵時期,中國需要一個穩(wěn)定、和諧的國際環(huán)境,也希望在謀求自身發(fā)展的同時促進(jìn)國際和平與合作,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確實(shí)希望能夠和平地崛起。新世紀(jì)的國際法應(yīng)該為這種正義的、善意的訴求提供充分的支持。另一方面,國際法在本體論上至今很大程度仍然是西方文明的產(chǎn)物,發(fā)展中國家對國際法的參與主要限于具體實(shí)踐層面。過去一百五十多年尤其是近二十多年以來,中國國際法學(xué)界主要是學(xué)習(xí)與運(yùn)用國際法,在國際法的發(fā)展上面,尤其是法哲學(xué)意義的發(fā)展上貢獻(xiàn)不多。然而,若要真正擔(dān)當(dāng)起一個負(fù)責(zé)任大國角色的話,中國就應(yīng)該在國際法理論,尤其是本體論上作出自己的貢獻(xiàn)。我們應(yīng)該把延綿不斷的中華文明的優(yōu)秀理念介紹給國際社會,實(shí)現(xiàn)與西方文明的交流與結(jié)合,促進(jìn)國際法本體論的再次質(zhì)變。
一、本體哲學(xué)思想簡介
本體,西文的對應(yīng)詞為Noumenon,復(fù)數(shù)形式為Noumena。在西方哲學(xué)史上,本體一詞一般用來指世界本質(zhì)、實(shí)體或存在體。古往今來,有諸多哲人都涉足了這類本體論域的、純粹關(guān)于世界本質(zhì)的思考,只是他們各自使用的術(shù)語長期以來并不是一致的。“本體”的詞源最早可追溯到希臘文noein(思維)一詞,該詞的意思是“被思想的事物”或“理智的事物”,是指相對于現(xiàn)象的可理解對象或終極實(shí)在的事物。由此可見,現(xiàn)象與本體的區(qū)別古已有之[1]。古希臘哲學(xué)家以自然界的感性事物為世界本體,如水、火、氣等;米利都學(xué)派首先提出世界本原問題,開創(chuàng)了本體論研究;柏拉圖的“靈魂回憶”、“純粹理念”等理論實(shí)際上也屬于本體論域的純粹思考,他還在其“形式論”中充分討論了本體與現(xiàn)象的區(qū)別問題。巴門尼德最早以抽象的“存在”為本體。亞里士多德則首先提出本體范疇,并以本體(或曰實(shí)體)為其第一哲學(xué)的最高對象,這些觀點(diǎn)見諸他在《形而上學(xué)》、《范疇篇》等著作中提出的“普遍形式”、“本質(zhì)定義”等理論之中。亞里士多德的本體概念影響了近代的一些哲學(xué)家的本體觀,如斯賓諾莎的實(shí)體論等。
“本體”這一概念的明確歸功于康德,或者我們可以干脆地說,“本體”(Noumenon)這個詞就是康德造出來的。德語中本來有一個表示本體的詞:Ding-an-sich,但是康德在采用這個詞的同時,又對應(yīng)于“現(xiàn)象”一詞的詞根(menon),使用了一個新的詞:Noumenon,顯然有其特殊的含義。在其所著的《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指出:“表現(xiàn)物,只要依據(jù)范疇的統(tǒng)一性作為對象被思維,稱之為現(xiàn)象。但如果我設(shè)想某物,它僅是知性的對象,而卻作為這樣的,盡管不是感性的直觀,而能將(作為)智性的直觀給予;則這樣的一類某物當(dāng)名為本體(只能用智力了解)。”“本體之概念———它關(guān)涉于不應(yīng)被思考作是感性對象,而是只通過純理智認(rèn)作是物自身的東西———是絕無矛盾的概念。”可見,康德創(chuàng)造這個術(shù)語,是為了把現(xiàn)象與本質(zhì)區(qū)分開來,把探討現(xiàn)象的認(rèn)識論與探討本質(zhì)的形而上學(xué)區(qū)分開來。根據(jù)康德的界定,“本體”這一概念主要有以下幾個意思:第一,它是超感覺、超經(jīng)驗(yàn)、超現(xiàn)象的對象,是離開意識而獨(dú)立存在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是感性的來源;第二,它是認(rèn)識的界限,防止感性直觀超出現(xiàn)象界而擴(kuò)大到物自身;第三,它是理性的理念。
本體論,英文的對應(yīng)詞為Ontology,德文與法文的對應(yīng)詞均為Ontologie。該詞最初的源頭是希臘文logos(理論)和ont(是,或存在),后來又有拉丁文Ontos作為其詞源,意指存在物或存在者。德國學(xué)者郭克蘭紐最早使用了“本體論”一詞以指代形而上學(xué)。法國學(xué)者笛卡爾把研究本體論的哲學(xué)稱作“形而上學(xué)本體論”。克勞伯把本體論稱為“第一科學(xué)”,沃爾弗則叫它作“第一哲學(xué)”。應(yīng)該指出的是,在西文中,“本體”與“本體論”兩個概念之間并不像中文表述那樣具有一目了然的、嚴(yán)格對應(yīng)的聯(lián)系。西文中的“本體論”不僅包括關(guān)于本體的理論,還包括形而上學(xué)的一般性或理論性部分,甚至有時被用來指整個形而上學(xué)。無怪乎有的學(xué)者會認(rèn)為,嚴(yán)格地說ontology應(yīng)譯為“是論”或“存在論”。但就本文的討論范圍而言,“本體論”僅需取其最狹義的含義。因此,本體論是關(guān)于存在及其本質(zhì)的抽象性質(zhì),或曰最終本性的學(xué)說,簡言之,它就是關(guān)于本體的學(xué)說。
二、本體哲學(xué)思想之揚(yáng)棄
本體哲學(xué)思想對中國當(dāng)代法哲學(xué)的發(fā)展具有借鑒意義。然而,欲將“本體”、“本體論”這一組概念引入法哲學(xué)的領(lǐng)域中,必須對這一組概念做出適應(yīng)于時代的揚(yáng)棄。這其中的關(guān)鍵又在于對“本體”的揚(yáng)棄,因?yàn)楸倔w論就是關(guān)于本體的學(xué)說,一旦恰當(dāng)?shù)亟缍吮倔w,本體論的界定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了。對于康德的本體概念,可以吸收以下精華部分:第一,本體是獨(dú)立于意識的、關(guān)于事物本質(zhì)的抽象存在,它是對事物的具體認(rèn)識(既可以是理性的又可以是感性的)的來源,我們只有透過現(xiàn)象、超越具體理性才能認(rèn)識它。第二,本體劃出了對事物的本質(zhì)認(rèn)識與非本質(zhì)認(rèn)識的界限,后者不能夠取代本體成為所謂的“基本理論”。第三,本體是根本的、純粹的理性理念,它可以指導(dǎo)具體認(rèn)識和行為。
當(dāng)然,康德本體觀的以下方面是應(yīng)該予以否定的:第一,本體不可知。列寧曾指出,從這個意義上講康德是唯心主義者。的確,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diǎn),一切存在,包括關(guān)于事物本質(zhì)的存在,都是可以認(rèn)識的。當(dāng)時康德提出本體不可知,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通過論證作為絕對實(shí)體的上帝的不可知,將宗教勢力排斥在認(rèn)識論之外,保持自然科學(xué)的獨(dú)立性。但是,如今時過境遷也就沒有這個必要了。第二,本體論與認(rèn)識論的絕對對立。在辯證唯物主義看來,物質(zhì)決定意識,意識反映物質(zhì),不存在不可知的事物,只是可知的程度與方式不同。正因?yàn)槿绱?作為對先前哲學(xué)(包括康德哲學(xué))的揚(yáng)棄的唯物辯證法沒有采取本體論與認(rèn)識論絕對對立的立場。本體,在我們看來,一方面是一種抽象的客觀存在,另一方面是可以被認(rèn)識并用來指導(dǎo)實(shí)踐的。因此,我們這里引入的本體及本體論概念,是一個經(jīng)過唯物辯證法批判的概念,是一個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概念。本體,是指獨(dú)立于意識的、關(guān)于事物本質(zhì)的抽象存在,它是對事物的具體認(rèn)識的來源,它可以被認(rèn)識并被用來指導(dǎo)實(shí)踐。本體論就是關(guān)于本體的學(xué)說和理論。
三、本體哲學(xué)思想在中國國際法哲學(xué)中的運(yùn)用
在法學(xué)領(lǐng)域中引入本體概念,并非筆者的獨(dú)創(chuàng)。近年來,很多學(xué)者都在這方面做了有益的嘗試。
首先,來看法理學(xué)領(lǐng)域的情況。張文顯先生在法理學(xué)中引入并界定了“法的本體”概念。他認(rèn)為,任何一門科學(xué)的出發(fā)點(diǎn)都是它的研究對象的本體性質(zhì)。法律本體就是法這一社會存在物及其本質(zhì)、關(guān)系和規(guī)律。關(guān)于這些問題的理論研究就是法的本體論。法的本體論涉及法律的本質(zhì)是什么、法律的基本特征有哪些、法律內(nèi)部的構(gòu)成要素和結(jié)構(gòu)如何、法律的存在形式是怎樣的、法的核心內(nèi)容是什么等重要問題。關(guān)于法律本體問題的回答歷來是劃分各種不同流派的主要依據(jù)[2]。葛洪義先生指出,法的本體論是指關(guān)于法律現(xiàn)象究竟是什么的學(xué)說和觀點(diǎn),只有弄清本體論與認(rèn)識論的關(guān)系,才能正確把握方法論問題的要害和關(guān)鍵[3]。上述界定都是具有合理性的對本體概念的解釋。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并沒有批判性地回溯本體概念的哲學(xué)來源,而僅僅著重于在現(xiàn)代法理學(xué)的語境中賦予本體概念以某種重要意義,因而與本文所界定的法的本體概念有一定區(qū)別。相比之下,本文的法律本體概念范圍更為狹窄一些,只有直接關(guān)乎本質(zhì)的關(guān)系與規(guī)律(而不是所有基本關(guān)系與規(guī)律)才能進(jìn)入本文視野。丁以升先生強(qiáng)調(diào),法律的本體問題是法哲學(xué)領(lǐng)域的重要理論范疇。他介紹并采納了古希臘米利都學(xué)派的觀點(diǎn),認(rèn)為本體是指本原物,一方面,它是所有其他事物的出發(fā)點(diǎn)與范型;另一方面,其他事物的存在的合理性必須以它為基礎(chǔ),并向它復(fù)歸[4]。此外,還有一些學(xué)者在一般意義上使用了本體概念,他們沒有專門解釋這一概念,而僅以之說明某些關(guān)于“法本原”、“法自身”的基本范疇。
其次,來看部門法哲學(xué)領(lǐng)域的情況。陳興良先生在刑法中使用了本體概念。他認(rèn)為,所謂“本體刑法學(xué)”,是一種自在于法條、超然于法條的法理,它不以法條為本位而以法理為本位。法理的邏輯演繹取代了法條的規(guī)范詮釋[5]。不難發(fā)現(xiàn),這個“本體刑法學(xué)”概念雖然也具有偏理論、重思辨、超實(shí)在法的特征,但它實(shí)際上不過是借“本體”來談理論,將刑法法理在一種廣義的本體論的語境下單獨(dú)拿出來討論而已。直言之,“本體刑法學(xué)”就是理論刑法學(xué)。應(yīng)該說,這種做法代表了目前在部門法學(xué)中較為常見的對“本體”一詞的使用模式,即直觀地“借用”。
再次,來看國際法學(xué)領(lǐng)域的情況。李家善先生在介紹自然法與萬民法的關(guān)系時,曾經(jīng)稱Noumena為“本體論”[6]。顯然,他無意于仔細(xì)探究與嚴(yán)格區(qū)分“本體”(Noumena)和“本體論”(Ontology)概念。王鐵崖先生在討論國際法的淵源與國際法一般原則的關(guān)系時,使用了“國際法本體”的概念,他傾向于認(rèn)為國際法的原則就是國際法的本體,國際法本體是對應(yīng)于國際法淵源的范疇[7]。這也是一種對本體概念的直觀借用。事實(shí)上,大多數(shù)學(xué)者在論述國際法的理論問題時,都沒有使用“本體”概念;而少數(shù)有意或無意使用了這一概念的學(xué)者,也并未注意去推敲“本體”概念的真正內(nèi)涵。
最后應(yīng)該指出,即使是國外的學(xué)者,也鮮有使用帶有濃厚哲學(xué)氣息的本體(Noumena)概念來討論國際法乃至法學(xué)問題的,他們至多在有限的場合使用了廣義上的本體論(Ontology)概念。總的來說,目前在中國法哲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對本體概念的使用,主要包括三種情況。第一種,同時也是最常見的一種,是直觀性地借用,即不去界定本體的范疇,而是利用“本體”這個詞帶給人的直觀印象(偏理論、重本原、超實(shí)在等),闡述自己所關(guān)心的問題;另一種是解釋性借用,即先在某一法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對本體做出自己的界定,然后再加以使用;最后一種則是引用舊有的哲學(xué)(包括法哲學(xué))的本體觀,這多半是出于介紹的需要。與前人的做法不同的是,本文所要從事的,是對本體概念的批判性、系統(tǒng)性使用。筆者認(rèn)為,法的本體,是關(guān)于法的本質(zhì)的抽象存在,是一切關(guān)于法的現(xiàn)象與意識的來源。法的本體論,是探討法的本質(zhì)的抽象理論,簡言之,它就是關(guān)于法的本體的理論。法的本體論是法哲學(xué)的最基本組成部門,它絕對不等同于我們一般所說的“法的基本理論”,后者是一個更為寬泛而常用的概念。法的本體論只回答“法是什么”、“法的基本架構(gòu)如何”、“法如何作用于社會關(guān)系”等最為本質(zhì)的問題。人們可以通過研究法的本體論來更好地認(rèn)識法的本體,并由此更好地指導(dǎo)自己的社會實(shí)踐。
相應(yīng)的,國際法的本體,是關(guān)于國際法本質(zhì)的抽象存在,主要由國際法的概念、性質(zhì)、分類、效力依據(jù)、淵源、運(yùn)作模式等最為本質(zhì)、抽象的范疇構(gòu)成,是一切關(guān)于國際法的現(xiàn)象與意識的來源。國際法本體論,就是關(guān)于國際法本體的理論。國際法本體論絕不等同于一般所說的“國際法基本理論”或“國際法原理”,后兩者是更為寬泛而常用的概念。國際法本體論只回答“國際法是什么”、“國際法的基本架構(gòu)如何”以及“國際法如何作用于國際關(guān)系”等最為本質(zhì)的問題。國際法本體論是國際法法哲學(xué)的最基本組成部分。人們可以通過研究國際法本體論來更好地認(rèn)識國際法的本體,并由此指導(dǎo)國際社會實(shí)踐。
四、在國際法哲學(xué)中引入本體哲學(xué)思想的意義
在國際法哲學(xué)研究中引入本體與本體論概念,筆者認(rèn)為至少具有以下重要意義:
第一,凸顯構(gòu)建國際法理論的兩大基本元素。實(shí)際上,關(guān)于國際法的性質(zhì),只有兩種學(xué)說:自然法學(xué)與實(shí)在法學(xué)。古往今來,無出其右。其他的理論總是在這兩者之一或兩者結(jié)合的基礎(chǔ)上,提出自己的主張。比如,格勞秀斯(Grotius)提出“國際法是自然國際法與意志國際法的結(jié)合”,普芬道夫堅(jiān)信國際法就是自然法,而特里派爾則認(rèn)為國際法是實(shí)在法。再如,凱爾森(Kelsen)盡管指出國際法是實(shí)在法,自然法是“非科學(xué)的”;但他在建構(gòu)所謂“純粹的”法律體系時還是以明顯帶有自在性的“基本規(guī)范”———“約定必須遵守”為體系基礎(chǔ),可見其理論在本體上仍然跳不出自然法學(xué)與實(shí)在法學(xué)結(jié)合的范示。由此,勞特派特僅承認(rèn)凱爾森的“純粹法學(xué)”具有“方法論”上的巨大意義也就不足為奇了。可見,這兩種學(xué)說是關(guān)于國際法本質(zhì)的認(rèn)識的基本分類,是國際法本體論的基本元素,構(gòu)建完整的國際法理論就要從這兩大學(xué)說入手(當(dāng)然,這種構(gòu)建是一個揚(yáng)棄性的進(jìn)程,筆者提出的新的自然法概念不同于舊的自然法概念)[8]。